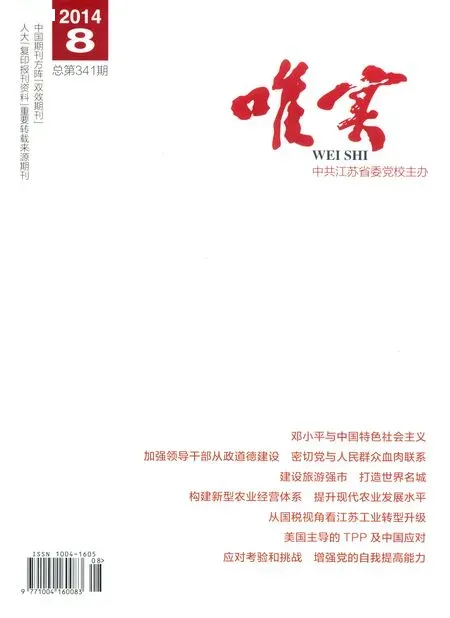抗英殉國的兩江總督裕謙
施國俊
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英國為維護其鴉片貿益,打開清朝深鎖的國門,對中國發動了鴉片戰爭。在這場作為中國中古史和近代史分界線的重大歷史事件中,清宣宗道光帝派出的守疆重臣多為昏庸茍安之輩,“文臣可倚以御侮者,僅林文忠公一人,次則裕靖節耳”(陳康祺《燕下鄉脞錄》,清光緒八年刻本)。這位裕靖節公就是時任兩江總督裕謙。
裕謙(1793—1841年),原名裕泰,字魯山,號舒亭,謚號“靖節”。博羅忒氏,蒙古鑲黃旗人。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禮部主事,遷員外郎。道光六年(1826年),任湖北荊州知府,歷任湖北武昌知府、荊宜施道道員、江蘇按察使、江蘇布政使、江蘇巡撫。鴉片戰爭期間,由江蘇巡撫署理兩江總督,不久實授兩江總督,成為總管江蘇(含今上海市)、安徽和江西三省的最高軍政大員。
一
清中晚期,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在中國進行的罪惡鴉片貿易,成為侵蝕清帝國最大的“毒瘤”,今天看來,徹底剜除這個“毒瘤”是顯而易見的必然舉措。而匪夷所思的是,是否禁煙卻成為當時廟堂上莫衷一是的議題。裕謙作為當時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員,出于民族大義、愛國熱忱,始終堅定地站在禁煙派一邊,順應了正確的歷史潮流。
19紀初期,西方強國開始向中國偷運鴉片,清廷數次禁煙,可效果甚微。道光時,鴉片流毒已十分嚴重,官場腐敗、貪腐橫行,民風萎靡、國民體質日漸虛弱,白銀大量外流。面對這樣一個是非分明、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朝廷中竟爭論激烈,形成兩大對立派別:弛禁派、嚴禁派。當朝的最高統治者清宣宗也態度曖昧,立場動搖。弛禁派荒誕地提出:“聽民間得自種罌粟,內產既盛,食者轉利值廉,銷流自廣,夷至者無所得利,招亦不來。來則竟弛關禁,而厚征其稅。”(梁廷楠《夷氛聞記》)。道光十八年(1838年),鴻臚寺卿黃爵滋上《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疏》,把兩派的論戰推向了高潮,清宣宗把黃爵滋的奏疏發至各省督撫,要求各抒己見,結果弛禁派竟以21∶8占有絕對優勢,由此可見當時體制的衰落、朝廷的腐敗、官吏的昏庸。在這樣的氛圍中,裕謙始終堅定地站在禁煙派一邊,成為當時中級以上官吏中較早主張并認真執行嚴禁鴉片的一員。
早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裕謙還是武昌知府時,就開始嚴禁鴉片。他認為查禁鴉片“尤為目前急務”,頒布了《嚴禁鴉片煙示》,指出“鴉片煙產自外洋,毒于砒鴆,最為風俗人心之害”,嚴令“私開煙館者,照邪教惑眾律擬絞”。并一再強調,“方今最為民害者,唯鴉片煙一項,流毒既廣,病民尤烈”;“鴉片煙上干國憲,下病民生,數十年來銀出外洋,毒流中國,患甚于洪水猛獸”。之后,裕謙轉任荊宜施道道員,在荊宜施道任上,裕謙共緝拿煙犯1000多名。裕謙在所轄地區堅決打擊各種販賣、吸食鴉片活動,有效遏制了煙毒的流害。
道光十四年(1834年),裕謙升任江蘇按察使,5年后,由江蘇布政使署理江蘇巡撫。在江蘇任內,他制定了杜絕上海洋船夾帶煙土章程,加強巡緝內河各船走私并嚴查漕船走私。對待船只走私夾帶鴉片,“一經查出,即將該船執照扣除治罪,船貨一并入官”。在全省城鄉廣貼布告“以懾吸食之心”,對待吸食、販賣、開館者限期查辦,“有犯必獲,獲犯必懲,懲必加重”。一次,他得知自己的一名家丁吸食鴉片,立即依法嚴懲。由于裕謙采取嚴厲而有效的禁煙措施,江蘇境內從上海口岸到各府州縣破獲了數百起走私販賣鴉片案,繳獲了數萬兩的煙土。僅1839年6月至1840年1月,短短7個月時間,“各屬拿辦資販吸食各犯,問擬遣軍流徙統計,不下二千名”。(以上引文見裕謙《勉益齋續存稿》,清道光十八年刻本)江蘇成為僅次于廣東的禁煙成績卓著的省份,有力地打擊了販賣和吸食鴉片的活動,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利益。
二
英國為維護非法的鴉片貿易,于1840年6月悍然發動罪惡的鴉片戰爭。江浙閩粵一帶,是英軍侵略的重點。先后任江蘇巡撫、兩江總督的裕謙,對英國侵略軍入侵江浙保持高度警惕,積極采取備戰措施隨時準備抗敵御侮。
1840年7月5日,侵華英軍第一次攻占浙江定海,江蘇沿海告急。據《清史稿·裕謙傳》記載,當時,裕謙新任署理兩江總督,立即“赴寶山、上海籌防”,他在各關口修造炮臺,添鑄三千斤至八千斤大炮數十位,分口排立。新制抬炮1000桿,分發水陸各營。又命江南提督陳化成坐鎮寶山,調徐州鎮總兵王志元守上海,蘇松鎮總兵田松林守崇明。針對江蘇軍隊習于安逸、營伍廢弛的現象,他“將年力就衰之游擊黃琴及歷練不深之守備孟兆蘭分別勒休撤任”,又“將違例坐轎之中軍副將沙序元及年力就衰之城守協副將張明召分別褫職勒休”。添置武器、調整部署、整頓軍紀、加強訓練,通過裕謙的積極布防,江蘇的軍力大為增強。
裕謙積極建議朝廷派兵收復定海,他上奏道光帝說:“必先收復定海,使之容身無地,水米無資,而后以克制之道,相機堵御,則英人欲進不能,欲守無藉,雖船堅炮利,不能為役矣。”(《清史稿·裕謙傳》)對于甚囂塵上的恐英言論,裕謙嚴詞駁斥。他上疏奏劾欽差大臣、署理兩廣總督琦善“張皇欺飾”“弛備損威”“違制擅權”“將就茍且”“失體招釁”等五大罪狀,并譴責琦善“我兵眾寡不敵”的謊言:“粵中水師船炮,縱不如該夷之勇猛,至陸路官兵,則省城有駐防,有督標、撫標、提標,又有沿海水勇,以數萬計,視賊何啻十倍?而賊之在粵者不過千人,琦善果能調兵嚴防后路,何至夷賊千余,繞出山后,便稱眾寡不敵耶?”(《鴉片戰爭》第3冊,神州國光社1954年版)裕謙認為只要指揮得當,虎門口沙角、大角炮臺的失利是可以避免的。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奉詔去浙江收復定海的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伊里布因畏敵,借口欽差大臣琦善正在廣東和英夷商談,奏請暫緩進兵。清宣宗大怒,免去伊里布欽差大臣,任命時任江蘇巡撫裕謙為欽差大臣,去浙江會同提督余步云收復定海。此時英軍侵占定海已逾半年,供養匱乏、病疫嚴重,故放棄定海南下。清政府終于收回定海。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閏三月,裕謙升任欽差大臣、兩江總督,專辦浙江、江蘇攻剿事宜。裕謙把浙江定海、鎮海作為防御英軍侵略的重點,制訂了定海善后事宜十六條,對定海的防衛進行周詳布置:升定海縣知縣為直錄同知;新筑炮城、月城、土城等大量防御工事;添增炮位,補充軍械;調定海鎮總兵葛云飛、壽春鎮總兵王錫朋、處州鎮總兵鄭國鴻三鎮精兵5600余名駐守定海城。他親自坐鎮嘉興或鎮海指揮,制定了“以御為剿,以守為攻,杜絕救濟,嚴防要隘”(《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2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的防御戰略,并號召和鼓勵軍民人等一齊殺敵立功。他告示于眾:“英逆船只如敢犯我疆圉,不論兵船貨船,陸路則誘其登岸,水路則引使擱淺,槍炮齊發,刀矛并施,同心痛殺。有功者,即來本大臣軍營報功,查驗明確,立即照格給賞,不折不扣。”(《鴉片戰爭》第4冊,神州國光社1954年版)在愛國大義和裕謙的激勵下,江浙一些地方如江蘇崇明民眾“自備斧資,團練鄉勇”,“踴躍奮興,欲圖殺賊”。
裕謙積極備戰捍衛國家主權、民族利益的鮮明立場和仗義執言的品質與當時清朝多數官吏昏庸怯弱、明哲保身的情形形成了鮮明對比。
三
身為江浙抗英前線的最高指揮官,歷史把裕謙推向了抗英斗爭的最前沿。面對當時最先進的堅船利艦,裕謙毫不畏懼,表現出決不向侵略者低頭的大無畏的愛國主義精神。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夏秋間,英侵略軍統帥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帶著大批兵艦自廣東沿海一路北上。8月26日攻克廈門后,英艦繼續北上劫略。裕謙當時正坐鎮鎮海,他立即調兵遣將嚴密布防,并率文武官員誓于神前:“城存俱存,以盡臣職。斷不肯以退守為辭,離卻鎮海縣城一步,尤不肯以保全民命為辭,接受英人片紙。”他上奏清宣宗,如鎮海失陷,“則敵焰愈張,兵心愈怯,沿海一帶必將全行震動”。因此,必須死守鎮海,“非此不能固結兵心,滅此朝食;更非此不能挽回徘徊瞻顧之積習”(《清史列傳·裕謙傳》中華書局1987年版)。其不顧個人安危得失及一心為國之情躍然紙上。
9月26日,英艦29艘滿載侵略軍分三路進攻定海,裕謙命令定海守軍堅決抵抗,“退者立斬”。在裕謙的指揮下,其麾下葛云飛、王錫朋、鄭國鴻三總兵率領部下血戰六晝夜,奮力殺敵,寧死不屈,最后三總兵及大部分守城士兵均壯烈犧牲。10月1日,定海淪陷。
10月10日,英軍在鎮海登陸,分左、右、中三個縱隊進攻鎮海城。裕謙親率鎮兵4000余名保衛鎮海。黎明時,英軍中央和左翼縱隊兩路夾攻金雞山要塞,守將狼山鎮總兵謝朝恩率眾英勇抵抗,戰斗異常慘烈,和敵人多次短兵搏殺后,謝朝恩不幸戰死,金雞山失守。激戰中,浙江提督余步云兩次以保全數百萬生靈為借口,建議裕謙向英軍投降,裕謙斷然拒絕,“此不過茍且旦夕,況有傷國體”(《鴉片戰爭》第4冊,神州國光社1954年版),決然遏制了余步云的可恥意圖。上午,英軍右翼縱隊進攻招寶山要塞,守將余步云不戰而逃,英軍輕取招寶山要塞。中午,英軍在強大炮火的掩護下猛攻鎮海縣城。裕謙登上城樓,冒著槍林彈雨“親援桴鼓”(《鴉片戰爭》第6冊,神州國光社1954年版),鼓舞全軍士氣。他對幕僚說:“勝,為我草露布;敗,則代辦后事。”由于金雞山、招寶山兩座要塞已經陷落,鎮海縣城失去屏障,加之英國侵略軍人數眾多、武器精良,鎮海縣城被英軍攻陷。裕謙寧死不屈,投孔廟泮池殉國,被副將豐伸泰救起,第二天死于舟行途中,終年48歲。清廷贈裕謙太子太保銜,照尚書例賜恤,附祀京師昭忠祠。
鴉片戰爭是19世紀中葉,勃興的西方資本主義強國英國對東方封建古國大清帝國蓄意挑起的一場掠奪性侵略戰爭,雖然衰落腐朽的被侵略方不可避免地落得了割地賠款的失敗結局,但為了國家民族大義進行不屈抗爭的人物、事件理應被歷史記住。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作為封建科舉錄用的滿蒙官吏,裕謙難免存在著不諳洋務、不嫻武備、不智愚忠等問題,他指揮的定海、鎮海保衛戰最終也以失敗告終。但他在禁煙運動中的堅定立場和果斷行動,在反抗外國侵略時的英勇表現,特別是身為欽差大臣、兩江總督這樣的高官,親臨前線指揮對敵作戰,誓死抵抗到底,戰敗后不惜投水殉節,這在當時的滿清官吏中,尤其是滿蒙八旗高官中是極為罕見的。讓我們記住這位歷史上唯一一位為國捐軀的兩江總督——裕謙。
(作者系南京市地方志辦公室地情資料處處長)
責任編輯: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