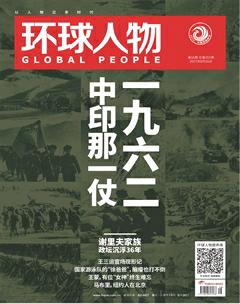王蒙,有位“女神”終生難忘
許曉迪
王蒙:1934年生于北京,中國當代作家、學者,曾任文化部部長,著有《青春萬歲》《活動變人形》等近百部小說,2015年,憑借《這邊風景》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
他的新作講述張仃夫人陳布文的故事,見證兩代人的精神追求
1996年盛夏,62歲的王蒙出國訪問,來到瑞士日內瓦湖邊。他在長椅上坐下,看到了一位老婦人的側影。她右手拿著一個飛盤,拋擲出去,一條哈士奇狗快速躍起,叼著盤子飛奔回來。
一人一狗的游戲,王蒙看了快一個小時,直到老婦人轉過頭,露出一張東方面孔。他心頭一閃,莫名地想起一位故人,一位從未謀面的大姐。
21年后的盛夏,北戴河作協創作之家,83歲的王蒙對《環球人物》記者講起寫作小說《女神》的緣起。他的北京話帶著痰音,沉穩、渾厚,時不時地夾著幾句“門兒也沒有”“也是一絕”“這不開玩笑嗎”的輕松,偶爾會停下來抿一口茶水,另起一個話頭。
這樣的腔調,帶著幾分“話當年”的興奮唏噓,也有幾分老調重彈的意興闌珊。他所講述的,不僅是一位女性的傳奇人生,也是一代人從青春到暮年的滄桑歲月。
“女神”的歸來
《女神》發表于2016年《人民文學》11月號,今年又出了單行本。在小說的后記中,王蒙說他的寫作,是還一個久未兌現的陳年老賬,為他念念不忘的“陳姐”,營造一個小小的紀念碑。
60年前,1956年,也是在《人民文學》——當時最輝煌的文學刊物,王蒙發表了他的成名作《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這一年,他22歲。
故事發生在一個區委會,小說的主人公林震從學校調來組織部后,發現這里充斥著各種類型的官員——萎靡世故的、外強中干的、腐化墮落的,在與各種權力、腐敗的斗爭中,這位“新來的青年人”陷入了迷惘和困惑。
小說一發表,就引發軒然大波,嚴厲的批評一度占了上風,王蒙被指責是“用個別現象里的灰色斑點,夸大地織成了黑暗的幔帳”。論爭最終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他盛贊小說是一部“反官僚主義”的作品,王蒙有“文才”,是新生力量,要保護。
一時間,云過天青,轉危為安。王蒙由一個無名小卒,躍升為文壇的“新生力量”。在為小說修改召開的座談會上,王蒙的發言謙虛、謹慎,大段背出《反對自由主義》《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原文,體現了一個老黨員的穩重、深沉。
會后,王蒙收到一封信。信中所寫,是對他發言的失望:“你的發言是多么平和,多么客觀,又是多么令人不愉快地老練啊。”他按照所附的電話號碼打過去,聽筒里傳來爽朗的大笑:“王蒙同志呀,現在已經找不到像我這樣多事的人啦,哈哈哈……”
這就是王蒙與其心中“女神”的一“信”之緣、一“(電)話”之緣。
一個月后,形勢急轉直下。王蒙被打成右派,下放農場,背石頭、種樹、遷墳、釘馬掌,干了幾年的體力活。之后,他帶著全家遠走新疆,一去16年。1979年,王蒙重回北京,成為歸來的英雄,“重放的鮮花”,文學青年的偶像。他被委以重任,從《人民文學》主編到作協書記,從中央委員到文化部部長……芝麻開花節節高,在上世紀80年代,王蒙成了文化舞臺上的主角兒、大腕兒。
“故國八千里,風雨三十年”。經歷了大起大落、大開大闔,當年的那封信、那通電話早已湮沒在歷史煙云中。直到1996年,在瑞士日內瓦湖邊,看到那位與狗一起玩飛盤的婦人,王蒙“如遭電光石火,心頭一閃”,“沒有任何來由地想起了她”,想起了信中醇厚文雅的行楷,和電話里響亮的哈哈大笑。
早年間,王蒙也曾多方打探,一些老藝術家也明明白白地告訴他,“她”是藝術家張仃的夫人。“是我自己較勁。”王蒙說,“我想知道的,是她個人的歸屬、經歷,‘某某的夫人在我的頭腦里沒有感覺,像一個零,也像一個謎。”
2016年,王蒙曲里拐彎地打聽到,“她”是藝術家張郎郎的母親。“我把張郎郎夫婦請到家中吃飯,聊天時才知道,1957年和我通電話時,37歲的她,已經是一名家庭婦女,‘張仃的夫人確實是她唯一的身份。更使我驚奇的是,她曾經是延安青年,投身革命,新中國成立后擔任周恩來總理的秘書,最終卻選擇退職回家,買菜做飯,養育子女,簡直是革命隊伍里絕無僅有的人物。”
他將種種感觸,通通寫進了小說《女神》。時隔60年,陳布文——這位充滿傳奇色彩的女性,在王蒙的文字中復活、歸來。
最文化的家庭主婦
1920年,陳布文生于江蘇常州的農村,自小寫得一筆好字。16歲時,她給林語堂主編的《論語》《人間世》投稿,字體雖然秀麗,但寫作風格卻幽默老辣,被編輯們誤以為是位中年男性作者。
1937年,陳布文逃婚,從家鄉來到蘇州,和青年畫家張仃相識,結為伴侶。第二年,他們雙雙到達延安,開始了革命+文藝的不凡人生。
在延安,張仃是特立獨行的人物。他身穿皮夾克,腳蹬長筒皮靴,與詩人塞克、歌唱家杜矢甲,并稱延安的“三大怪人”。三人湊到一起,活脫脫一個波希米亞小群體。他曾經舉辦過一次漫畫展,畫的大多是作家、藝術家的頭像。他也給妻子畫了一幅:一個有著五官的紅紅的西紅柿,兩邊加了兩條小辮。
20多歲,陳布文隨軍去了東北,在《東北日報》當記者,一桿毛筆、一個墨盒就是她在戰爭年代的武器。很快,她就因書寫的迅速、漂亮而名聲遠揚。新中國成立后,她進入中南海,成為周恩來的機要秘書。
很難想象,這樣一個天之驕子,竟會在32歲選擇離開,先是在大學教書,一年半后又離開講臺,還原為白丁——家庭主婦。
“我不清楚她告別政治的原因。她是6個孩子的母親,需要輔佐丈夫、照顧家庭,這是最現實的考慮。也許,她厭倦了‘高處不勝寒、加班加點的匆忙日子。在她的小說《假日》里,就透露了對工作壓倒生活的不滿。”王蒙說。
“退職回家”后的陳布文,成了家里的“伙頭軍”,每天面對著白菜豆腐,紐扣拉鎖,尿布床單,雞毛蒜皮。她愛上了京劇,“有事無事喜歡坐在沙發上練習手指,一個人扮演所有的角色……但就是不準我們聽她的自演自唱”。兒子張郎郎回憶道。
張郎郎生于延安,長于北京。少年時愛好寫詩,模仿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駭世驚俗地剃了個光頭,穿件俄式軍棉衣,腰里勒一根電線,每天早晨在圖書館前的小松林里,狂背老馬的詩。1960年,張郎郎和同學組成詩歌沙龍,定期在家里活動,交流詩作、繪畫,閱讀當時的“內部參考書”。
“家庭主婦”陳布文,也是沙龍的參與者與指導者。“母親常常告訴我,藝術家就是叫花子,問我是否甘心如此……在話語中,她對官僚習氣的蔑視,直言不諱,我從小就耳濡目染。”
1962年底或1963年初,先鋒詩歌社團“太陽縱隊”宣告成立。成員包括張郎郎、巫鴻、郭路生(即食指)等。1966年“文革”爆發,張郎郎被公安部通緝。逃跑前夜,他在友人王東白筆記本的扉頁上匆匆寫下四個大字:“相信未來”,1968年食指正是以此為題,寫下了名滿天下的代表作。
“在大風大浪中,陳布文始終保持著從容、鎮靜,這是她最不平凡的一點。”得知兒子被判死刑后,她沒有掉一滴眼淚,從早晨坐到晚上,一言不發,直至黃昏,一個朋友趕來,告訴她周總理的批示,保住了張郎郎的命,她才深深地嘆出一口氣。“文革”中,張仃被“紅衛兵”揪斗毆打,她沖向前去,大喊大叫,聲色俱厲,大講井岡山、遵義與延安的故事,居然從氣勢上壓倒了對方。
在政治運動爆炸火熱的時代,陳布文安穩度劫。1985年12月,她因病逝世。彌留之際,她對家人說,想去一趟日內瓦,再看看周總理開會的地方。
31年后,王蒙來到日內瓦,為她獻上了無比尊崇的贊語:“你是最文化的家庭婦女,最革命的母親,最慈祥的老革命,最會做家務的女作家與從不臭美、不知何為裝腔作勢的教授。”
“碩果僅存”的女性主義男作家
生于1934年的王蒙,被朋友們戲稱為中國“碩果僅存的、具有女性主義意識的男作家”。他對女性的認識、描摹,帶著鮮明的“王蒙印記”——首先是平等,然后是理解。
在自傳中,王蒙描寫了自己的父親,一個綽號“王爾巴哈”的哲學家,喝咖啡,愛藝術,崇拜科學,更是游泳愛好者,有些神經質和情緒化。在他的印象里,父母之間總是充滿紛爭,甚至大打出手。母親的陣營還有姥姥、二姨兩個女人,有一回,二姨順手抄起一鍋沸騰的綠豆湯,向父親潑去。而當3個女人一起沖向他時,這個男人的最后一招竟然是:脫下褲子。
因為父親的揮霍、放縱,王蒙對女性有深切的同情。“我受‘五四精神的影響,從小就讀魯迅、巴金、茅盾、冰心的作品,知道女性解放對于現代國家的意義。民國時有一位女英雄唐群英,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時,黨綱中刪去了‘男女平權的內容,她怒不可遏,沖到主席臺就給了宋教仁一耳光。剛解放的時候,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郭蘭英唱的《婦女自由歌》:‘舊社會,好比是,黑格洞洞的苦井萬丈深;井底下壓著咱們老百姓,婦女在最底層。革命最大的號召力,就是給予‘翻身的希望。”王蒙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青年時代的王蒙,每天讀詩和寫詩,大段背誦契訶夫戲劇《櫻桃園》與《萬尼亞舅舅》中的臺詞,讀巴爾扎克《人間喜劇》動輒失魂落魄到深夜,用五角錢一張的炭質唱片聽柴可夫斯基和司美塔那的音樂。那時的他,筆下浸染著革命的熱忱與文學的浪漫,尤其是書中那些年輕女性:《青春萬歲》里的女中學生鄭波、王薔云,活潑真誠,投身于革命事業,呼喚自由平等;《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里的趙慧文,與林震一樣,不甘于在平凡瑣事中沉淪,他們互通心曲,一起聽音樂、煮荸薺,欣賞油畫和春夜的槐花香氣。
1963年,王蒙全家來到新疆,在此扎根16年。在這里,王蒙褪去了“小資產階級”最后一點多愁善感,他學會一口流利的維吾爾語,與當地群眾打成一片,一起吃著馕餅、喝著奶茶,一起在戈壁灘的皓月下放聲高歌,一起在麥場上勞動,一起吃著哈密瓜天南地北地聊天……在這一時期創作的《這邊風景》里,王蒙塑造了雪林姑麗、愛彌拉克孜等美麗、溫婉、柔弱而堅強的女性形象,也描寫了瑪麗汗、帕夏汗等婦人的狠毒、顢頇、狂野和恣肆。在“政治壓倒一切”的時代,王蒙的描寫,抵達了令人驚嘆的復雜、深邃與美好。
從《蝴蝶》到《活動變人形》,從《青狐》到《奇葩奇葩處處哀》,從封建時代到革命時代,從改革時代到市場時代,王蒙筆下的一個個女性,也疊印著他個人的命運沉浮。而在現實生活中,對他影響最深的女性,莫過于妻子崔瑞芳。
崔瑞芳是王蒙的初戀,一見鐘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她曾穿著半高跟鞋,去京郊看望在那里勞動的王蒙,不惜與一切對丈夫不好的親人決裂;當王蒙在電話里說起要去新疆時,她立刻就同意了,兩人帶著3個孩子和全部家當,再加上兩條游在黃桃罐頭瓶里的金魚,風風火火地登上西去的火車……2012年3月23日,崔瑞芳去世,享年79歲。告別遺體時,王蒙在靈柩前失聲痛哭,幾近癱軟。在場之人,無不動容。
后來,王蒙又遇到了新的愛情。他不愿意自己的感情被娛樂化,干脆用寫文章、上電視的方式告訴讀者,他再婚了。
83歲的“高齡少年”
在小說《女神》中,王蒙解釋了在他心目中,何為“女神”:歷經坎坷,同時又純真地執著于理想信念的女性,方稱得上“女神”二字。
純真、執著、理想,也是王蒙人生的關鍵詞。作協主席鐵凝說王蒙是“高齡少年”,因為他對生活中各種事永遠都充滿興趣。
《環球人物》記者采訪王蒙時,他正在北戴河的作協創作之家。從1999年起,每年盛夏,他都會來到這里,在海濱待上一個月,上午寫作,下午游泳,晚上散步,回去后上上網、聽聽歌,從柴可夫斯基、蕭邦到蔣大為、李谷一,從古琴、洞簫到周璇、鄧麗君……“這就是我的天堂,我的共產主義!”這幾年,北戴河游泳場以年齡為由,規勸他不要游泳,他還是堅持下海,劈波斬浪。
20多年前,王蒙就學會了用電腦寫作。那時他正在寫“季節”系列,以“四部曲”(《戀愛的季節》《失態的季節》《躊躇的季節》《狂歡的季節》)講述一代革命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對他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不是身外之物。
然而,他身外的世界,卻在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當它寫出來的時候,社會的關注早已經是別樣了。市場、公司、股票、購房、購車、懲治貪官、買斷工齡、打工仔、托福、高考、三陪、足浴、醫療改革、黃金周旅游……”
在一些批評家眼里,王蒙過時了,老套了,現在的時代是新人的舞臺。對于這些評論,王蒙并不太在意。“他屬于某個時代,但絕不甘于被同代人所局限。他喜歡和年輕人相處,他的思緒不斷突破時空的限制。”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郜元寶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當王朔異軍突起,卻遭到猛烈抨擊時,王蒙寫了一篇聲援文章《躲避崇高》,其中有這樣一句:“他(指王朔)的一句名言‘青春好像一條河,流著流著成了渾湯子,頭半句似乎有點文雅,后半句卻毫不客氣地揶揄了‘青春常在‘青春萬歲的浪漫與自戀。”
這種拿自己當靶子“開涮”的勇氣,讓王蒙與王朔一起被綁在了靶子上。“我評價王朔是‘微言小義,入木三厘,他不可能像史鐵生一樣,對人生有沉甸甸的思考。他寫得淺,但幽默中有對人生的嘲諷和揶揄,那是另一套生活的感受。”
2013年,王蒙在電影院看了電影《小時代》。他更是震驚于這代人的勇氣,“青春都不是吃素的。我們這代人,從小聽到的都是‘大時代,竟然還能在時代前面加‘小字?”
“有大時代就有小時代,時代有雄偉的一面,當然也有瑣碎的一面。”王蒙說,“‘革命很浪漫,是狂飆突進,是翻天覆地。但是,我們不能世世代代過著游擊隊的生活,像切·格瓦拉一樣,為了理想一次次遠離現實。我們要和平,要建設,要小康,要過日子;這樣一來,又難免會走向世俗、庸俗乃至低俗。這就是歷史,這就是人生,永遠在發展,永遠無止境,永遠有遺憾。”
83歲的王蒙一直保持著生命的熱力。“他唱歌,豪情萬丈,唱俄羅斯歌曲,聲震屋宇,將我震得耳鳴了好半天。他‘以睡為綱,讓許多失眠者羨慕嫉妒恨。他效率奇高,有一次我失眠,早晨5點給他發e-mail,咚的一下立即收到回復,嚇了我一大跳。”郜元寶向記者說道。
耄耋之年的王蒙是《鏘鏘三人行》《圓桌派》這類新銳談話節目的常客,在其間笑論人生,揮灑自如。他談女權問題、談大齡剩女、談兩性責任,在年輕人的話語場中,他的發言毫無違和感。
就在4個月前,王蒙站上了《朗讀者》的舞臺,讀了《明年我將衰老》的一段,獻給已故的妻子和3個孩子。“我仍然是一條笨魚,一塊木片,一只傻游的鱉。我還活著,我還游著,想著,凍著。活著就是生命的慢漲。”
是耄耋抒懷,也是青春狂歌。正如他所說,“學習到老,成長到死,困惑少一點了,不是由于沒有困惑,而是由于對什么事更耐心,更從容,更善于等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