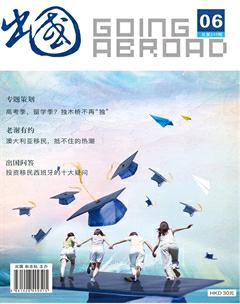德國大學初體驗
王雪妍
雖然已經過去很多年了,然而每每回憶起自己剛剛踏入德國大學校園時的情景,喜悅、興奮、迷茫、孤獨、惶惑……五昧雜陳的感受仍然記憶猶新。
三月份我通過了德語語言考試,在大學注冊為正式學生,便順理成章地進入到了德國大學的學習生活之中。我的Master學習其實是從十月份的冬季學期開始的,現在這個夏季學期只是我的零學期,也就是說我可以去聽課,但并不能參加期末考試,不能獲得學分。這樣也好,我相信有這一個學期的時間準備,下學期我肯定能以更好的狀態,快速投入到自己的學業中去。
德國的大學沒有圍墻,不像在國內,大學校園被集中在一片特定的區域里,這里的教學樓、宿舍樓、食堂就散落分布在整座城市之中。有些建筑既供大學里的教師和學生使用,也是屬于這座城市的公共設施。我所在的德累斯頓理工大學有著將近二百年的歷史,古老的教學樓見證著這所大學的興衰變遷,里面的木質桌椅,紅磚墻壁,似乎都在散發著濃濃的文化學術氣息,坐在其中,我的心情也會不由自主地沉靜下來。
大學的留學生管理處經常會組織一些校園參觀活動,由每個學院的高年級學生志愿者帶領,幫助新來的外國學生了解大學的歷史發展,認識上課地點,熟悉選課流程,使我們這些新生能盡快融入到德國的大學生活中去。夏天的德累斯頓美不勝收,晚上九點多鐘天空依然明亮。在這座美麗的城市里,我喜歡和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們坐在校園后面的一處空草地上,悠閑地談論著各自國家的風俗文化,談論在德國的種種有趣的見聞,談論過往的經歷和未來的理想……
周一至周四,每天都有一堂一個半小時的講座。開始時我像聽天書一樣什么都聽不懂,雖然我以優異的成績通過了德語語言考試,但是教授的薩克森州方言伴著飛快的語速,還有數不盡的專業詞匯,都讓我覺得無所適從。
有一次,晚上七點鐘在圖書館的報告廳里舉辦一個傳播學的專業講座“Wie kommuniziert man in der Krise?”(在危機中人們怎樣傳播),主講人是Klaus-Peter Johanssen,企業危機公關領域的專家。Johanssen是一位典型的研究型學者,說話不緊不慢,語調平穩清晰,可是我聽這樣的專業講座還是有很大困難,只能聽懂個別單詞和句子,主講人口中專業的遣詞造句讓我聽得云里霧里。伴隨著幻燈片上的文字,我基本上理解了講座的大意——主要是以Shell(殼牌)公司為案例,講解了企業在危機中應該如何應對與處理。對我來說,講座中最大的困難其實并不是語言上的困難,而是自己當時心中的不淡定。近百人的報告廳里只有我一張亞洲面孔,前后左右都是金發碧眼的德國男孩女孩;我覺得自己像動物園中展覽的大猩猩,每個人都會用異樣的眼光看著我,雖然我明明知道并沒有幾個人會在意我的存在,然而我的心跳速度卻比平時要快很多。孤獨、陌生、歸屬感的缺失,再加上聽不懂的外語,隨之而來的便是自己心中的不知所措與惶恐不安。就這樣一直堅持了近兩個小時。也就是在這兩個小時里,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身在他鄉的寂寞與格格不入。后來我安慰自己,這就對了!意識到了差別才能消除差別;感受到了孤獨才能戰勝孤獨。如果身在德國始終感覺跟在中國一樣。那恐怕才是一種不正常的狀態吧!
不得不承認,德國大學的講座真的很有價值、很有水平。上講座課的全部都是教授,將理論知識講的深入淺出,一堂課下來讓學生覺得充實而富有收獲。所有教授的PPT課件也做得很嚴謹,幻燈片上的每一張插圖、每一幅圖表,一定都會標明來源出處。讓我充分感受到,這里才是真正神圣的科學的殿堂;知識在這里才能真正贏得我們的敬仰與崇拜。
想起來覺得自己真的很幸運,當其他中國同學都在抱怨交不到德國朋友的時候,在一次講座課上,我認識了烏利,一個熱心友好的德國男生。當時烏利就坐在我的旁邊,我看著教授放的不是很清楚的幻燈片,就問他網上有沒有課件下載,他很熱情地為我寫下了網址和下載密碼,然后我們就隨意聊了起來。從那以后,有幾次講座我們都坐在一起,我有什么不懂的問題問他,他總會細致耐心地為我解答。
除了專業課,大學還設有豐富多彩的體育課,以及二十多種語言課,可供大學學生選修。在這個沒有考試壓力的零學期,我選修了擊劍和西班牙語,既是知識上的增長,同時也是眼界的開闊和自身經歷上的一種豐富。來到德國的大學,我像一條池塘里的小魚游進了寬廣的海洋,面對著全新的環境,雖有種種不適應,但我還是對周圍的一切感到新鮮和興奮,并對未來的學習生活充滿了無限的憧憬。
我的德國大學生活才剛剛拉開帷幕,我知道,這一定不是一條平坦輕松的道路,里面不僅僅有鮮花和驚喜,也會有坎坷,有荊棘。
為了補充專業知識,同時提高自己的語言能力,我常常在圖書館里自習到晚上十二點,直到廣播里傳出“圖書館還有十分鐘就要關門”的通知,我才收拾好書本準備回家。抬頭望望四周,我并不是最晚離開圖書館的,很多留學生以及德國本地學生都在抓緊利用著最后一分鐘的時間埋頭苦讀。走出圖書館,天已經全黑了,一陣風吹過,路邊的落葉翻著跟頭在街上舞蹈。在走向車站的路上,我忽然想起來,今天是周末,公交車都比平時少。果然,在11路S-Bahn的車站,我孤伶伶地等了二十多分鐘。平時要四十多分鐘的路程,今天由于等車花了一個多小時。
在大學的宿舍樓區,窗戶里發出的點點燈光并沒有想象中的陌生和疏離,反而就像友好的德國人在向我微笑,親切而自然;但是這種微笑也只是禮節性的,它并不能深入內心給人以安慰。我和這座城市、這片宿舍區此時此刻就這么毫不相干地各自存在著,仿佛唯一的交點就是我腳下的土地和吸進身體里的氧氣。又一陣風吹過,我捋捋頭發,裹緊了外衣。不知什么時候,我的身后多了幾個身影,那是三四個喝得半醉的德國學生,嘴里還說著我聽不懂的帶著薩克森口音的德語,我不自覺地加快了腳步。第二天早晨,走出宿舍樓,迎著風,揚起下巴,挺起胸膛,我忽然覺得像凱旋的勇士一般渾身充滿了力量,只想在心里大喊一聲:
“德國大學,我終于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