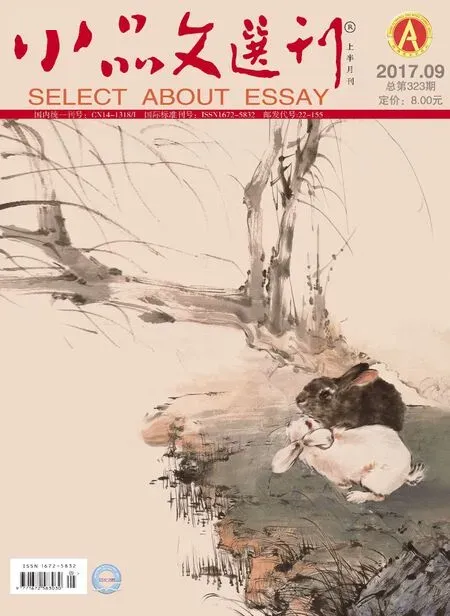故鄉(xiāng)冊(cè)頁(yè)
□李云飛
故鄉(xiāng)冊(cè)頁(yè)
□李云飛

窠立臺(tái),這三個(gè)方塊漢字,恰似三粒有棱有角的苦蕎麥,喂養(yǎng)了一座村莊。這是一個(gè)小小的山村,幾十個(gè)依山而建的庭院,幾家有高頭大門,紅漆門板,幾家沒(méi)有圍墻,沒(méi)有大門。從對(duì)面山頭看過(guò)去,直接可以看到窯洞的門簾,像一面旗幟在飄動(dòng)。揭起門簾,一窯洞的溫馨,就是一家人的天下。還能看到院里的犁,鐵锨,在太陽(yáng)下泛著清閑的光,掛在房檐下的那彎鐮,像一鉤新月,照著周圍的谷穗、苞谷和一頂舊草帽。
有一次回到老家,我發(fā)現(xiàn)豁峴里突然多了一座石碑,好像也從土里長(zhǎng)出來(lái)似的,方方正正,立在路邊,猶如村莊一個(gè)小小的屏風(fēng)。黑色的石碑上,刻寫著幾個(gè)堅(jiān)硬的大字“窠立臺(tái)遺址”,下面還刻著一行小字:“甘肅省人民政府立”。這是地方最高一級(jí)政府為這片貧瘠土地樹(shù)的碑。我那天路過(guò)時(shí),看見(jiàn)幾只羊正在那里吃草,放羊老漢懷抱榆木鞭桿坐在那里,靠著石碑打盹。風(fēng)從豁峴吹過(guò)來(lái),塵埃一層層落在他身上,使他越來(lái)越像一件剛剛出土的新石器彩陶。
故鄉(xiāng)的源頭,從一只彩陶的花紋里緩緩流瀉出來(lái),離離荒草隨風(fēng)搖曳,繪在罐壁上的一只青蛙,因?yàn)楦珊裕钜稽c(diǎn)就叫不出聲了,黃土地的喉嚨里噙著五千年的一聲嘆息。新石器,一個(gè)堅(jiān)硬的時(shí)代,那些夾生的日子,早已成了片片化石,風(fēng)一吹,滿天的星星就斑駁成了一座月光的廢墟,或者遺址。
我的故鄉(xiāng),土的天下,最窮的是土,最富的也是土。土地上,駕著毛驢耕作時(shí),泥土翻出嘩嘩的波浪,好像長(zhǎng)莊稼又長(zhǎng)野草的土地,忽然之間興奮了起來(lái),自己把自己樂(lè)成了一朵土色土香的奇葩。土路上,車輛馳過(guò)時(shí),攪得湯土一路飛揚(yáng),仿佛那些不安分的土,在故意追著車子跑,也想乘上車去山外看看桃花和杏花,還有山娃打工的地方是啥模樣。土廟里,住著土地爺爺,他老人家好像也是單身漢,沒(méi)有神仙眷侶,孤苦伶仃,看著土生土長(zhǎng)的村民一輩子面朝黃土土里刨食,他慈悲的心腸就難過(guò)得啊,說(shuō)不出一句土言土語(yǔ)。
我們村子里的廟,規(guī)模不大,也很樸素,像一戶幸福人家的庭院,坐落在村莊最北面,臨紅塵而居,與人為鄰。廟里居住的神仙,似乎成了我們的村民,有了和我們一樣的籍貫。充滿鄉(xiāng)土氣息的廟宇,和家家的上房一樣,坐北向南,面朝村莊,冬暖夏涼,春暖花開(kāi)。
我讀過(guò)書(shū)的小學(xué)校,這里原先有幾棵樹(shù),榆樹(shù)、杏樹(shù)和白楊樹(shù),它們的枝干、葉子和根,上世紀(jì)就化為灰燼,重新返入大地作了泥土。不大不規(guī)整的院子成了耕地,去年的地膜還捂著干枯的記憶。崖畔下面的窯洞已經(jīng)坍塌,空洞的門口堆著一堆黃土,還有塵土不斷落上去,好像要把傷口一樣的窯洞封存。一群麻雀,嘰嘰喳喳地追逐著飛入破敗的窯洞里,小小的翅膀,攪起塵土如攪動(dòng)了舊時(shí)光,在窯洞里涌動(dòng),久久不散。
記得王校長(zhǎng)把那片犁鏵掛到校門口的杏樹(shù)上時(shí),正是春回大地的日子,他用一節(jié)榆樹(shù)根敲打,先是敲掉一層紅銹,然后敲出一片歡快的聲音,陽(yáng)光一樣灑滿村莊。每天早晨,王校長(zhǎng)一邊敲鐘,一邊看著從各個(gè)山頭上走來(lái)的學(xué)生,心里默念著他們土里土氣的名字,直到一個(gè)不少地走進(jìn)校門。這時(shí),對(duì)面山上耕地的人,也學(xué)著王校長(zhǎng)的樣子,用鞭桿敲了敲泥土擦亮的犁鏵,居然也像模像樣地敲出了幾聲漢字的音韻。
莊稼花次第開(kāi)放的時(shí)節(jié)到了,它們大紅大紫地走來(lái),喧囂、奢華、洶涌,我無(wú)法一一細(xì)數(shù),豌豆撕扯不清的蔓上,一群蝴蝶,抑制著激情,在認(rèn)真排演雜技節(jié)目。也許蝶兒們紫色的心事太重了,豆蔓被壓得撲倒在地,而它們的演出似乎才開(kāi)始,還得層層攀援節(jié)節(jié)高升。小麥一個(gè)比一個(gè)樸素,它們最有金子一樣的身世,卻一點(diǎn)不事張揚(yáng),不像洋芋,在頭頂上別上一大件一大件銀飾,東施效顰地學(xué)牡丹,學(xué)來(lái)學(xué)去,沒(méi)想到學(xué)成了山坡地上的新土豪。蕎麥開(kāi)花太鋪張了,遍地的香一疙瘩一疙瘩涌動(dòng),濃烈得讓人無(wú)所適從,讓人忘記了其他的莊稼也還在山坡上開(kāi)花。
紫苜蓿,藍(lán)胡麻,在對(duì)面的山坡上,它們同時(shí)開(kāi)了花,在六月茂密的陽(yáng)光下,胡麻和苜蓿好像比賽似的,看誰(shuí)家的日子過(guò)得紅火。實(shí)際上,作為好鄰居,它們的美好品德,都蕩漾著馨香的漣漪,被風(fēng)一遍遍傳頌著。胡麻那小小的花朵,像放置在絲綢上的一個(gè)個(gè)小小的紫色酒杯,精美而高貴,落入其中的細(xì)雨滴,都被芬芳釀成了甘醇。那些蜂蝶從花朵上起飛的模樣,個(gè)個(gè)都像喝醉了酒,搖搖晃晃,忽高忽低,不忍離開(kāi)的樣子。
七月,新收割的小麥運(yùn)上了場(chǎng),家家大門口,摞起的麥垛子,都是一座小小的麥積山。這一座山上,每一粒麥衣殼,都是一座佛龕,都住著一位慈祥的胖菩薩,每一個(gè)從這座山下走過(guò)的人,抬頭仰望時(shí),內(nèi)心都會(huì)涌滿虔誠(chéng)。
石磨、碌碡,這些村莊的石頭,成了黃土地的骨骼,面對(duì)歲月的風(fēng)吹雨打,總有一種沉重表情,保持著堅(jiān)定立場(chǎng),為所有的莊稼鋪平通向糧食的道路。石磨曾經(jīng)把到口的糧食一粒粒嚼碎,用五谷的芬芳把村莊頭頂?shù)哪敲对卵酪惶焯煳古郑汛迩f的日子喂養(yǎng)成人,慢慢拉扯大,而自己總是挺著一副瘦骨嶙峋的身子,一圈又一圈畫著自己的圓,圓別人的夢(mèng)。
土被逼急了也會(huì)造反,比如在缺雨少雪的那些日子里,土的心里渴極了,容顏被人和畜一遍遍走來(lái)走去踩踏得傷痕累累,土的身子被車輪一寸寸碾壓成粉末時(shí),土實(shí)在是忍無(wú)可忍了,就隨風(fēng)而起,一路反上天去。有人說(shuō),那是土待在地上太久了,想到天上去看看那朵雨做的云,順便站在高處,看看遠(yuǎn)方水做的河流。
我記得張老漢經(jīng)常在挖水窖,在豁峴最低的地方,以便集聚更多的雨水。仿佛他六十多年的人生,經(jīng)常被大旱逼到了最低處,滄桑的風(fēng)云多,滋潤(rùn)的雨露少。他挖窖時(shí)像一只打洞的黃鼠,漸漸地整個(gè)人陷下去了,只看見(jiàn)他把干透的黃土,一锨一锨丟上來(lái),他從窖里上來(lái)時(shí),活脫脫一疙瘩黃土塊,被自己從窖里扔了上來(lái),就像土地剛剛誕生的一個(gè)嬰兒。
干旱山區(qū),一戶人家打一眼水窖,就像現(xiàn)在城里人買一套樓房。誰(shuí)家要打一眼水窖,就像操辦一場(chǎng)盛大的事情,家家戶戶都來(lái)人幫忙,挖窖胚、敲打紅膠泥,每一樣活兒都得操心費(fèi)氣、出力流汗。打窖就像制造一件瓷器,打成的水窖,從內(nèi)形去看,酷似一件高頸花瓶;從地上看,一眼水窖,就像一只眼睛,眼巴巴地望著天空。打成一眼水窖,如果裝滿一窖水,那簡(jiǎn)直就是裝了一窖白花花的銀子。
選自《甘肅日?qǐng)?b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