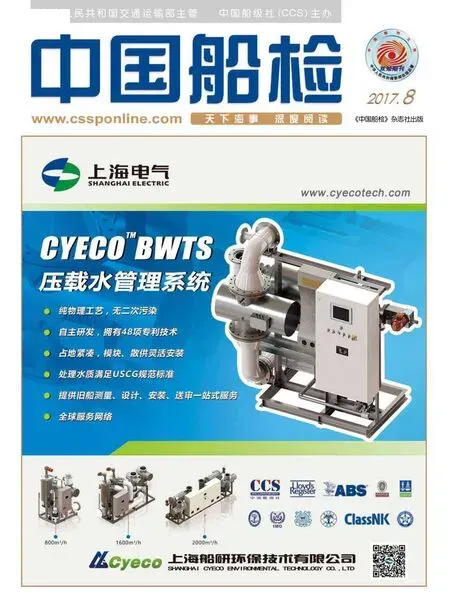智能船舶的發展對國際海事公約帶來的影響
中國船級社 蔡玉良 馬吉林
聚焦
智能船舶的發展對國際海事公約帶來的影響
中國船級社 蔡玉良 馬吉林
時下,船舶智能化大潮正洶涌而至。那么,船舶智能化主要有哪些特點?這股浪潮將給國際海事公約帶來怎樣的影響?海事界應如何應對?
近年來,自動控制、信號處理、網絡通信、傳感器、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快速發展,并與工業生產深度融合,為傳統工業的轉型升級帶來了新契機。在近日舉行的2017世界交通運輸大會上,與會專家幾乎無一例外地將“未來交通”的籌碼押在“無人駕駛”上,而對航運業而言,“人工智能+船舶”同樣被寄予厚望,相信很多人都觀看過羅爾斯·羅伊斯公司發布的無人駕駛船控制中心的演示視頻并被其“科幻”效果所震撼。船舶智能化乃至無人化是當今航運界的發展趨勢。
另一方面,船舶不同于其他交通工具,由于其具有遠航程、大運力、低運價的特點,一直以來都作為國際貿易運輸的主要方式。因此,為了保障海上航行安全,提高船舶航行效率,在防止和控制船舶對海洋和大氣污染方面采取統一的標準,以國際海事組織(IMO)為代表的權威機構制定了大量的公約、規則供世界各國遵照執行。公約、規則會根據航運狀況的發展進行修訂并定期發布。本文旨在通過分析智能船舶的發展,初步解析其對現行公約、規則可能產生的影響。
智能船舶的發展
中國船級社所理解的智能船舶是指利用傳感、通信、物聯網等技術手段,自動感知和獲得船舶自身、海洋環境、物流、港口等方面的信息和數據,并基于計算機技術、自動控制技術、大數據技術、智能技術,在航行、管理、維護保養、貨物運輸等方面實現智能化運行的船舶,以使船舶更加安全、更加環保、更加經濟、更加可靠。智能船舶的發展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所以我們用了“更安全、更環保、更經濟、更可靠”的說法。
智能船舶應具備四個特點:
1、具有感知能力,即具有能夠感知船舶自身以及周圍環境信息的能力;
2、具有記憶和思維能力,即具有存儲感知信息及管理知識的能力,并能夠利用已有的知識對信息進行分析、計算、比較、判斷、聯想、決策;
3、具有學習和自適應能力,即通過專家知識以及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不斷學習積累知識并適應環境變化;
4、具有行為決策能力,即對自身狀況及外部環境做出反應,形成決策并指導船岸人員,甚至控制船舶。
如圖1所示,智能船舶的發展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從當前的互聯互通、系統整合到未來的遠程控制、自主操作。
互聯互通是智能船舶的最初階段,布置感知系統,建設系統間以及船岸間的通信和數據共享能力,實現對船舶的遠程監測。
系統整合階段制定統一的船舶數據標準,逐步將多源異構系統整合為單一集成系統,實現平臺化管理。為實現“一平臺+多應用”的目標奠定基礎。
遠程控制:管理人員在岸基控制中心、母船等位置,通過遠程通信手段,實現對被控制船舶的操控。遠程控制應用的前提是需要解決設備的健康管理等一系列技術問題。
自主操作:在感知的基礎上,利用高度復雜的軟件技術、控制算法,例如基于博弈論的避碰技術,形成控制指令。自主操作船舶具備自適應能力,無須船員進行常規操作。
其中第三、四階段即是目前“時髦”的“無人智能船”所具備的特點。無人智能船是指沒有船員在船的情況下可以控制運動的船舶。無人智能船可以是遠程控制船舶,也可能是自主操作船舶。
對國際海事公約可能產生的影響
現行海事公約架構主要分為三類,如圖2所示。第一類關注的是管轄權規則,旨在規定船旗國及其船舶的權利及義務,代表性的公約是《聯合國海洋公約法》;第二類關注的是船舶的技術條件及運營狀況是否滿足海上航行安全、防止海洋污染,船員基本權利是否得到保障等,代表性的公約有《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國際海上避碰規則》、《國際海事勞工公約》等;第三類關注的是由船舶事故造成的機海損而導致的民事責任劃分,代表性的公約有《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海事索賠責任限制公約》等。
從前文可以看出,當船舶智能化尚處在第一、二發展階段時,現行公約、規則框架尚能適用,當進入第三、四階段后,船舶的智能化程度高度提升,帶來的最顯著變化就是“在船”船員數量急劇減少甚至達到無人在船,船舶的航行主要依靠岸基遠程操控,甚至自主航行。這種根本性的變革可能會導致現行公約、規則架構無法滿足要求,比如:
1、在一些公約、規則中,船舶本身的定義可能會不再適用。與船舶相關的諸多角色,如船長、輪機長等船員的概念可能會發生本質的改變;從船旗國有關商船的法律法規角度上看,無人智能船是否會在登記、注冊等方面遇到困難?如何定義船的“船長”?是主要的遠程操控者,是航行程序的編制者,還是一個不直接對船舶操控的被授權人?遠程操控者是否會被定義成“船員”?海商法將來會對無人智能船授予什么樣的權利?如是否給予自由航行權、通行權等當前船舶目前擁有的權利?
《聯合國海洋公約法》中對船舶沒有明確定義,公約第91.1條規定,“每個國家應確定對船舶給予國籍。船舶在其領土內登記及船舶懸掛該國旗幟的權利的條件。船舶具有其有權懸掛的旗幟所屬國家的國籍。國家和船舶之間必須有真正聯系。”目前業界普遍認為無人智能船被認為是船舶,無人智能船和船旗國需履行與當前船舶相同的義務和權利。
2、由船舶機海損事故導致的民事責任劃分將變得有爭議,原本在公約、規則中清晰的責任界線是基于現行公約定義的運營公司、操船人員等概念劃分的。當一艘配備完全符合自動駕駛和避碰系統要求的船舶出現了機海損,責任誰來承擔?船東、岸基遠程操控人員,還是無人操控系統的制造商?
3、由于在船舶設計方面可以逐步不再考慮人的因素,船舶的結構會發生根本變化,供人居住的艙室,及其相應的通風、空調、排污系統也會減少或者消失,因此與防火結構、各類報警、救生設施,防污染設備(如生活污水處理裝置)、艙室的舒適度等諸多要求相關的公約、規則會有所變化,這將對適用于當前船舶的技術法規架構產生影響,下文就具有代表性的公約進行舉例說明。
(1)對現行《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產生的影響
《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簡稱SOLAS,共計12章。它是為保障海上航行船舶上的人命安全,在船舶結構、設備和性能等方面規定統一標準的國際公約。根據公約規定,各締約國所屬船舶須經本國政府授權的組織或人員的檢查,符合公約規定的技術標準,取得合格證書,才能從事國際航運。
從第I章“總則”第1條“適用范圍”和第2條“定義”來看,無人智能船與SOLAS公約的要求不抵觸。同時公約也是靈活的,給出了公約免除條件,如第4條(b)規定,“對于具有新穎特性的任何船舶,如應用本公約第II-1章、第II-2章、第III章和第IV章的任何規定可能嚴重妨礙對發展這種特性的研究和在從事國際航行的船舶上對這些特性的采用時,主管機關可予免除這些要求”。當然,免除的詳細資料和理由提交國際海事組織以分發給各締約國政府,供其參考。無人智能船可以考慮為一種新穎特性的船舶,因此有可能享受到公約相應章節的免除特權。
同時,公約各章節考慮到了船舶及營運的客觀條件、新技術的產生及應用,提出了免除條件、替代設計和布置。免除或等效替代無人智能船上的相關設施配備布置可參考國際海事組織發布了MSC.1/ Circ.1212通函“關于替代設計和布置指南”。
在SOLAS公約對無人智能船適用性研究過程中,有兩個關鍵性的內容需要注意:
(a)公約中涉及到對“在船人員”的工作程序要求。包括但不限于應持有的必要資料、應遵守的工作程序、應承擔的相應義務等。
例如II-1章“構造-結構、分艙與穩性、機電設備”第5-1條“向船長提供的穩性資料。應將主管機關同意的必要資料提供給船長,以使他能用迅速而簡便的方法獲得有關各種營運狀態下船舶穩性的正確指導。”同樣的還有第19條,“需要提供破損控制圖給高級船員……”。第VI章“貨物和燃油運輸”第2條“貨物資料”:“托運人應在裝貨前及早向船長或其代表提供關于該貨物的相應資料……”類似的資料應該提供給誰?是否無人智能船岸基遠程操控人員可以像前文提及的等效為“船員”而必須獲取這些必要資料?
同樣,而對于II-1章要求引起值班輪機員或其他相關人員注意的報警并采取相應措施,如第38條“輪機員報警裝置”,第51條“報警系統”,第53(4)“自動控制和報警系統”以及第37條“駕駛室與機器處所之間的通信”。這些條款都應該依據55條“(機電設備)替代設計和布置”考慮進行等效設計,比如報送給岸基遠程操控人員,同時要求岸基遠程操控人員可以對報警做出反應,并給出相應措施。
對于II-2章“防火、探火和滅火”第15條“指導、船上培訓和演習”及第16條“操作”關注了船上訓練和操作,目的是使在船人員在失火時候船舶可以處于可控狀態。本章等效替代可能有些挑戰性,比如需要建立岸基遠程操控人員對火災應對的相應程序,如何遠程有序操作滅火系統達到有效的滅火效果,這些都是值得探討考慮的問題。
而涉及到義務,尤其是人道主義救援義務時,無人智能船面臨著更大的挑戰,按照第V章“航行安全”第33條“遇險情況:義務和程序”要求,“處于能提供援助位置的船舶船長在收到來自任何方面的關于海上人員遇險的信息后,有義務立即全速前往提供援助,如有可能并通知遇險人員或搜救機構,本船正在全速前往援助中。不論遇險人員的國籍或身份或其被發現時的狀況,均適用此提供援助的義務。”在《聯合國海洋公約法》第98條“救助的義務”中也規定了“每個國家應責成懸掛該國旗幟航行的船舶的船長,在不嚴重危及其船舶、船員或乘客的情況下:(i)救助在海上遇到的任何有生命危險的人;(ii)如果得悉有遇難者需要救助的情形(在可以合理地期待其采取救助行動時)應快速前往拯救;(iii)在碰撞后對另一船舶及其船員和乘客給予救助,并在可能情況下,將自己船舶的名稱、船籍港和將停泊的最近港口通知另一船舶。” 無人智能船由于其自身結構特點以及救生設備的配備狀況決定其本身不具備良好的救援條件,無人智能船是否可以船上沒有人員作為拒絕執行全速救援遇險船舶的義務?是否有替代性解決方案?
(b)公約中涉及與“在船人員”相關的船舶結構設計以及設備性能及其安裝布置要求。
由于船舶的無人化,很多公約要求安裝布置的船上的設施將不再適用,或者需要等效設計和布置以滿足要求,例如II-2章“構造-防火、探火和滅火”第7條“探測和報警”:“符合《消防系統安全規則》的手動報警按鈕應遍布起居處所、服務處所和控制站。每一出口都要裝有手動報警按鈕點。”而第III章“救生設備和裝置”,對于無人智能貨船來說,整章有可能不再適用。第V章“航行安全”中和駕駛臺的設計相關的第15條“關于駕駛臺設計、航行系統和設備的設計和布置以及駕駛臺程序的原則”以及第22條“駕駛室可視范圍”則需要考慮等效替代,當船舶既可以在船操控也可以遠程操控時,遠程操控人員是通過設置在陸地上的電子可視化的駕駛臺進行操控,船舶周圍的信息可能會通過高精度音視頻獲取裝置實時傳輸至岸基控制中心,通過如虛擬現實等新技術呈現于岸基操控人員面前。因此應考慮到等效替代的設計能夠滿足公約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當公約中要求人員需要立即做出響應措施時候,比如立即執行滅火指令,從自主操舵轉為人工操舵等等,應充分考慮船岸通信以及船舶指令執行的可靠性。比如當岸基操控人員發出啟動固定式滅火系統等關鍵指令時,或當岸基操控人員通過船舶周圍信息再現系統發現需立即采取應對措施時,應考慮到船岸通信或者執行系統失效。畢竟在現有船舶上,這些指令可以很快執行并附有應急方案,而遠程操控船舶有可能會面臨由于惡劣天氣等原因而導致通信延遲故障,進而引發重大財產損失。
(c)公約中涉及“人員配備”的要求。
公約第V章“航行安全”,第14條“船舶配員”要求:“各締約國政府承擔義務,各自對本國船舶保持實行或在必要時采取措施,以確保所有船舶從海上人命安全觀點出發,配備足夠數量和勝任的船員。”從安全角度出發,船舶要求最低配員。需要關注的是最低配員的要求會不會阻礙無人智能船的發展,因為從定義上說,無人智能船就是無人在船。另一方面,如果認為陸地上的岸基操控人員也是船員的話,存不存在最低配員的概念?在智能船的發展過程中,船員是逐步減少直到無人在船的,安全配員的要求是個值得關注的方向。
(d)公約中涉及到“海上保安”的要求。
公約第XI-2章“加強海上保安的特別措施”用于應對威脅船舶或港口設施或任何船/港界面活動或任何船到船活動保安的任何可疑行為或情況。應當考慮到,當船舶發展至無人化時,對船舶的入侵將變得形式多樣,比如從技術角度來說,通信與控制網絡具有受到黑客惡意入侵的可能性,船舶會受到非法控制,帶來巨大的保安風險。
(2)對現行《國際海上避碰規則》產生的影響
國際海上避碰規則,簡稱COLREG,是為防止、避免海上船舶之間的碰撞,由國際海事組織制訂的海上交通規則。規則中的“船舶”的定義為“指用作或者能夠用作水上運輸工具的各類水上船筏,包括非排水船筏、地效翼船和水上飛機”。因此,無人智能船是適用于該規則的。規則第2條“責任”中則做了如下說明:“在解釋和遵行本規則條款時,應充分考慮一切航行和碰撞的危險以及包括當時船舶條件限制在內的任何特殊情況,這些危險與特殊情況可能需要背離本規則條款以避免緊迫危險”。這里強調了必要時的人為介入。類似的還有第5條,“每一船在任何時候都應使用視覺、聽覺以及適合當時環境和情況的一切有效手段保持正規的望,以便對局面的碰撞危險做出充分的估計。”這兩條都強調了人的作用,即在遵守這個規則的前提下,也要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加以良好的經驗進行判斷,從而避免碰撞。可以想象完全遵守避碰規則、利用先進避碰算法進行自主航行的船舶并不能滿足規則的要求,這對完全自主航行的智能船來說是個非常大的挑戰。對于岸基遠程操作的船來說,則需要考慮等效的設計,例如利用先進的聽視覺技術獲取船舶周圍的信息遙控船舶,是否可以滿足規則的要求?
對于避碰規則中對號燈、號型的要求,則應充分考慮到無人智能船的特殊性,比如是否應該為這種船型設置單獨的信號燈,用于指示其特殊性以及工作狀態是否異常,比如是否通信正常等,以使得其他船舶了解到其工作狀況,以做出相應的措施。
(3)對現行《海員培訓、發證和值班標準國際公約》產生的影響
《海員培訓、發證和值班標準國際公約》是為統一各國的海員培訓、發證和值班標準,以確保海運船舶的航行安全而制定的國際公約。公約中定義的“值班人員”對于無人智能船來說則是有著微妙意義的,無人智能船的運行并非完全無人“值守”,遠程的監控、操作運行也是一種變相的值班,而且由于高度的智能化可能會導致人均操控船舶的數量大大提高,當一艘甚至多艘船舶出現緊急情況需要人員介入時候,可能使操作員的產生巨大的精神壓力,進而做出不當抉擇產生巨大損失。因此,現行公約完全可以作為新的資格制度的藍本,用于制定無人智能船的“操作員”行為準則。
海事界積極行動
當前,國際海事組織制定有超過50個有效的公約、規則供全球締約國所使用,這些公約和規則都是締約國必須遵守的。同時,這些公約、規則同時會轉換為各締約國航運業的法規。智能船舶的發展必須要有公約、規則的支撐,從上文簡要的分析可以看出,針對智能船適用性帶來的公約、規則的修訂將會是一個復雜而又龐大、甚至顛覆性的工作。
多個國家已經深刻意識到智能船舶的發展亟需配套的公約、規則支撐,由丹麥、愛沙尼亞、芬蘭、日本、荷蘭、挪威、韓國、英國和美國九個國家共同提出“海上自主水面船舶(MASS)監管范圍界定”,以期海安會第98屆會議批準為新的工作計劃。丹麥等提案建議對IMO文書進行法律監管范圍界定,以識別出當前正在起草的“排除無人操作的IMO規則、不適用于無人操作的IMO規則以及雖未排除無人操作的IMO規則,但需要進行修正以便確保MASS的建造和操作是以安全、安保并環保方式進行”。歐洲至少還有兩個團體正在研究修改法規以適應無人智能船的發展,其中一個是歐洲無人海事系統的安全和規章小組,由瑞典和其他六個國家共同組成。另一個是英國的海上自治系統監管工作組。他們的目的是確保《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在下一次更新迭代時,能夠反映新技術的發展。
中國船級社一直致力于智能船的研究工作,我們已于2015年作為國際上第一家船級社發布了《智能船舶規范》,同時成立專門的項目組應對智能船的發展,這其中包括公約、規范對無人智能船適用性的專項研究。我們力圖在將來公約、規范的修訂過程,充分考慮我國船舶工業發展水平,引導和促進國內智能船舶技術的有序健康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