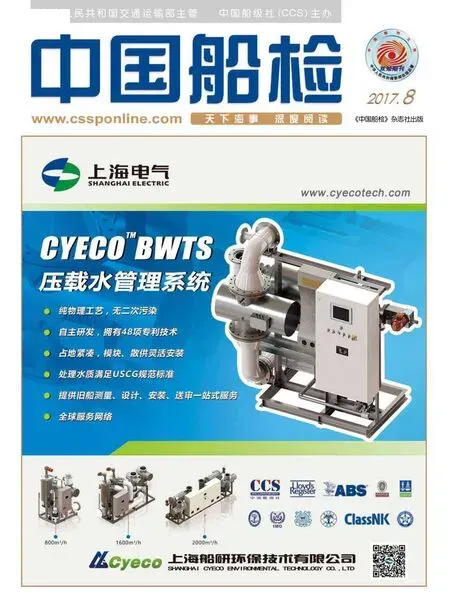建設海運強國面臨的挑戰
建設海運強國面臨的挑戰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海運發展取得了很大成就,海運保障性、競爭性和引領性顯著提高,世界海運大國進一步鞏固。當前正處于形成海運強國實力的沖刺階段,這一階段主要任務就是提升海運六大內部發展要素水平,構筑完善四大發展環境,也是為到2040年成為世界公認海運強國奠定新基礎的關鍵階段。這一階段海運發展依然面臨嚴峻挑戰,從實現海運強國實力的外部效果看,挑戰主要表現為:面對復雜地緣政治形勢日益凸顯的國際環境,暴露出在應對各類突發事件中海運保障性面臨的挑戰;面對海運新一輪漫長低谷調整,暴露出企業經營大幅波動、可持續發展面臨的挑戰;面對國際規則新一輪調整,暴露出我國話語權和影響力提升面臨的挑戰。從實現海運強國所需發展環境看,挑戰主要表現為面對新一輪海運調整和變革,如何構筑我國海運發展生態圈?
海運保障性依然薄弱
隨著國家經貿地位的提升和海運業綜合實力的發展,海運船隊綜合運輸能力顯著提高,進口石油等物資比重不斷提高,港口吞吐能力適應性實現適度超前,支持保障系統顯著改善,但面對復雜地緣政治形勢日益凸顯、國際形勢復雜多變的發展環境,特別是一系列事件給我國海運保障性提出諸多挑戰。
一、海運控制力弱。一是對重要海運通道影響力小,作為海運需求第一大國而非軍事強國,相對其他經貿和海運大國,在馬六甲海峽、巽他海峽、龍目海峽、蘇伊士運河、霍爾木茲海峽、曼德海峽、巴拿馬運河和蘇伊士運河等國際海運咽喉要道地區影響力有限,無法與其他大國達到均衡,對維護這些要道的安全、自由通航貢獻尚十分有限;二是缺乏全球海運網點支持。自大航海至二戰結束,全球海外重要島嶼被列強瓜分完畢,通過長期發展已經形成其綜合基地,以有效應對各類突發事件。由于歷史上長達100多年的積貧積弱,我國沒有像美國、英國和日本等在海外擁有島嶼,難以適應應對復雜形勢對海運支持保障的需要。如索馬里護航中海軍后勤保障、馬航370事件中的搜尋救助支持暴露出的問題;三是通江出海通道尚待完善。瀾滄江、圖們江、鴨綠江和黑龍江為我國四大重要通海、通航國際河流,由于種種原因,尚未形成通向泰國灣、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的海上通道;四是航運控制權有待提高。我國是海運需求第一大國,但出口主要是FOB、進口主要是CIF,控制權弱,既不利于在價格機制形成中維護自身利益,也不利于將自身海運需求轉化為海運發展動力。
二、國防安全船隊、經濟安全船隊保障性能有待提高。一是缺乏國防安全船隊建設計劃,雖然各類海運專業船舶齊全、規模龐大,但大多基于運輸功能、靠泊碼頭進行裝卸進行設計,沒有定向軍民融合,在國家安全事務中只能用于后勤運輸保障,難以適應非常態突發事件對海運的需求。二是海運船隊規模相對較小,占世界運力比重低于需求比重6個百分點,經濟保障和海運自身利益與海運需求規模不相稱,例如進口原油比重雖逐步有所提高,2016年也僅僅達到28%,仍遠低于原2010年預期50%的目標水平,更低于日本三分之二的承運比重,2012年伊朗石油運輸問題暴露出我國海運運輸以及相關保險能力的脆弱。
三、支持保障系統裝備水平需要提高。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海上支持保障系統裝備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但針對維護我國海洋權益新形勢,救助打撈系統仍難應對非常態突發事件、遠海搜尋救撈和深海防范的要求。馬航370事件更是直接暴露出我國在遠海海上搜尋、救助和深海打撈的差距。
海運國際競爭力有待提高
國家海運業競爭力主要通過參與國際海運競爭的海運企業、碼頭公司和港口城市體現(爭奪國際航運中心)。在本輪海運市場高峰和“中國因素”的歷史機遇背景下,我國海運業在品牌建設上取得顯著成績,提升了國際競爭力。但也暴露出海運服務貿易逆差擴大、海運市場調整中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不足,迫切需要提高創新能力和持續盈利能力。
海運服務貿易出口快速增長,但逆差不斷擴大。隨著我國海運業的快速發展,我國海運服務貿易出口由2000年的16億美元增長到2010年的229億美元,年均增長30%,和其他經貿大國海運服務貿易出口差距逐步縮小,同期由相當于日本、德國海運服務貿易出口的9.5%和21%上升到71%和55%。但同時可以看到,日本海運服務貿易由逆差逐步轉為基本平衡,出口占進口比重由2000年的80%上升到2014年的95%,德國同期由85%上升為134%,實現由逆差到順差的轉變。而我國海運服務貿易逆差呈現持續擴大態勢,由2000年的45億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264億美元,2012年進一步上升到近600億美元。
企業經濟效益大幅波動,可持續發展能力面臨挑戰。在跌宕起伏的海運市場競爭中,企業的持續盈利能力是其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重要體現。從2005年~2015年累計經營效益看,我國海運企業整體盈利能力不強,同時經營效益大起大落、持續盈利差,暴露經營上的巨大風險和應對海運市場危機能力弱。
國際航運船舶流集聚規模居世界前列,國際航運信息流、資金流集聚規模任重道遠。我國先后提出上海、天津、大連和廈門國際航運中心建設目標,其中上海國際海運中心建設成就最為顯著,依托需求規模優勢,船舶流集聚規模達到世界前列,航運和相關機構集聚規模顯著提高,但在城市綜合環境、海運基礎服務、海運信息和海運金融等服務領域依然存在較大差距。
海運發展引領性亟待提升
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和海運事業的發展,作為世界海運大國正日益廣泛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為維護世界海運秩序和促進海運發展做出的貢獻顯著提高。但在維護世界重要海運通道安全作用有限,在世界海運相關組織任職人員少、層次低,重要海運規則與主要技術標準仍然處于跟隨狀態。
國際重要海運通道安全通航影響力弱。一方面是自大航海到二戰,世界發達國家基本將海上戰略要點瓜分完畢,而我國走出去發展時間很短,全球海運網點少;二是作為發展中國家,綜合國力依然潛力巨大,在維護世界重要海運通道安全通航的能力有限。
在世界海運規則、技術標準制定和海運服務創新方面作用不強。海運是技術和資本密集的行業,也是一個傳統行業,歐美依托綜合國力優勢,具有很強規則執行能力甚至單邊執行能力,倡導組織成立了相關國際海運機構;依托文化、技術和人才優勢,在規則和技術標準研究擁有良好的機制,鞏固了其規則制定能力、議程設置能力、輿論宣傳能力和統籌協調能力等,當前重點集中于環境保護、安全航行和反恐,我國以及亞洲國家長期處于跟隨狀態;依托長期磨合、積累形成的海運文化、人才和技術優勢,大量海運技術和服務創新基本由歐美完成,引領世界海運技術和服務發展趨勢。
參與國際海運相關組織水平不高,區域國際海運組織建立、作用成效不大。作為最古老的海運業,至20世紀80年代國際海運相關組織由歐美主導基本建成,構成了當今世界海運治理體系,后發國家只能謀求在已有組織中發揮作用,維護自身的話語權和海運利益。依托海運發展取得成就,我國在國際海運相關組織地位不斷提高,但缺乏有效持之以恒人才培養、輸送機制,人員參與少、關鍵部門中高層任職人數少的矛盾依然突出,議程設置能力、輿論宣傳能力和統籌協調能力等存在較大差距,即使和周邊國家相比也存在差距,如印度、日本和韓國均已成功推舉本國候選人當選IMO秘書長。我國雖然努力推進亞洲國際海運相關組織的建立,以抓住海運發展中心向亞洲轉移的機遇,但成效不大。
參與規則制定機制有待完善,提案少、質量不高和被采納少的問題依然存在。由于整體技術、經濟和人才實力的差距,加之缺乏統一的參與機制,我國在規則制定、規則執行和統籌協調等方面與海運大國地位不相稱,提案數量、質量和歐美存在較大差距,近幾年平均提案數量也只有日本的30%、韓國的75%,在世界重要海運規則、技術規則制定中仍是跟隨狀態。
建設我國海運生態圈迫在眉睫
由于上一輪海運高峰引發船東瘋狂造船,加之世界經貿結構性調整,海運量的需求增長放緩,海運市場處于新一輪漫長調整;隨著人們對氣候變化和對生態環境的重視,海運規則正在向環境保護、安全運營和海員體面工作的方向調整;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不斷與海運服務各個環節深度融合,引發新一輪海運服務的創新。新的發展環境,迫切需要形成新的海運發展生態圈,探索中國特色海運強國建設模式,有效整合海運發展要素的優勢,形成核心發展能力。當前推進海運生態圈形成過程主要面臨如下三個方面的挑戰:
一、提升國民對海運的認識,營造發展海運共識。由于歷史上長期形成的農耕文化和“海禁”政策,也沒有像西方曾從航海戰略獲取巨大財富和大量海外國土的感受,加之海運也遠離人們的日常生活,使得國民對海運在國家安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雙重作用缺乏基本認識,即使像中國航海日公告這樣的文件中,也缺乏類似對海運、海員作用的基本描述,這一認知缺陷是我國構筑海運經濟政策長期面臨的挑戰。基于新的發展形勢,國家明確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和海洋強國戰略,海運強國也于2014年由行業戰略上升為國家戰略,應抓住這一機遇加強海運文化建設,逐步提升國民對海運的認識。
二、創新海運經濟政策,完善海運法律體系。海運的技術經濟特性決定了其“好日子短,苦日子長”的市場波動特點,投資海運長期回報低于資本平均回報,而海運又是關系國家安全、經貿發展的產業,因此,世界海運大國都制定了以稅收為基礎的海運經濟政策,促進海運可持續發展。我國參照全球主要海運國家慣例,研究建立有利海運的經濟政策,當前主要是海員所得稅和國際海運噸位稅制。根據我國海運發展需求和國際規則調整,完善海運相關法律法規。配合國務院法制辦開展《海上交通安全法》《海上人命搜尋救助條例》《潛水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審核修改工作、推動《海商法》修改進程,開展《港口法》實施評估和修改的前期研究,加快《國際海運條例》的修訂工作。
三、促進產業和企業協調發展,構建互動機制。與其他海運大國相比,海運需求第一大國和產業鏈完整是我國獨有的優勢,在改革開放早期面臨能力不足、投資收益高的背景下,各個行業單獨發展均取得了顯著成就。隨著市場供求關系的轉變,各行業均面臨跨界發展和融合發展需求,推進海運業與上下游產業、相關政府部門、社會組織及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互動發展機制,形成良性的海運產業生態圈,并以此構筑核心能力、參與全球競爭,從而充分發揮中國海運產業完整的優勢。一是根據海運業的經濟技術特點,開發符合市場規律的定制化金融服務、基礎設施投融資模式,降低金融風險和金融成本;二是加強原油、煤炭、鐵礦石等大宗物資進口和制成品出口海運權益控制,努力實現貨主、金融保險和海運企業共同參與商務談判,鼓勵我國貨主企業提高出口CIF、進口FOB合同比重,提高全程供應鏈管理能力;鼓勵與海運企業形成長期合作關系,簽訂長期包運合同。建立船舶建造、海上運輸、船舶檢驗以及金融服務機構合作機制,提高特定航線特色船舶建造技術經濟特性,為提供優質服務、降低成本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