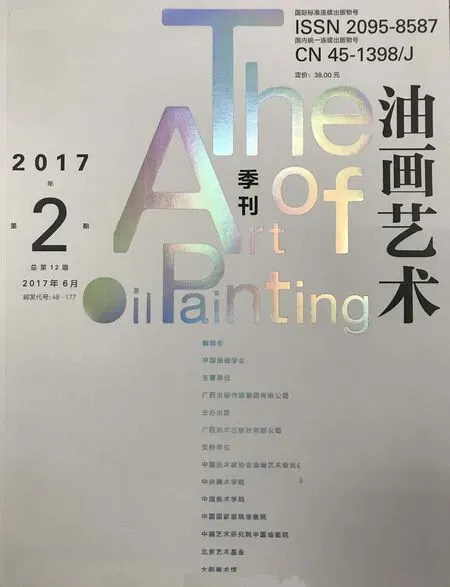沉醉于繪畫的快感—對話李強
李強
采訪人馬文婷
地點:四川美術學院虎溪公社 時間:2014年11月
馬文婷(以下簡稱“馬”):看到你最近的這批作品,我覺得盡管仍然延續了你這么多年來一直描繪的主題,但是當我們仔細去體味畫面細節的時候,還是會發現無論從繪畫方法或者構圖方式上,都和以前的作品拉開了一些距離。
李強(以下簡稱“李”):幾年前我在畫“返境”系列的時候,出發點是基于我對傳統文化的一些表達的愿望,所以說傳統格局或者說“訪古”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還記得當時畫室里到處都擺滿、貼滿了傳統國畫的畫冊和圖片,是因為我希望每一招每一式都是借由這個母體生發出來,通過我今天的筆端去對照一種古人的大的精神意境。但是后來我漸漸地失去了最初的新鮮感,覺得如果再做下去的話意義也許就會被凝固,很難再推動了。
我經常在想當你的繪畫系統越來越完善,當你已經完全知道如何去呈現一個結果的時候,這時恰恰就失去了挑戰,不知道該怎么辦了。當你技術越來越熟練,別人越來越喜歡的時候,我卻發現自己的繪畫漸漸失掉了最初的吸引力,開始變得習慣并且復制自己,工作就會變得無趣,甚至會越來越懷疑繼續工作下去的價值。同時我也發現回溯傳統的藝術家越來越多,甚至成為藝術圈的一種流行的時候,我便對這個出發點產生了一種懷疑,對這種文化普遍現象保留了一份警惕。所以從前年開始,我便有意識地讓自己在創作的過程中游離出這個已經固定下來的思路,去尋找更多表現的可能,有時候過去的東西雖然也很難完全甩掉,但是我總是希望在這個過程中去反復地提醒和調整自己要和過去習慣的很多東西錯位,去努力尋找這種錯位的點該怎么設置。
馬:對,實際上呈現的同時也會伴隨著對自我的推翻和顛覆,在這個過程中總是會對自己不滿意,一直想不斷地去追尋意義之上的意義。現在對你來說,和傳統的關系緊不緊密已經變得不再那么重要了,我覺得你現在的畫面從視點的游移到環境的營造,已經脫離了傳統國畫式,或者真實生活,感覺更像是你心中的風景,介于真實和游離之間。李:其實一直以來我都想和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走著走著,我突然發現經過這么多年的探索之后,似乎又回到了我一開始畫畫的那個狀態,在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年輕的時候那些很單純的愿望——為什么喜歡畫畫,畫畫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這類問題突然是那么重要。這促使我不斷地去調整自己面對花卉這個熟悉題材的感受,現在它已經更多地成為我寫意筆墨的或者說繪畫手感的一個載體。
馬:這次展覽的名稱叫作 “藉境離景”,似乎和一些禪宗的術語有所淵源?我的理解是它其中還是暗含了一種中國式的精神,我覺得幾千年來傳統典籍中的很多說法,大家現在在字面上都不經常說了,但是仔細想想道理上或者說骨子里還真描述得非常準確。
李:我希望它能和我現在的工作狀態有一個對照,這是這個展覽名稱的初衷。也就是說實際上現在在我心目中越來越看重的是一種觸感,以及所謂精神承載的那部分東西,題材對我來說反而不那么重要了,這樣的體驗過程,使得我今天在放下一些東西的同時又撿起了一些東西,也許我已經找到了與“返境”不同的場域吧。
馬:我想當你在乎繪畫手感的時候,就會去在意筆觸在畫面上留下的痕跡,這些痕跡會促使你不斷去平衡它們在畫面上的位置,這就形成了一種和畫面之間非常具體的對話,你在說的同時,也在看畫面的反應。這恰恰能夠使藝術家進入一種特別真實具體、可觸可感的狀態。有的時候我也經常會陶醉于某一個具體細節的完成,或者是為某個地方完全的一籌莫展、痛苦焦慮,所以我特別迷戀繪畫的過程,我覺得這也正是畫畫這個工作最吸引我的地方。
李:是的,有的時候我面對一張空白的畫布可以一想想好幾個月,有時候在畫這一張的時候腦海里就已經不斷地又去醞釀下一張畫。其實,我覺得這種對畫面的反復試煉與尋找,是每個畫家都逃脫不了的一個重要體驗。這個過程往往追尋的還不完全是畫面效果,而是能否讓我獲得那種與畫面真實對話的觸感。有時候,往往就那么一點點小小的體會,甚至是一個很小的不為觀者察覺的細節呈現,都能讓我非常興奮。
馬:有的時候來看你的畫,經常都是前一晚上畫得特別酣暢淋漓的畫面,第二天一來全部都刮掉了,我覺得很多好的地方都消失了,但是又有很多好的地方出現了,你的畫經常要覆蓋很多遍層次,這是不是尋找繪畫觸感的一種方式?
李:可以算是吧,我覺得現在對每張畫面的要求總是在不斷變化著的,最終的結果也是在過程中慢慢自然成型的。我覺得作為一個畫家要做到的東西有很多,但是至少這種交流和觸碰在我看來很重要,不然的話我覺得繪畫語言很容易慢慢就會變成一種樣式化的東西。
馬:對,我覺得最害怕的就是畫著畫著自己就麻木了,這個肯定是需要不斷去明確和提醒自己的,也確實很難,因為每個階段遇到的問題都很具體,是很不一樣的。回想你這些年的作品,從一開始的“天堂”系列,到后來的“現場”“返境”,這樣一條線索下來之后,在這個過程中要不斷地選擇一些東西、放下一些東西,一直到最近的這批,看似放下了很多東西,但是這個“放下”本身也是很難的,是一個價值判斷的問題,不是一開始就做得到或者是能放得下的,每個人都要在這個過程中去慢慢尋找。
李:其實每個人都有選擇,每個人對自我的要求和選擇都不一樣。之前我畫工廠,畫災難現場,后來畫“返境”,是因為當時我的腦袋里每天都在想這些問題,而且和我個人的生活也有一定的關系,特別是親人的病痛生死讓我對生活有更多的體會與領悟,生活的變化真的會讓你不自覺地就要去想這些問題。但是后來我發現其實繪畫是承載不了所有宏大的終極問題的,也不能直接去解決任何問題,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越來越覺得繪畫最初的出發點是非常重要的。繪畫不僅僅是去簡單地反映問題、表達問題,而是應該更深入地和問題下的自我對話,找到這個自我的位置,這個可能也是今天的這個藝術現場帶給我的觸動和改變。
馬:這次展覽中有一組全部是由小畫組成的作品,和其他作品的氣息有些不一樣。這令我聯想起了2008年你畫的“大象日記”那組作品,它們之間有聯系嗎?或者有何區別?
李:我覺得這組小畫可能更像是一個狀態記錄,有些是非常日常的生活瞬間,本身也并不特別,被我隨手抓拍來的,它和花有一定的聯系,但是由于題材的豐富性,尺寸又小,繪畫的空間和隨意性就非常大,可以去體會更多的效果和語言上的變化,也是一種不一樣的工作方法,就是不停地畫,沒有預設地畫,然后最后來看看怎樣把它們歸置在一塊兒,這也讓我在巨大的工作量之間獲得了一些輕松愉悅的瞬間,算是一種調節。這個和我畫色粉風景的愿望也是一樣,希望通過一些技術、尺幅和內容上的轉變,來試圖和大畫在效果上拉開一定的距離,破一破自己多年來比較習慣的這種繪畫手感。
馬:如果做一個串聯,我覺得之前這幾個系列的作品對你思想上的變化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在思考問題的時候,往往會有一個宏大的構建,這個本身并沒有問題。但是對于一個藝術家而言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把這些構建通過自己的畫筆和內容傳達出來,或者說在一個階段之后,去思考這些構建還能不能夠或者說合不合適你的表達。這個思考和調整的過程,一方面是在選擇和放棄,一方面又會迫使自己不斷去尋求新的可能性。今天這個世界越來越豐富,同時個人的場域又越來越狹小,就使得大家在這樣一個場中都要不停地向自己進一步追問,去不斷挖掘和尋找自己的需要。
李:之前的幾個階段對我來說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在一個大背景下逐漸變化的過程,說到變化,我覺得最大的變化就是我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拋棄了很多對我來說是累贅的,或者說是無關的東西。我在畫這批畫時腦海中總有一些不確定和不可知,有些是刻意要求自己要回避以前的繪畫習慣,有些又是在過程中自然產生的。由于你不知道和沒安排,在創作的過程中,畫面其實就記錄或者保留下了那么一點點殘留,這其中包含了你在這個過程中所有的糾結、探索和成敗,但是正是這些因素才使得畫面在最后能夠呈現出來其本身的生命力和鮮活感。我覺得我們談“精神性”這個東西是很難說清楚的,它有時候就是一種感覺,而這種感覺又是很難用語言和觀念去描述的。雖然我還是以花卉和風景為主題,至少對我來說,我現在再面對對象時的愿望和方式跟以前已經有些不一樣了。
馬:是的,我們有的時候經常會把問題想得很大,但是最后畫完了再坐下來看看時,好像總覺得有些表達上面的誤差,有些東西并不是很能恰如其分地傳達出來,可能總會存在一些轉換上的差異,也許是來自你的內容、技法是不是合適,是需要放棄還是轉換,或者是其他什么東西,總之這個思考過程和結果呈現的不對稱經常是一個很大的困擾。
李:就這個問題而言,任何時代的藝術家在藝術現場中都將面臨對自己的位置和方向的選擇。選擇沒有問題,但是我想說作為一個畫家來說,其實他在畫面上能解決的問題可能就只有那么一點點,因為畫畫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具體的過程,它是一個整合的有機體,方方面面的,跟你所有具體的生活,每個階段的人生狀態都是連為一體的,很多太大的東西往往無法落實在具體的點上,有時候反而從一些小的、具體的東西出發,才更容易讓自己明確下來。
馬:繪畫和其他媒介一樣,都會面臨語言和思想之間有效溝通的問題,只是繪畫似乎要更復雜一些,更加難以把握。愿望和需要是沒有高低對錯之分的,如果說當代是一個大的復雜的場域,那么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領域和位置,你可以不斷變化,也可以堅持自我。當然作為現實場域中的自我也是在時時流變的,肯定還存在著語言有效性的問題,這是無法回避的。
李:實際上每個人都在變,在不斷變化的過程中,自我也是在不斷變化和充實的。我覺得繪畫永遠是視覺這一瞬間傳遞的一個東西,溝通也在瞬間。繪畫永遠有它自身獨特的東西,有它獨立存在的意義。那么如果繪畫過于套路化、流程化,就很難打動自己,也很難打動別人。當你缺少要求的時候,這就叫逃避了,你的這種堅持就叫逃避,你脫離現場,你開始回避問題了,你對自己不進行批判和研究了,這就得不斷地給自己提醒。
馬:我覺得現在你的整個狀態在轉變,似乎更愿意去跟一個真實的自己相處,接受自己所有滿意或者不滿意的東西,能夠坦然地去面對自我,知道要站在哪里,要往哪里走。這才是你最大的變化。
李:對自我的要求是必需的,一個人如果缺乏做事情的愿望,或者說任由一種慣性的愿望來支配是很可怕的。要變,就要推翻和懷疑,焦慮和痛苦是常態。哪怕在別人的眼中只是一點點的改變,對自己來說都會得到一些收獲和體會。只有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去反復,才能累積到一定的量,并期待一次更大的跨越。我畫面中的敗筆和疏漏也許旁人是根本無法看到的,但是它確實讓我獲得了以往從未獲得過的體驗,所以我說我整個畫花的系統,還有我整個設局的系統全變了。比如我們說到我畫的色粉風景,實際上這批風景就和我當時“現場”那批很不一樣,選擇的題材和場景以及我的愿望都不一樣。如果說以前可以算是“借物達意”的話,新的這批畫的意義我就想讓它顯得更模糊一些,并不希望它去傳遞一種非常明確的、可言說的東西。我的“返境”可以說得很清楚,我的“現場”也是。但是今天我真的說不出來。沒有一個明確的觀念或者說設置,完全沒有,就是體會,就是很多的繪畫觸感和在這個過程中不斷發現的那種新鮮的、不可知的誘惑感。
馬:我覺得這種東西它是不能用一兩句簡單的觀念就可以解釋清楚的,不像之前的系列可以用一套系統話語去描述它,分析它是怎樣產生和怎樣生效的。但是今天的這個東西它恰恰是一種精神上的交流和感受,這用語言是沒有辦法說清楚的。而且每個人在看到你作品的時候,都會有不一樣的體會,這恰恰是繪畫最有意思的地方。
李:其實對于繪畫精神的問題,我并沒有把它作為一個獨立的單詞來考慮,我覺得它一定是自然成型的,絕不會是抽象空洞或者說強加上去的,應該是通過一些東西自然流露出來的。對于一個畫家來說,畫面自身還能不能給畫家提供自由的空間和更新的可能性這一點是相當重要的,這也是吸引著你去不斷推進的一個重要的因素。最近這批畫我開始畫一大叢花,構圖不再遵循一種章法,筆墨也更加自由隨意,想以此給自己打開一個釋放的空間,在這個過程中將自己投入到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狀態中去。很多的遲疑也好,反復也好,當徹底放松之后,你會發現其實所面對的問題越來越沒那么復雜了,發現之前很多的糾纏都是一些并不重要的迷局。
我覺得撿起什么和丟下什么對現在而言是有意義的,但這還只是一個階段,并不意味著我已經“得道”了,每一個階段的推進永遠都是處在過程之中的,也許下一個階段的自己又會完全不一樣,在過程中就意味著得到的永遠是階段性的結果,而每個階段所得到的結果也并不一定需要它給自己帶來多么巨大的提升,只要一直保持著持續的生命力,一直努力去挑戰自己,我覺得這個創作狀態才是至關重要的。生活和藝術都需要主動,主動就會有要求,或者說有要求生活才會變得更主動。主動會幫助你不斷去尋找一些新的可能性,同時又在不斷推翻自己,這會使生活和繪畫都變成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哪怕在旁人眼中只是很小的一點點改變,對自己的意義都很大。我覺得現在這種狀態反而可以讓自己簡單起來,認清自己,知道自己要去向哪里,反而在畫畫時帶給了自己很多莫名的余地和空間,有的時候對了,有的時候又發現自己錯了,這種反復確定和追尋的過程帶給我太多繪畫的快感,同時也讓我獲得了很多不一樣的體驗。

李強《大象日記2016》30 cm×30 cm×36布面油畫2016年

李強《雪2016No.1》150 cm×200 cm布面油畫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