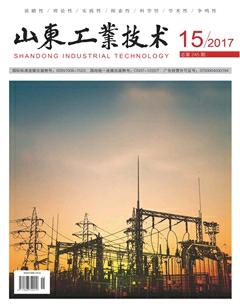解讀廣東省集中交易第一單
岑建軍++王夢瑤


摘 要:本文詳細(xì)解讀廣州電力交易中心完成的2016年首次電力集中競價交易過程。通過分析本次交易中的交易特點,并詳細(xì)模擬了本次交易過及電價形成過程,在對之后的廣東省競價交易新動態(tài)的對比分析后,得出電力市場集中競價交易的深度思考,并分析得出電力交易中的異常現(xiàn)象對交易對象心理造成的影響。
關(guān)鍵詞:電力交易;集中競價;申報價差;交易異常
DOI:10.16640/j.cnki.37-1222/t.2017.15.259
0 引言
能源革命的核心價值訴求是綠色低碳,節(jié)能優(yōu)先,加快形成能源節(jié)約型社會。在能源供給上,建立多元供應(yīng)、多輪驅(qū)動的能源供應(yīng)體系;在產(chǎn)業(yè)技術(shù)上,要緊跟國際新趨勢,以綠色低碳為方向,推動技術(shù)、產(chǎn)業(yè)、商業(yè)模式創(chuàng)新;在體制上,構(gòu)建有效競爭的市場結(jié)構(gòu)和市場體系,轉(zhuǎn)變政府監(jiān)管方式,建立健全能源法治體系。依法治國的重大決定強(qiáng)調(diào)“立法和改革決策相銜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據(jù)、立法主動適應(yīng)改革和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需要”[1]。立法是電改的頂層設(shè)計,沒有立法,就不能實現(xiàn)國家電力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xiàn)代化。
因此,新一輪電力體制改革方案,必須審時度勢,從推動能源革命和建立法治社會的戰(zhàn)略高度來進(jìn)行總體設(shè)計,必須緊緊扣住這兩個大背景、大前提,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認(rèn)清本輪電改究竟改什么,從而找到“順應(yīng)能源大勢之道”[2]。
據(jù)此本文主要針對電力體制改革配套文件重點內(nèi)容進(jìn)行解讀,并對電力體制改革文件的意義進(jìn)行了探討[3]。
1 新聞簡報
在國家能源局電力體制改革專欄中,改革動態(tài)專題中報道了“售電公司首次參與競爭交易 ,廣東成交電量68096萬千瓦時”消息,報道稱3月25日,廣東省內(nèi)36家發(fā)電企業(yè)與81家電力用戶在廣東電力交易中心開展了3月月度集中競爭交易。經(jīng)過3小時的報價后,出清結(jié)果公布。7家發(fā)電企業(yè)未能中標(biāo)電量,80家電力用戶最終成交,最終平均降價水平為0.125元/千瓦時。據(jù)悉,這是廣東省乃至全國范圍內(nèi)首次吸納售電企業(yè)參與的集中競爭交易,標(biāo)志著售電公司成為名副其實的市場主體。
據(jù)了解,廣東下月月度集中競爭交易將繼續(xù)根據(jù)各市場主體的申報電量,合理控制供需規(guī)模,實現(xiàn)有效合理競爭。
2 交易詳情
3月25日,廣東電力交易中心組織開展了2016年3月份集中競爭交易,集中撮合,競價規(guī)模為10.5億千瓦時,競價申報時間2016年3月25日10:00-12:00.其中 申報價差即(用電企業(yè)申報價-目錄電價)或(發(fā)電企業(yè)申報價-批復(fù)電價)
供應(yīng)方:共有36家發(fā)電企業(yè)參與報價,總申報電量為12.9767億千瓦時,異常報價剔除量為0萬千瓦時,其中29家最終成交,成交的發(fā)電企業(yè)平均申報價差為-0.429023元/千瓦時,其中最高成交申報價差為-0.2403元/千瓦時,最低成交申報價差為-0.500元/千瓦時。
需求方:共有81家用電企業(yè)參與報價,總申報電量為11.218億千瓦時,其中80家最終成交,成交的需求方平均申報價差-0.0243973元/千瓦時,其中,作為需求方的售電公司獲得較大收益,共9家參與,8家成交,平均成交價差為-0.151元/千瓦時,成交電量6.81億千瓦時,占總交易量的64.86%。
本次交易的售電公司主要包括廣東粵電電力銷售有限公司、華潤電力(廣東)銷售有限公司、深圳能源銷售有限公司、廣州恒運綜合能源銷售有限公司、新奧(廣東)能源銷售公司和深圳市深電能售電有限公司等8家在粵企業(yè)。
3 交易特點
3.1 交易時間臨時調(diào)整
交易規(guī)定時間原定為2016年3月25日9:00-11:00.但實際操作中出現(xiàn)了電力用戶不積極現(xiàn)象,未能按時填報交易需求電量。實際競價過程,由于對市場預(yù)料不足,為提高交易量,監(jiān)管部門和政府采取臨時不就干預(yù)措施,將時間推遲至10:00-12:00。
3.2 申報量上限臨時調(diào)低
按照交易規(guī)定,電力交易機(jī)構(gòu)應(yīng)提前發(fā)布發(fā)電企業(yè)集中競價允許申報量的上限。發(fā)電企業(yè)可以以此為依據(jù)確定競價電量的上限。此次交易過程中,在發(fā)電企業(yè)已經(jīng)按要求完成申報上限電量的情況下,臨時接到監(jiān)管部門和政府部門的通知,要求修改調(diào)低申報電量上限,一定程度造成發(fā)電企業(yè)的心里恐慌。
本次交易前,由于發(fā)電側(cè)總意向電量為17.3億千瓦時小于用電側(cè)總意向電量10.8億千瓦時,交易規(guī)模從14億千瓦時被臨時減少為10.5億千瓦時,導(dǎo)致發(fā)電企業(yè)競爭壓力較大。
3.3 存在非理性報價
發(fā)電企業(yè)在對用戶和售電公司期望的降價水平不了解情況下,臨時被要求降低報量水平也帶來了一定程度的恐慌,發(fā)電側(cè)出現(xiàn)了不理性的大幅降低報價水平以爭取市場的情況,表現(xiàn)為“純殺價”。有的發(fā)電廠最高成交申報價差達(dá)-0.5元/千瓦時,導(dǎo)致平均成交價差水平為-0.1255元/千瓦時的“血拼價格”。
此次競價結(jié)果創(chuàng)廣東省組織集中競價歷史里來的最高降價水平,成為全國范圍內(nèi)發(fā)電企業(yè)降價水平較高的省份之一。
3.4 交易規(guī)則存在缺陷
交易規(guī)則中引入價差返還系數(shù),申報價差電費差額按照3:1的比例返還給發(fā)電企業(yè)和電力用戶,在目前嚴(yán)重供大于求的情況下,此舉容易誘發(fā)發(fā)電企業(yè)在申報競爭電價時采取大幅降價以競量的僥幸心理。
在《關(guān)于明確2016年售電公司參與直接交易的通知》中的異常報價和踢出電量機(jī)制在此次交易中被暫停,發(fā)電企業(yè)少了‘報太低可能作為異常報價被剔除的擔(dān)心,整體讓利過大。發(fā)電側(cè)平均申報價差達(dá)-0.5元/千瓦時。
3.5 政府干預(yù)過多
從此次競價過程來看,仍然是政府控制供需關(guān)系和競爭強(qiáng)度的形態(tài),雖然名為“集中競價”,但實際還是大用戶直購的集中撮合模式,離真正的市場還有很大差距。endprint
4 模擬集中競價計算示例
假定集中競價交易規(guī)模上限為500萬千瓦時,發(fā)電企業(yè)申報電量上限按競爭直購電量的1.2倍計算。
4.1 申報數(shù)據(jù)
供應(yīng)方(發(fā)電廠)有5家參與報價,總申報量600萬千瓦時,最高申報價差-0.1元/千瓦時,最低申報價差-0.18元/千瓦時。需求方(電力用戶)共有7家參與報價,總申報量620萬千瓦時,最高申報價差-0.001元/千瓦時,最低申報價差-0.02元/千瓦時。具體申報見表1。
4.2 形成價差對(已按差值從小到大排列)
價差對(發(fā)電企業(yè)申報價差--用電企業(yè)申報價差)形成規(guī)則:
(1)價差對為零或負(fù)值時,按差值對小者優(yōu)先中標(biāo)。
(2)價差對為正值時不能成交;即用電企業(yè)與發(fā)電企業(yè)所出價格小于目錄電價或批復(fù)電價。
(3)若價差相同,按申報電量按比例分配或申報時間進(jìn)行優(yōu)先匹配。
4.3 集中撮合
(1)第1,2號價差對相同,成交電量按發(fā)電企業(yè)B,D申報電量B(均為96萬千瓦時)分配;D,B企業(yè)分別售出40萬千瓦時,用戶1購到80萬千瓦時,因用戶1購電量滿足。則與之對應(yīng)的15,16,17價差對自動失效。
(2) 第3,4號價差對相同,但電廠D,B剩余電量不足以滿足用戶2的申報電量,所以全部成交后,用戶2分別從D,B購得56萬,共112萬千瓦時,缺口8萬。此時與D,B相關(guān)的第5-14價差對自動失效。
(3)按剩余價差對撮合18,19,20.因為用戶2還缺口8萬千瓦時,所以成交分配按(C:A:E申報電量=216:96:96=9:6:6)分配。
4.4 撮合結(jié)束后,成交電量,成交價差
可以看出,由于報價策略不當(dāng),用戶7沒有獲得中標(biāo)電量;由于主要受規(guī)模控制的約束,ACE電廠和用戶6只有部分成交,反之,由于報價策略得當(dāng)BD和用戶1,2,3,4,5全部成交。
4.5 結(jié)算價格
(1)
(2)
(3)
其中為價差返還系數(shù),在本次廣州電力交易中為1:3。
5 深度剖析
5.1 交易評價
(1)廣東省作為電力體制改革試點之一,開創(chuàng)了售電公司進(jìn)入電力市場交易的首單,在售電側(cè)改革推進(jìn)過程中寫下濃重一筆。但在售電主體進(jìn)入業(yè)務(wù)實際操作階段,支撐售電公司業(yè)務(wù)開展的信息化支撐平臺成為市場化進(jìn)程進(jìn)一步推進(jìn)的迫切要求[4]。
(2)應(yīng)加快完善電力體制改革市場交易的競爭規(guī)范;降低相關(guān)政府部門過度干預(yù)。
(3)發(fā)電企業(yè)報價偏離正常價格價格過多,存在非理性降價行為,這是市場規(guī)則混亂和市場剛開始博弈混亂的結(jié)果。
5.2 市場異常行為對電力用戶心理影響
(1)電力信息平臺發(fā)布交易信息不及時或臨時變動導(dǎo)致用戶心理恐慌,出現(xiàn)不理性競價行為。如臨時調(diào)低申報電量上限,導(dǎo)致發(fā)電側(cè)出現(xiàn)了不理性的大幅殺價(心理群體整體智能低下定理)。
(2)電力用戶仍依據(jù)政府部門所提供的參考電價進(jìn)行報價(集中撮合),若購電大宗電力用戶(如售電公司需求量占60-70%)出現(xiàn)私下價格協(xié)商形成聯(lián)盟,容易使三大類交易主體中的大用戶(散戶)為了保證能競上中標(biāo),大用戶只能選擇跟隨售電公司的報價在市場形成盲目跟風(fēng)的羊群行為[5]。
(3)在交易供大于求的環(huán)境下,發(fā)電側(cè)(供方)為防止沒有中標(biāo)電量和確保最大申報量全部出清,發(fā)電申報提交最低成交申報價(-0.5元/千瓦時)是個大概率事件。而在此后的交易時,沒有成交的發(fā)電企業(yè)“吃一塹長一智”一定會殺價進(jìn)入,依此趨勢發(fā)電企業(yè)在電力競價中壓力山大。
(4)在交易中政府部門過度干預(yù),如交易初期臨時退后報價截止時間,及指定價差返還系數(shù),相對松懈或?qū)捤傻碾娏σ?guī)則使得售電側(cè)與購電側(cè)用戶產(chǎn)生投機(jī)心理,對電力市場期望值降低,打消之后參與市場競爭積極性,不利于規(guī)范化市場體制形成。
5.3 廣東電力交易新動態(tài)
4月26日,廣東電力交易中心公布了第二次月度集中撮合結(jié)果。交易系統(tǒng)網(wǎng)站的公布結(jié)果。
對比第二次交易結(jié)果,可以分析得出以下結(jié)論:
(1)結(jié)果中:需方最高成交價-1.1厘/千瓦時。這部分電量的成交價是由散戶報的,也就是參加交易的供應(yīng)側(cè)(發(fā)電廠),需求側(cè)(售電公司,大用戶)這三大類電力交易主體中所占比重較低的大用戶成交結(jié)果。說明兩年來,部分大用戶的市場意識沒有培養(yǎng)起來,參與度與實力都不如售電商。
(2)結(jié)果中:需方最低成交價-79厘/千瓦時。這部分是由售電公司報的,而最終市場競價的利潤又流入電網(wǎng),肥水不流外人田。
(3)結(jié)果中:需方平均成交價-51.58厘/千瓦時。可知上個月初次市場交易后,交易雙方都或多或少獲得利潤,需方的賭性顯現(xiàn),多數(shù)需方拿出至少10%出來,進(jìn)行博弈。
(4)結(jié)果中:供方最高成交價-371厘/千瓦時,最低成交價-500厘/千瓦時,平均-436厘/千瓦時。說明供應(yīng)方主要的電力生產(chǎn)方式中火電機(jī)組開始真正的競爭。
參考文獻(xiàn):
[1]朱成章.電力體制改革的難度(上)[J].大眾用電,2016(04).
[2]戴麗.這些年我國的電力體制改革[J].節(jié)能與環(huán)保,2016(01):24-31.
[3]劉洪深.電力體制結(jié)構(gòu)模式演進(jìn)與我國電力體制改革方向[J]. 大眾用電,2016(01).
[4]洪猛.電力體制改革與核電電價政策淺析[J].中國核工業(yè), 2016(01):51-53.
[5]劉紀(jì)鵬.國企改革助力電力體制新發(fā)展[J].中國電力企業(yè)管理,2016(0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