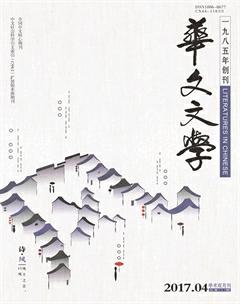從當代中國幾次文學論戰看理想的文學批評之建構
徐全
摘要:本文所探討的“十七年”時期姚文元所參與的文學論戰、“文革”結束之后的《苦戀》論爭風波以及2000年初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論戰,代表了當代中國三個不同思想時空的文學批評論爭樣貌,但共同點是:論戰一方希望維持馬克思主義作為文學批評的主導觀念和方法,進而達到鞏固既有意識形態主導地位的目的,故而他們將文學批評視為一種任務(task)或使命(mission);而另一方則試圖將文學批評定位在藝術審美層面,一些知識分子更是將文學批評作為歷史重構和解析的工具。因此,文學批評與文學的學術研究具有本質的不同,理想的文學批評乃是多元的觀點、批評視角與批評方法的融合。
關鍵詞:文學批評;姚文元;白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中圖分類號:I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677(2017)4-0035-13
1949年之后的中國,左翼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從原本作為一種文藝理論的流派,隨著中國政權的更動,而逐漸具備了文藝批評方法的正統性。此種批評模式將一切文藝作品從階級分析法與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進行解讀,從“世界觀——方法論”的哲學模式去審視文學作品的優劣。原本,文學批評究竟是側重意識形態屬性、社會批評,還是應當側重藝術審美屬性的評析,并無統一的答案。只不過,在彼時強調馬克思主義文藝路線的氛圍之下,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文學理論研究都成為一種為現實政治服務的工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理論除了成為官方所倡導的文學批評模式外,更成為了衡量其它一切文學批評理論是非對錯的唯一標準,成為文學批評的指導思想。如此一來,則文學批評從一種感情表達、思想陳述等單純的個人行為,轉化成具有強烈政治思維色彩的價值導向行為。一切文藝作品的解讀,都無法超越此一邏輯。
于是,文學批評就不僅僅是評論家、知識分子或是民間個體化的一種作品或作者評價,它同時也成為了方法唯一、標準唯一的一種“任務”和“使命”。官方倡導文學為政治、為社會主義服務,則文學批評也應為民眾塑造出一種合乎左翼革命歷史觀和價值體系的思想形態。因此,歷史觀的話語建構也成為特定環境下文學批評所具有的一種功能:時而對現實或當下進行評判;時而進行歷史記憶或者歷史觀的塑造。
筆者認為,從1949年到1979年,中國的文學創作與批評樣貌是:作家是生產商,文本是其制造出的商品;文學批評則是一種“質檢標準”或一套“質檢程序”,執行這一標準的初衷,就是要篩選出好的作品與好的作家,以服務特定的意識形態體系。
從1949年起到1966年“文革”爆發這“十七年”中,官方為了塑造馬克思主義作為革命史觀的唯一正當性,文學批評的寬松環境伴隨著一次次的論爭甚至政治運動以及人身迫害而漸漸消失。那段時期的中國文學批評架構,只容得下以“階級分析法”為綱的模式存在,任何與此相異的文學批評觀念或是文學作品,都會遭到壓制。姚文元對胡風、朱光潛、周谷城甚至賀綠汀的批判,就是在此一環境的土壤中發生的。雖然被批者以及巴金等人都曾一度對姚文元的大批判進行反制,但是整體“左”的文學批評格局難以改變。“文革”的爆發便是這一格局發展到極端的表現。
“文革”結束之后,發生在1981年的文學劇本《苦戀》論爭風波,是不同意識形態在文學領域的又一次對撞。這次論戰涉及的是如何看待“愛國”觀念、如何看待1949年之后的中國史。不過與“十七年”時期不同的是,《解放軍報》代表官方意識形態所進行的批判,卻面對文藝界各種形式的抵制;更為突出的一點是:深受“文革”浩劫影響的普通大眾并沒有在文學論戰中充當看客,而是參與其中。最終,《苦戀》論爭風波沒有發展成為“文革”的回潮。
世紀之交前夕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及其改編電視劇所引發的論戰,參與方更加廣泛。一方面,伴隨著同名原著改編為電視劇,編劇梁曉聲歷史反思式的文本批評方式遭到質疑;另一方面,官方也希望借助電視劇的公映進行意識形態價值觀與紅色歷史觀的重塑;但更值得關注的是,對蘇聯以及紅色思想持批判立場的知識分子則完全否定這一作品,并由此引發司法訴訟。相較于《苦戀》論爭時代,大眾在論戰中的表態也顯得更加開放和多元。大眾對官方的意識形態和歷史觀塑造,也未有積極回應。
本文討論的,便是如何從這些文學論戰中,總結出一種對文學批評自身價值或獨立性進行定位的思考或認識。
一、“十七年”時期姚文元的文學批評回顧
如今,“文革”被公認為是極“左”思潮泛濫并對文學批評產生了重大影響的產物。不過,“文革”時期大批判式的文學批評模式并非一夜之間出現,而是在“十七年”(1949至1966)階段中逐步形成的。“十七年”的含義是:在中國官方角度看,于政治社會領域是新政權的鞏固、國民經濟的恢復以及全面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的時代;而在思想文化界,則配合新政權的意識形態標準,包括文學批評在內的各種文化行為,都漸漸成為塑造新的歷史觀的工具。這其中,后來成為“四人幫”骨干的姚文元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角色。
對文學藝術界進行思想上的“整頓”,并不是從反右運動開始的,也不是以后來的“文革”為開端,實質上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就已經拉開了序幕,這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便是從文學理論爭鳴演化為政治迫害的“胡風反革命集團”事件。值得一提的是,后來成為“四人幫”之一的姚文元,之所以能走入政治與文藝難以區分的歷史漩渦,便是以發表在1955年第一期《文藝報》上的批判胡風的文章《分清是非,劃清界限》為起點的。而在整個1955年,姚文元批判胡風的文章差不多有十多篇。①
“十七年”時期的文學批評承載的官方政治使命已經越來越重,如何看待中國歷史上的文學家并以此去認識中國革命史,成為了當時執政者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胡風和魯迅關系密切,弘揚魯迅必然也就要借此機會批判胡風及其思想,以確立起符合彼時左翼意識形態的魯迅批評觀。1959年,為了深入對胡風及其思想進行批判,姚文元的《魯迅——中國文化革命的巨人》一書正式出版發行。這部當時被收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書》的作品,是一篇典型意義上的文學批評,但是卻也具有鮮明的“使命”和“任務”色彩。姚文元強調的是,文學批評,尤其是涉及到魯迅的文學批評,就是一場斗爭;而對這一點,他一點也不回避,認為“對于魯迅思想和創作的研究,必然涉及到文化思想和文藝思想上許多根本的原則問題。歷來在魯迅研究上,就是尖銳的思想斗爭和政治斗爭的沙場。”②由此可見,在淺層次上,姚文元對魯迅進行的文學批評,是要“糾正”和清除胡風對魯迅個人及其作品的批評理論的影響;其次,在深層次上則是要將魯迅的個人經歷納入到整個中國近現代的革命史觀中。故而,在論及《魯迅——中國文化革命的巨人》一書對于文學批評觀念建構的重要性時,姚文元寫道:
……一,對于廣大讀者,可以從正確的批評文章中區分鮮肉和爛肉,區別滋養品和毒品,獲得正確的鑒賞,不致不加區別的‘隨手拈來,大口吞下;對于新文藝,‘也可催促它向正確,前進的路,反對那些錯誤、倒退的傾向,堅持正確的文藝路線。文藝批評是思想斗爭的武器,是催促文藝向正確方向發展的一種力量,是幫助廣大讀者理解和欣賞文學創作的鑰匙。③
顯然,在姚文元的觀念中,胡風的文學批評理論是屬于“爛肉”,因此“鮮肉”的文學批評理論就必須合乎馬克思主義的標準以及革命的現實需要。姚文元對魯迅的評述,幾乎都會引申到對胡風的批判,以切合彼時的官方文藝路線的需要。在敘述“為何會出現魯迅這一偉大人物”的問題時,姚文元認為是“偉大的時代產生了偉大的魯迅”,而將魯迅與中國現代史中的共產革命相結合,他這樣看待魯迅這一偉大人物的誕生:
魯迅是適應著中國近代歷史的要求而產生出來的,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到偉大的五四運動產生了革命民主主義者魯迅,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產生了共產主義者魯迅,這是一個鐵的事實……胡風分子們曾竭力使魯迅神化,把魯迅的出現說得神乎其神地令人難解,這完全是唯心主義的煙幕彈。④
魯迅與梁實秋、林語堂等人曾經的論戰,也不可避免地成為姚文元批判胡風的歷史素材。他認為“魯迅同資產階級反動文人和反動理論的戰斗,有著長久的意義……而且留下了許多很寶貴的現在還有現實意義的意見……魯迅的戰斗文章將繼續從思想上武裝我們,成為我們為貫徹社會主義文藝路線而斗爭的有力的武器。”⑤因此,魯迅曾經進行過的思想戰斗一直持續到了今日。而有關“道德階級性”的問題,更是成為了姚文元借力打力、“以魯迅壓胡風”的工具:
在階級社會里,只有階級的道德,階級的善惡……胡風分子們所慣用的欺騙手腕,就是抽去后期魯迅道德觀念的階級內容……這是用以迷惑不堅定者的主觀唯心論的語言……抽象地談真善美,只有利于剝削階級而不利于勞動人民……我們要同魯迅一樣憎恨剝削階級的道德,我們要同魯迅一樣不斷掃除自己和別人心上的垃圾。⑥
姚文元認為,魯迅也好,文學批評這一形式本身也好,都具有鮮明的“工具化”特征,其一切都是為了服務于政治大局。從這個意義上說,批判胡風這一做法本身都不能夠稱之為是終極目的。姚文元在《魯迅——中國文化革命的巨人》一書的末章中,以一段極富鼓動性的文字,概括出了他看待文學批評功用和價值的立場,這也可以看作是他本人從普遍意義上,對文學批評家“使命”或“任務”的具體定位:
我們的筆,應當是一支號角,響亮地吹奏著共產主義思想的贊歌;我們的筆,應當是一把利劍,劈開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思想,把它從各個領域中徹底清除出去;我們的筆,應當是一把鐵鏟,不斷地開辟著前進的道路;我們的筆,應當是一支畫筆,繪下我們偉大時代和創造這個時代的英雄們的容貌和靈魂;我們的筆,應當是一根鋼骨,可以用它支撐起新的社會主義的民族的新文化的巨廈;我們的筆,應當是一把掃帚,老老實實地為掃除我們屋子里的灰塵服務;我們的筆,應當是一塊海綿,把古今中外人類歷史上創造的一切優秀的凈化都吸收進來。……我相信,魯迅是希望我們這樣做的。⑦
當姚文元以《魯迅——中國文化革命的巨人》一書批判胡風的時候,胡風已經被定性為“反革命”,完全失去了自由,難以再對姚文元的批判進行回應。姚文元本人在“十七年”時期,不僅僅批判胡風。他對賀綠汀、周谷城、朱光潛等人的文藝批評,都曾經引起巨大的轟動。其中,較為重要的一次論爭,是發生在姚文元和美學家朱光潛之間一場有關“美”的標準的論戰。1961年,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先后發表了《論生活中的美與丑——美學筆記之一》、《關于美學討論的幾個問題——答朱光潛先生》等文章,對朱光潛的美學思想提出批判。姚文元認為,對“美”的評價標準,應從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角度出發去評判,例如他認為“新生的向上發展的就是美的,衰老死亡的阻礙發展的就是丑的”⑧。朱光潛作為當時著名的美學理論家,并沒有保持沉默,而是以撰文回應的方式進行了反擊。在同年的3月17日,朱光潛在上海《文匯報》發表了題為《從姚文元同志的美學觀點談到美學中的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的文章,以《紅樓夢》中的劉姥姥為例,認為“假如現實生活中有那樣的老婦人,她無疑是丑的,但作為藝術作品,她是一個寫得淋漓盡致的逼真的人物,能否產生美感呢”⑨,故而朱光潛認為姚文元“對美的所有概念都是片面的”⑩。
姚文元在“十七年”時期的文學批評活動,顯然不是簡單意義上的文學探討。在當時的社會語境下,文學批評已經是一種塑造新思想的工具,也是從事“階級斗爭”的工具,而不是局限在文人小圈子中的作品鑒賞,更不是大學校園中的純粹意義上的文學學術研究。在那個時代,文學批評動輒就有可能上升為政治斗爭、政治迫害甚至政治動蕩。“文革”的爆發,也是以文學藝術的批評作為起點和具體形式的。只不過,當時不少文藝界人士并沒有意識到:忽略、放任姚文元這種大批判式的文學批評可能帶來的深遠和負面影響。對于這個問題,巴金在當時的舉動及晚年的回憶,頗為值得深思。
當姚文元這支被江青稱為“無產階級的金棍子”在“十七年”時期,將批判的言辭一次次指向文藝家時,巴金并沒有保持沉默。1962年5月,上海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會中,巴金進行了題為《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的發言,他覺得作家的創作應該有獨立性,不能夠完全成為政治的附庸,認為“要一個作家負擔過多的責任,使人感到不寫文章反而兩肩輕松,不發表作品叫別人抓不到辮子,倒可以安安靜靜地過日子,這決不是好辦法。”{11}而最為引人關注的,則是巴金對當時文學批評充斥大批判、肆意整人的情況的擔憂,尤其是對于姚文元之流的文學批評模式,巴金大為不滿:
他們喜歡制造簡單的框框,也滿足于自己制造出來的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們都套在他們的框框里頭。倘使有人不肯鉆進他們的框框里去,倘使別人的花園里多開了幾種花,窗前樹上多有幾聲不同的鳥叫,倘使他們聽見新鮮的歌,看到沒有見慣的文章,他們會怒火上升,高舉棍棒,來一個迎頭痛擊。他們今天說這篇文章歪曲了某一種人的形象,明天又說那一位作者誣蔑了我們新社會的生活,好像我們偉大的祖國只屬于他們極少數的人,沒有他們的點頭,誰也不能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12}
巴金的敏銳性在于,他能夠充分意識到,那時的文學批評,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學術研究,而是與社會政治的大環境、整個中國的意識形態和文藝政策取向有著巨大關聯,文學批評本身已經成為了這種社會體系的一環。因此,一些類似于姚文元之流的文學批評家們必然是以政治氛圍來確定文學批評的標準。巴金對此指出:
……我們也有一些專門看風向、摸‘行情的‘批評家……不管說好說壞,總是把自己放在高居臨下的地位,不用道理說服人,單憑一時“行情”或者個人好惡來論斷,捧起來可以說得天上有地下無,罵起來什么帽子都給人戴上,好像離了捧和罵就寫不成批評文章似的……只有在作家和批評家互相學習、彼此幫助、互相尊重、攜手前進、共同為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奮斗的緊密團結的局面下,才會有萬花吐艷、百鳥鳴春的盛況。{13}
巴金的上述談話,主要是針對姚文元,這在當時已經是公開的秘密,{14}且在巴金本人晚年的回憶中也得到了證實。特別值得深思的是,巴金晚年在回憶這一段往事時,非常憂慮后人忽略了“十七年”時期文學批評的此種亂象,而只是孤立地將“文革”看成是對中國文藝發展造成阻礙的階段。在巴金的意識中,“文革”的爆發根本不是在某一天之內突然形成的,而是有著“十七年”時期的種種因素疊加的。姚文元作為立場偏頗的文藝批評家,能夠依靠政治嗅覺,不斷進入到文化和意識形態控制領域的核心上層,且在這一過程中亦未遇到什么阻礙,都是在“十七年”時期發生的,而“文革”結束之后的中國社會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和反思,顯然還沒有全面和深化。巴金在《隨想錄》中寫道:
五十年代中期張春橋就在上海‘領導文藝、‘管文藝了。姚文元也是那個時候在上海培養出來的……這些人振振有辭、洋洋得意,經常發號施令,在大小會上點名訓人,仿佛真理就在他們的手里,文藝便是他們的私產,演員、作家都是他們的奴仆。……但是張春橋、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并不曲折,他們也走得很順利,因為他們是踏著奴仆們的身體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個,我今天還責備自己。我擔心那條青云之路并不曾給堵死,我懷疑會不會再有‘姚文元出現在我們中間。我們的祖國母親再也經不起那樣大的折騰了。{15}
二、改革時代的《苦戀》風波
1980年代初期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改革”始動的時代。那時的中國社會,剛剛經歷了文革帶來的負面記憶,知識界開始逐漸流露出歷史反思的傾向。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反思已經不僅僅是對“文革”十年的重新認識,而是上溯到了中國的近現代史,思考中國人與國家命運的張力和關聯。
改革時期的中國,奠基在左翼社會主義革命基礎之上的合法性并未改變。故而在思想文化甚至社會領域,官方與部分民間思想界形成了意識形態上的二元張力。西方學界注意到了這一點,認為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國社會,一方面是中國知識界、文化界、民間要求思想解放、創作與多元的訴求;另一方面則是官方維護左翼價值觀的既存事實。{16}本文分析的《苦戀》論爭的主角白樺,就曾公開表示“寧歌頌民主墻上一塊磚,千萬不要歌頌救世主”。{17}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苦戀》論爭事件發生了。
電影文學劇本《苦戀》,由武漢軍區軍旅作家白樺創作完成,發表在1979年的《十月》第三期上,展現了知識分子在理想與現實矛盾中的無奈選擇和悲劇命運。在當時的中國,從學界到民間,伴隨著經濟改革的起步,對“文革”的反思逐漸演變為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文學界也不可能自外于這種反思。劇本中,曾經反抗過國民黨統治的主人公凌晨光,是中國彼時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凌晨光舍棄了國外的一切優厚待遇,滿懷報國之志回國效力。回國之后的他遭遇一次次政治運動和迫害;雖然境遇每況愈下,凌晨光仍舊苦苦依戀著自己的祖國,無怨無悔;直到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為一生的愛國信念劃下休止符時。劇本認為,凌晨光留下的,是雪地中一個巨大的問號。
《苦戀》這部劇本所傳遞出的文本信息,反映了當時的中國社會思潮,例如對個人崇拜的隱喻。在劇本中,有這樣一個極為有名、也引起了巨大爭議的反問式對白:“你愛國,可是這個國家愛你嗎?”而在劇本的結尾處,則將“祖國,我愛你”稱之為“神圣的權利”。在白樺的塑造下,造成主人公死亡的,是“國家”,是“被香火熏黑的金身佛像”(隱喻對個人崇拜的反思),而非“祖國”。劇本中的“祖國”,是主人公自小生活的土地、山川、河流,與之相伴的親人、朋友、同胞等。
《苦戀》在發表后曾被長春電影制片廠拍成電影《太陽和人》。《苦戀》的劇本一發表,便引起了官方的關注并派專人前往拍攝現場,對影片的結尾提出修改意見。{18}可見,官方的文學批評行動早已經開始,只不過當時還未見諸于文字。1981年4月20日,《解放軍報》刊發特約評論員文章《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評電影文學劇本〈苦戀〉》對《苦戀》進行了批判,由此引發了文藝界甚至是全社會對該文學劇本的激烈爭論。《解放軍報》批判白樺及《苦戀》的理由是:劇本傳遞出的歷史觀是“新中國不如舊中國,共產黨不如國民黨,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祖國不僅毫無可愛之處,而且可憎可怕。”{19}而1981年,恰恰適逢中國共產黨建黨六十周年:
六十年{20}來,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華民族才根本改變自己的命運,在世界上站起來了。我們黨領導下的偉大的人民解放事業,是中華民族愛國主義史冊上最光輝燦爛的一頁;今天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集中地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21}
可見,該怎樣看待中國革命史——這一大前提式的原則,白樺就已經與官方產生了沖突。不過,由于“文革”剛剛過去,國家也經歷過饑荒歲月,這篇評論員文章也對“文革”等階段的歷史脈絡進行回應,認為“盡管建國以來,我們黨的工作有過失誤,幾經挫折,特別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未能充分發揮,但建國三十年來的成績仍然是巨大的。”{22}
作為一篇承擔著政治使命的文學批評文章,批判《苦戀》的文字,也是從其文本內容入手的。文本中的意象、背景、情節,通通成為被否定的對象:
《苦戀》通過藝術形象散布了一種背離社會主義祖國的情緒……實際上成了對于祖國的控訴和詛咒,是散布一種對祖國懷疑和怨恨的情緒……禪院長老和少年凌晨光關于神佛、香火和廟堂的對話的中心意思是:廟堂制造了神佛,愚弄了善男信女,騙取了香火。這種隱喻和暗示,所能產生的社會效果,只能是把人們對‘四人幫的仇恨引向黨和黨的領導人,引向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作品中一再用天上的人字雁群和人是‘天地間最高尚的形象的主題歌,來反襯地上的人的悲慘命運,指責我們的黨踐踏了人的尊嚴,抹殺了人的價值,制造了祖國大地上的人的悲劇。”
《苦戀》所引出的有關“愛國”內涵的討論,毫無疑問是《解放軍報》批判的主要內容。白樺在劇本中區分了“祖國”、“國家”、“愛國”等概念,軍報予以了反駁,認為“愛國”這一概念,在社會主義中國的具體歷史條件下,必須與“愛黨”、“愛社會主義”相結合:
愛國,愛國主義精神,從來不是抽象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和不同的階級社會里有著不同的內容。今天,我們講愛國,不只是熱愛我們祖國的地大物博、山川秀麗、歷史悠久和燦爛的文化傳統,而是要熱愛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十億勤勞勇敢的人民,熱愛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熱愛黨領導下的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事業。這種愛國主義具有最廣闊最深厚的社會基礎,具有嶄新的社會經濟的、政治的、思想的內容,是歷史上任何的愛國主義所不能比擬的;它反映了人民和國家間的新的關系,這種關系是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難道今天對祖國的愛,能夠同對黨、對社會主義的愛相對立嗎?”
在《解放軍報》的立場來看,愛國是歷史而具體的產物,而《苦戀》卻將愛國抽象為“愛傳統文化”、“愛山川秀麗”。《解放軍報》在文章結尾強調了傳統意義上由官方所倡導的文學創作觀,即:一方面對文藝工作提出了具體要求,希望不要再出現類似《苦戀》這樣的文學作品;同時也透過對官方文藝思想路線的重申,強化對中共革命史的認同與支持:
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的立國之本。它的內容是載入了我國憲法的。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都應遵守,各條戰線各項工作都應遵循,文藝工作不能例外。電影文學劇本《苦戀》的出現不是孤立的現象,它反映了存在于極少數人中的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資產階級自由化以至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潮……雙百方針是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的方針,指的是在文學藝術中各種形式和風格的自由競賽,在學術上的自由討論,反對用行政的方式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如果把它理解為可以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沒有任何限制的絕對自由,那就會走到違背廣大人民利益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邪路上去……每一個愛國的、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文藝工作者,都應緊密地團結在黨的周圍,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繼續解放思想,正確貫徹雙百方針,促進社會主義文藝的繁榮和發展,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正確反映我們所處的新時代,促進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同心同德為四化的偉大事業作出新的貢獻。
《解放軍報》對白樺和《苦戀》進行的批判,雖然是從文本內容出發的一則文學批評文章,但卻有著極為明顯的意識形態功能:重申確立擁護特定意識形態的文藝創作路線,倡導官方的歷史觀。
作為軍人作家的白樺,本人及其作品被軍報點名批判,而且是發生在全面改革的八十年代,確實令當時的輿論界、文學界大為詫異。《解放軍報》的這篇批判文章刊載之后,引起了全國性的震動。經歷了“文革”歲月的中國知識界,顯然對于這樣的文學批評文字難以接受。在那個沒有網絡的時代中,傳統媒介和會場成為了文藝家們反對大批判的平臺。例如,1981年1月,在由《電影藝術》和《大眾電影》召開的聯合座談會上,幾乎出現了“一面倒”地支持白樺和《苦戀》的聲音。{23}
在官方輿論體系中,例如上海《文匯報》等媒體的主編,在充分閱讀了白樺的文本之后,始終拒絕轉載《解放軍報》的批判文章。{24}而《苦戀》批判風波愈演愈烈之際,白樺的同行,則以“作品評獎”這種特殊的文學批評方式對白樺給予了支持。{25}為了抵制對白樺的批判,白樺的詩歌《春潮在望》經過同行們的努力,獲得了1980年度的“全國中青年詩歌獎”;中國作協下轄的《新觀察》也主動向白樺約稿;{26}官方的新華社則針對《解放軍報》的對白樺的批判與白樺獲得“全國中青年詩歌獎”這兩個看似矛盾的現象,發表了題為《批評,但不是棍子》的具有中立色彩的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與以往文學論戰的不同,民間大眾并沒有成為《苦戀》論爭中的旁觀者。有民眾議論“是不是姚文元放出來了”;北京大學亦出現大字報聲援白樺。{27}對白樺表示支持的人,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立場。例如,白樺曾談到,有陌生的青年人送給他一塊石頭,以鼓勵自己堅強勇敢。{28}全國各地大量的陌生人的聲援信寄往白樺家中。白樺在晚年的回憶中指出:
我經常收到讀者來信,但都沒有這一時期這樣多,每天傍晚通訊員小王就笑嘻嘻地給我送來一大堆,我仔細讀著那些陌生人的函電,想象著他們的職業、性格和形象,并擇其要者復信。常常感動得痛哭失聲,不知晨往而昏至。{29}
《解放軍報》的文章所引起的爭論,顯然也引起了政治高層的關注。時任總書記胡耀邦反對重走大批判式的“文革”老路,并且堅決不讓作為最高黨報的《人民日報》撰文參與論爭。{30}鄧小平也希望擺脫《解放軍報》引起的大批判格局,認為“《解放軍報》進行了批評,是應該的。首先要肯定應該批評。缺點是,評論文章說理不夠完滿,有些方法和提法考慮得不夠周到。《文藝報》要組織幾篇評論《苦戀》和其他有關問題的質量高的文章。”{31}《苦戀》的論爭風波,最后是以《文藝報》相對溫和的文學評論文章《論〈苦戀〉的錯誤傾向》以及白樺自己撰寫的檢討《關于〈苦戀〉的通信:致〈解放軍報〉〈文藝報〉編輯部》的公開發表,而宣告落幕。
《苦戀》論爭的過程表明,“十七年”以及“文革”時期以姚文元為代表的大批判模式,此時無法獲得文藝界、民間的認同,甚至也難以獲得政治高層的認可;民間和文藝界積極參與文學論戰,表達觀點,使得文學批評已經不再是精英的意識形態和思想討論的專利。
三、改編的探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論爭
影視劇改編者對文學原著進行文學批評,使得文學作品從單純意義上的紙質文本載體轉化為電影、電視劇、舞臺劇,從而為大眾提供了全新的文本解讀形式。文本內涵從扁平化的文字轉化為具有聲像畫面立體感的活動有機體。這一轉化過程本身,價值觀的塑造、歷史的評價、人物形象的更新等,便是這一文學批評方式的具體表現形式。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以下簡稱《鋼鐵》)長期以來被當作蘇聯革命文學的經典之作而加以流傳。在世紀之交的2000年,《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被中國影視創作人員搬上了電視屏幕,成為了一部長達二十集的電視連續劇。
中國人改編外國文學作品,必然會有中國人結合本國歷史的思考。更何況《鋼鐵》所渲染的蘇維埃國度已經成為了一個歷史名詞。因此,當電視劇版《鋼鐵》與觀眾見面時,或許是面對觀眾對于劇中情節可能出現的質疑,電視劇《鋼鐵》的責任編導劉放便表示,劇組在拍攝時,“在保爾(筆者注:《鋼鐵》主人公、被視為優秀左翼革命青年的代表)對革命的思考中注入了中國人對歷史的反思,從而使得中國版《鋼鐵》具有了歷史的厚重感和現實的啟示意義,保爾的形象也更加完整。”{32}那么,這種“歷史的反思”究竟是什么?
在蘇聯已經解體的背景之下,改編《鋼鐵》面臨的最大問題,便是如何將一部曾經充滿意識形態話語和革命價值思維的作品,變得讓今人能夠接受。《鋼鐵》編劇梁曉聲非常清楚這一困難,他認為“保爾·柯察金這一文學人物被尷尬地夾在階級斗爭的史頁中了”{33},因此,今日已經遠離了階級斗爭與革命話語的中國人,是無法接受傳統蘇聯意義上的保爾形象的,“一名典型的階級的戰士對革命的忠誠……乃是它所注定了要死去的那一重書魂。”{34}因此,梁曉聲對改編的原則,有了如下看法:
……要盡量可信地告訴今人——在革命的時期,在革命的大背景下,在革命的隊伍中和革命的漩渦里,人會變得怎樣?以及為什么?鮮血和犧牲、革命的暴烈、反革命分子的暗殺和恐怖手段、階級對階級的仇恨和報復……亦應在改編中有客觀的表現,而不應從改編的過程中用忌諱的橡皮任意擦去……{35}
除此之外,情感的刻畫也成為梁曉聲改編原著的一個重點。梁曉聲認為,革命與階級的敘述,并不能抹去人們對于情感的追求,“《紅樓夢》中永遠不會死的是愛情”{36},成為了梁曉聲將保爾情感化的重要動力。他直言不諱地指明,“將黨、革命、愛情和親情在理念上截然對立起來的革命者,在我看來,是不可愛的人。”{37}
因此,冬妮婭、麗達這兩位女性與保爾之間的情感,占據了梁曉聲劇本相當大的成分。保爾和冬妮婭之間的愛情,因為“革命”所帶來的差異,被徹底摧毀;為了凸顯保爾與麗達之間的愛情,也為了表現革命成功后的蘇俄政治斗爭與清洗對人的摧殘,梁曉聲甚至在劇本的情節安排中,加入了“讓已婚的麗達變成了遭受黨內迫害而下放工廠勞動、并與保爾重逢發生性愛以及麗達最后在大火中殞命”的內容。{38}愛情的塑造,某種意義上成為了梁曉聲在對小說《鋼鐵》進行文學批評時的一種更加個體化、人性化的反思:
……愛情是有硬度的——體現在保爾身上;愛情是有理性原則的——體現在麗達身上;愛情是遭到了傷害的——體現在冬妮婭身上。但這傷害不是金錢、權力和地位造成的,而是男人胸襟的狹隘造成的……愛也是有奉獻的體現在達雅身上……將愛情和革命對立起來,正如將愛情和權力和金錢結合起來一樣,都是時代對人的異化……{39}
而當電視劇最終公映時,其情節實際上較之于梁曉聲的文學劇本更加進取。主人公保爾以及他的革命經歷,呈現出了與原著小說甚至中國人長期所受教育大相徑庭的觀感——大俄羅斯主義在革命的名義下對烏克蘭的民族壓迫、頤指氣使的莫斯科官僚在烏克蘭為所欲為、升官的都是革命時期的投機分子、被紅色恐怖大清洗消滅的是革命時代的忠誠戰士——麗達沒有死于火災而是因被肅反委員會拘捕而失蹤、蘇維埃社會的腐化不堪等等;甚至在最后一集結尾,當最高蘇維埃席團的成員前往保爾家中為他授勛時,保爾的鄰居甚至以為是蘇維埃政府要逮捕保爾。保爾被塑造成了失去健康、失去愛情、失去人生發展機遇、且革命理想化為烏有的工具。
電視劇在塑造革命的對立面時也頗有意味:傳統意義上反共的白軍,被賦予了人道和正義的特質。電視劇中,白衛軍反對蘇維埃政權而密謀暴動,舉事前夜,白軍動情高呼“為了烏克蘭的解放和自由”;而主人公保爾,拒絕未經審判就槍決白軍官兵;為了解救被肅反委員會逮捕的白衛軍頭目的幼小女兒,保爾毆打了蘇共的肅反人員;此后,保爾更因無法適應革命恐怖主義的煎熬而退出肅反機構。{40}
梁曉聲的劇本,在部分情節上被導演修改、攝制組轉而采用了烏克蘭作家的編劇版本,梁曉聲也為此和導演公開沖突。{41}但是,就表現蘇聯體制的殘暴、人道主義在革命中的滅失等方面的情節主旨,梁曉聲的編創原意還是原封不動地在屏幕上顯現。雖然《鋼鐵》電視劇版是一部講述他國紅色題材的作品,但梁曉聲對保爾的塑造以及對《鋼鐵》的改編,還是在某種程度上碰觸到了中國意識形態中的核心層面。
2000年3月23日,《中華讀書報》發表了《重塑保爾不能“篡改”保爾》的評論文章,對梁曉聲在《鋼鐵》中的編劇思路進行了點名道姓的批判,認為梁曉聲的改編嚴重背離了原著的原意,濫用了“人的異化”的理論,“掉進了非歷史主義的泥潭”。對于梁曉聲想還原保爾被革命“異化”的“人性”一面,《中華讀書報》的文章認為:
勞動者作為人異化為非人,就說明了私有制的產生,也展現出了這種異化勞動的發展必然又將對私有制加以揚棄的道路。保爾和他同時代的勞動者,被私有制及其代表德軍侵略者、彼得留拉匪徒所異化,又起而對其加以揚棄,于是無怨無悔地參加了批判異化、拯救作為主體的人——勞動者的革命斗爭……忠誠于革命,他們就抒寫了人類最美好、最善良的天性,抒寫了人性的最美點,絕不能輕易地否定他們的選擇和忠誠,行為和追求。{42}
至于梁曉聲“掉進了非歷史主義的泥潭”,這是針對梁曉聲在劇本中著力刻畫保爾與冬妮婭、麗達、達雅等人的愛情而言;另一方面是針對梁曉聲在劇本中對蘇維埃革命中非人道性一面(肅反、黨內斗爭)的反思。文章認為:
“紅色恐怖”也好,革命隊伍內部的混亂和斗爭也好,都是事實。問題是,在改寫歷史的時候,我們應該怎樣正確地看待這些事實。梁曉聲應該知道,古今中外,一切變革社會的歷史潮流和運動,或者說,一切革命或革新的運動,在它的進行過程中,幾乎都難免帶有種種的局限性,甚至難免帶有內部的血污,但人們并不因此而否定這種歷史運動實行的意義{43}。
對梁曉聲的上述質疑,在當時并未引起整體性的大批判風潮。從某種意義上說,也說明當時中國社會在一定程度上對文學批評觀點多元化的包容。此外,除了對電視劇和小說情節的討論之外,隨著電視劇的放映,帶來的討論、反思、價值觀的辯論也在逐漸升溫。不同的群體以不同的視角,參與到對《鋼鐵》電視劇和原著的討論中去,以尋求對作品進行一種能夠反映當下時代特征的文學批評。官方也不例外,希望能借助這次作品批評來實現重塑理想型完人的目的(下文將述及官方組織的座談會)。這其中,有關“保爾和蓋茨誰是英雄”的討論是最為典型的。2000年3月11日,《北京青年報》以讀者來信的方式,刊登了一篇題為《保爾與蓋茨誰是英雄》的文章,署名“小潘”的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了這樣的疑惑:
……保爾·柯察金精神的核心是以個體生命無私地奉獻于社會,他將個人的命運與激流勇進的事業相結合,理想和信仰是保爾精神的根本……比爾·蓋茨的可貴之處,在于他不僅憑智慧和能力證明了知識可以造就財富的寓言,更重要的是,他在為自己謀求巨額財富的同時,也深刻地改變了人類命運。看看今天網絡時代的到來吧,微軟的產品已經與我們日常生活多么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保爾和蓋茨,誰是英雄?誰是今天應該令我們仿效的英雄?{44}
三天后,《北京青年報》又大篇幅刊載了民間百姓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但是立場觀點并非單一:有人堅持認為保爾就是英雄,而創造財富資本的蓋茨無法與之相提并論:
英雄不是隨便亂叫的,無論是慷慨赴死,還是從容就義,都是以犧牲自我來升華信念。英雄或許無名,但在人們心中永遠有他們的紀念碑……保爾在奮勇沖鋒的時候,是慷慨赴死的英雄;在與病魔頑強抗爭的時候,是從容就義的英雄,他是真正的英雄……蓋茨會有機會成為帝王,但他絕不會成為英雄,看看他為對付Netscape及其他對手所采取的種種手段,可見一斑。{45}
也有人認為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蓋茨依靠個人的努力,白手起家,是當之無愧的英雄:
保爾是他那個時代的英雄,蓋茨是這個時代的英雄。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以保爾作為偶像,生活在今天的我們以蓋茨為偶像……只講奉獻,不圖回報。是不是該變一變呢?是不是應該把那些獎狀、表揚變成獎金和財富?讓成就事業者真正得到實惠?……在輿論方面,我們經常看到的、人們天天學習的保爾式人物是不是該向蓋茨式人物轉換呢?{46}
當時,這場“關于英雄標準的討論”,由《北京青年報》發起,在全國輿論特別是青年人中展開。中宣部、教育部、共青團中央則在討論開始后,聯合舉行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座談會,討論小說以及同名電視劇對青年人塑造人生觀價值觀的意義。參加座談會的北京大學學生會主席認為保爾作為一個英雄,體現了“學習科學文化與加強思想修養的統一;學習書本知識與投身社會實踐的統一;實現自身價值與服務祖國人民的統一;樹立遠大理想與進行艱苦奮斗的統一”{47},因此,保爾不是一個過時的英雄。但耐人尋味的是,作為這一討論的一部分,輿論的參與以及大眾的反饋,為傳統意義上的保爾式英雄觀“潑了冷水”。青少年似乎并未因官方推動的討論而對《鋼鐵》及其價值觀的認同有所增加。{48}
其次,按照梁曉聲塑造保爾的思路以及后來正式公映的電視劇劇情,再結合當時社會輿論對于電視劇改編版本的評價來看,電視劇《鋼鐵》已經與原著小說拉開了相當大的距離:保爾成為了一個有人性、有人道、懂得為愛情后悔的青年;白軍成為了烏克蘭的自由而戰的持不同政見者;蘇維埃革命與紅色政權并非完美無缺,肅反委員會最終拘捕了麗達、濫殺無辜、官僚盛行,百姓活在政治恐怖中等等,傳統的左翼革命色彩已經大大弱化。
但是,一些對極“左”文藝理論持強烈批判立場的知識界人士,面對這樣的改編版本,依舊認為應該徹底而完全地否定《鋼鐵》——無論是小說還是電視劇,并且徹底拋棄文本中所倡導的蘇聯價值觀。南京大學學者余一中在自己撰寫的文學批評長文《“大煉〈鋼鐵〉”煉出的廢品——評〈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電視連續劇文學本》中,認為除了原著小說的中文譯本存在嚴重的翻譯謬誤之外,更為嚴重的問題,則是電視劇文本與歷史真實存在著嚴重背離。余一中的歷史真實觀在于:他認為,在蘇聯的極權體制之下,電視劇中很多對紅色體制與弊端進行反抗的情節,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例如,為了營救被懷疑參加托派而遭到逮捕的麗達,保爾只身一人在全俄肅反委員會總部與肅反人員針鋒相對;紅軍士兵可以任意嘲弄具有官僚腐化墮落傾向的政委等。余一中覺得,在蘇聯當時的恐怖政治氛圍中,根本沒有人敢去做電視劇中描繪的這些事。
此外,余一中認為電視劇并沒有擺脫原著帶來的階級革命的烙印,仍然將保爾塑造成為了“一出場就有清醒的階級意識和高度的階級覺悟”{49}的形象。故而,余一中對電視劇版中的保爾形象,給予了十分尖銳的否定評價:“一個由‘三突出{50}原則制造出來的假保爾”。{51}不僅如此,余一中更覺得,根本沒有任何必要將《鋼鐵》從小說改編為電視劇,因為蘇聯以及烏克蘭的那段歷史已經被證明是完全錯誤和失敗的,盲目改編以配合政治的需要,在藝術真實與歷史真實的統一上,是根本無法做到的,以這樣的改編作品去實現“英雄”的塑造,更是錯誤和不可能:
難道我們還要因循蘇聯的所謂社會主義文化模式,到斯大林所謂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實際上是文化專制主義)的樣板中去討生活,去找那些沒有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的‘英雄加以‘重塑嗎?{52}
余一中以“媚左”一詞來形容電視劇《鋼鐵》及其主創人員,卻引發了《鋼鐵》擁護者的強烈不滿。2000年6月26日,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下屬的《新聞出版報》刊發題為《由批評編校差錯所引發的論爭》的評論文章,點名批判余一中對《鋼鐵》的看法,并且上升到了政治和思想路線斗爭的高度,認為余一中“批判編校質量只是一層薄薄的面紗,借題發揮的后面卻做著一塊更厚重的文章……評判態度已不是嚴肅的學術研究,而是在借題發揮肆意攻擊……如果帶著政治和自己狹隘的眼光、偏見來評判一部被公認了的優秀文學作品,這種批評的用心就值得懷疑”{53}。并且,《新聞出版報》還在編者按中明確指出:
這個論爭不是純學術的,也不是雞毛蒜皮的小是小非,而是關系到是否堅持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原則之爭,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54}
余一中不接受這種意識形態批判的論調,不過他并未糾纏在輿論爭議中,而是一紙訴狀將《新聞出版報》告上了法院,認為《新聞出版報》的言論是“不負責任的誹謗之詞語”、“把純學術討論的問題引到政治上推波助瀾”;而《新聞出版報》則在法庭中辯稱,報社刊登編者按的目的是為了引起讀者對《鋼鐵》一書與電視劇價值的討論,并未侵害余一中的名譽權;最終南京鼓樓區法院認為《新聞出版報社》只是發表與余一中相反的觀點,報社的觀點同樣應得到尊重,故而并不構成對余一中的誹謗,判定余一中敗訴。{55}
《新聞出版報》是否侵害了余一中的名譽權,不在本文討論之列。筆者關注的是,相較于十七年時期姚文元對胡風、朱光潛、賀綠汀等人的隨意批判;相較于《苦戀》批判風波中文藝界對于創作與批評環境是否倒退以及“文革”重演的憂慮,同樣是面對一部政治性極強的文學作品及其改編、評價與論爭,當批評主體覺得已經難以再通過文學批評本身去回應對立觀點,且覺得對立觀點傷害到自己人格尊嚴時,司法訴訟成為了解決論爭的一個新途徑。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社會文化的一個巨大改變。
無論是梁曉聲編寫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電視文學劇本,還是他自己后來為電視劇內容進行解釋而撰寫的文學批評專著《重塑保爾·柯察金》,甚至后來《中華讀書報》批判梁曉聲的文章《重塑保爾不能“篡改”保爾》,都應當看作是一種文學批評,而且是歷史論爭性質的文學批評。梁曉聲編寫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電視劇本,反映了他對原著小說的觀點、看法與立場;他的《重塑保爾·柯察金》更是他對小說主人公跨越時空式的理解;而《中華讀書報》的《重塑保爾不能“篡改”保爾》,則是依據原著小說的文本,進行的反擊式文學批評。
回顧《鋼鐵》論爭不難發現,官方希望借助電視劇的開播對民眾特別是青年人進行意識形態理想的教育;文化界則希望將作品融入更多人性化的思考和表現;而側重歷史反思的知識分子則希望借助討論,達到反思和批判蘇聯歷史的目標;部分青年大眾則對這一作品反應,較為冷漠,也并不接受作品所傳遞出的價值取向。梁曉聲、余一中等,側重于反思蘇聯的歷史(只不過余一中比梁曉聲顯得更加“激進”);《北京青年報》、《中華讀書報》、《新聞出版報》等官方傳媒,則希望借助文本的價值觀及相關討論,重塑對蘇聯意識形態與歷史的某種正解。
因此,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雖然《鋼鐵》是一部外國文學作品,但是無論是肯定派還是否定派,卻都在論爭中傳遞出了一個共識:此種論爭,更多是在探討中國人自己的歷史與價值觀塑造。這種論爭帶動了對蘇聯歷史的再認識。其中一個較為值得關注、又極具現實指標性的討論焦點便是:《鋼鐵》是蘇聯紅色革命小說,情節是以烏克蘭、特別是與波蘭接壤的西烏克蘭地區為背景的,作者本人也是烏克蘭人。在統一的蘇聯時代,這不固然是一個問題。但蘇聯解體后,卻牽涉了極為復雜的民族、歷史和政治認同。中國作家劉心武便曾經對此發出“現在俄羅斯與烏克蘭儼然是兩個國家,這位作家和這本書,該算是烏克蘭作家寫的一本烏克蘭文學作品呢,還是也可以算是俄羅斯作家寫的一本俄羅斯文學作品呢”{56}的疑問。而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姜長斌則在其本人撰寫的評論文章《質疑〈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歷史背景》一文中指出,擺脫大俄羅斯主義的專制統治,一直是烏克蘭民族精英的理想,但《鋼鐵》卻將領導烏克蘭獨立運動的西蒙·彼得留拉(Symon Petliura)及其民族武裝稱為“匪幫”,但今日的烏克蘭人對彼得留拉深懷敬意。{57}故而,姜長斌認為,“文藝作品的藝術性和政治理性是一致的”,當中國“大力推薦《鋼鐵》這本書的時候,實在是應該考慮到當代烏克蘭朋友的民族感情。”{58}
結論
文學批評有時是社會批評(如《北京青年報》發起的“英雄觀”討論);有時是政論(如姚文元的文章);有時是生活評論;有時是情感、思想與認同觀念的博弈(如《解放軍報》對苦戀的批判);有時是歷史反思(如梁曉聲、余一中對《鋼鐵》的認識);有時是社會開放包容程度的“晴雨表”(如余一中與《新聞出版報》的司法訴訟);有時則是借助文學作品對現實進行強烈批判和否定的“異端”。這里的“異端”,不僅僅是觀點上的異端,也是文學批評方法上的“異端”(如白樺的《春潮在望》獲獎)。
回溯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中的這些文學論戰,則文學批評在當代中國的政治和文化語境中,從來都不是簡單、個體化的文本解讀或作者評價。在一次次的文學論戰中,參與論戰的不同人、不同陣營和力量,實質上都將文學批評作為一種闡述自我歷史觀、意識形態或是政治認同取向的工具。此種語境下的文學論戰,實際上已經成為了思潮的博弈、價值觀的碰撞、歷史的認知拉鋸。此外,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文學批評的表現形式也會有較大的區別,引起的社會效應也不同。
文學批評畢竟是一種獨立和個體化的文化活動。理想的文學批評,對于思想意識的啟蒙、歷史的反思、社會民眾人文素養的提升,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反之也會造成巨大的破壞。因此,文學批評與文學的學術研究,有著巨大的差異。建構理想的文學批評,其最大的障礙并非文學批評成為塑造歷史觀或意識形態的工具甚至“棍子”,最大的障礙其實來自文學批評這一舞臺的“容積”(tolerance)究竟有多大:是否能夠容納不同和多元的文學批評模式、立場與方法。畢竟,自由的文學批評乃言論和思想自由的延伸。
①史云編著:《張春橋姚文元實傳》,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19頁。
②③④⑤⑥⑦ 姚文元著:《魯迅——中國文化革命的巨人》,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年版,第5頁;第175頁;第4頁;第105頁;第121頁;第270頁。
⑧ 姚文元:《論生活中的美與丑——美學筆記之一》,上海《文匯報》(上海:1961年)。
⑨⑩ 朱光潛:《從姚文元同志的美學觀點談到美學中的理論與實踐的結合》,載1961年3月17日《文匯報》。
{11}{12}{13} 巴金:《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李濟生編選《巴金七十年文選》,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884頁;第883頁;第887頁。
{14} 史云編著:《張春橋姚文元實傳:自傳、日記、供詞》,香港: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257頁。
{15} 巴金: 《究竟屬于誰》,李濟生編選《巴金七十年文選》,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頁
{16} Thomas M. Magstadt, Peter M. Schotten. Understanding Politics: Ideas, Institution and Issues. NewYork: Worth publishers, Inc, 1999: 201.
{17}{18} 李乃清:《白樺:“苦戀”三十年》,《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6期。
{19}{21}{22} 《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評電影文學劇本〈苦戀〉》,載1981年4月20日《解放軍報》。
{20} 筆者注:指中國共產黨建立六十年。
{23} 韌霧:《“文革”后禁片的政治問題》,《國家人文歷史》2013年第2期。
{24} 馬達:《〈文匯報〉拒絕轉載批判〈苦戀〉文章內情》,《歷史與內幕》2005年第7期。
{25} 張萬舒著:《改革的年代:1977-1989》,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259頁。
{26}{27}{28}{29} 李乃清:《白樺:“苦戀”三十年》,《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6期。
{30} 徐慶全:《〈苦戀〉風波始末》,《南方文壇》2005年第5期。
{31} 鄧小平:《關于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鄧小平文選》(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4-348頁。
{32} 劉放:《重塑保爾·柯察金》,載2000年3月3日《人民日報》。
{33}{34}{35}{36}{37}{38}{39} 梁曉聲著:《重塑保爾·柯察金》,同心出版社2000年版,第1頁;第29頁;第29頁;第28頁;第101頁;第307-323頁;第37頁。
{40} 筆者注:可參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電視文學本)》,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
{41}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幕后起紛爭》,載2000年2月29日《長江日報》。
{42}{43} 曾慶瑞,趙遐秋:《重塑保爾不能“篡改”保爾》,載2000年3月22日《中華讀書報》。
{44} 《保爾與蓋茨誰是英雄》,載2000年3月11日《北京青年報》。
{45}{46} 《不同的英雄,不同的境界》,載2000年3月14日《北京青年報》。
{47} 《保爾精神體現了四個統一:中宣部教育部團中央聯合召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座談會》,載2000年3月17日《北京青年報》。
{48} 筆者注:在這場討論開始前,南京《揚子晚報》進行過調查,發現多數青年人并不欣賞保爾(參見2000年3月2日《揚子晚報》《欣賞保爾?崇拜蓋茨?一項調查耐人尋味》);而討論開始后,《北京青年報》刊載了北京某中學語文老師的班會記錄,其中認為蓋茨是英雄的有38人,認為保爾是英雄的只有9人(參見2000年3月16日《北京青年報》《中學生眼中的保爾與蓋茨:一個語文老師的班會記錄》);而各地報刊(如《天津日報》的文章《保爾和蓋茨:誰是英雄》)對這一問題的討論,也并沒有以“保爾是英雄”為唯一的答案導向。
{49}{51}{52} 余一中:《“大煉〈鋼鐵〉”煉出的廢品——評〈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文學本》,《當代外國文學》2000年第2期。
{50} 筆者注:所謂“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53}{54} 鐘宜漁:《由批評編校差錯所引發的論爭》,載2000年6月26日《新聞出版報紙》。
{55} 最高人民法院編《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3年第2期。
{56} 劉心武:《重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文學自由談》1997年第5期。
{57}{58} 姜長斌:《質疑〈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歷史背景》,《探索與爭鳴》2004年第11期。
{59} 筆者注: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曾于2000年3月27日發表評論文章《崇拜蓋茨無可厚非》等文章。
參考文獻
1. 姚文元著:《魯迅——中國文化革命的巨人》,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年版。
2. 梁曉聲著:《重塑保爾·柯察金》,北京同心出版社2000年版。
3. 史云編著:《張春橋姚文元實傳:自傳、日記、供詞》,香港三聯書店2013年版。
4. 李洪林著:《中國思想運動史》,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0年版。
5. 宋如珊著:《從傷痕文學到尋根文學:文革后十年的大陸文學流派》,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
6. 陳思和著:《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7. 曹文軒著:《二十世紀末中國文學現像研究》,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
8. 古遠清著:《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1949-1989大陸部分),山東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
(責任編輯:莊園)
Abstract: A literary debate that Yao Wenyuan took part in in the Seventeen-year Period, the storm surrounding a debate about the play,‘Bitter Love, at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debate about the novel,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 in early 2000, all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represent the pattern of literary-critical debates in three different time-spaces of thought with the common ground being that one party was hoping to keep Marxism as the guiding concept and method in literary criticism for the purpose of consolidating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existing ideology,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y viewed literary criticism as a task or mission while the other party was trying to position literary criticism in aestheticism and, moreover, a number of intellectuals used literary criticism as a tool of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For this reaso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academic research differ by nature while an ideal kind of literary criticism would be an integration of multi-points, critical viewpoints and critical methods.
Keywords: Literary criticism, Yao Wenyuan, Bai Hua,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