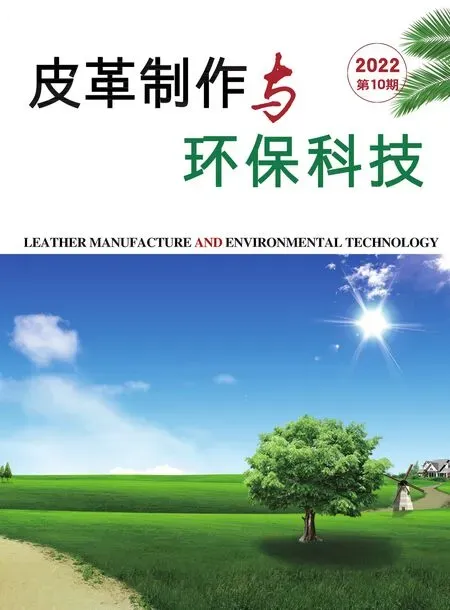傳統工藝和新興工藝處理重金屬廢水方法的對比研究
劉 飛,陸浩翔,文 明,徐 達,楊舒凡
(1.浙江天能資源循環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 湖州 313100;2.浙江天能動力能源有限公司 浙江湖州 313100;3.浙江天能電源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 湖州 313100;4.天能帥福得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湖州 313100;5.天能電池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 湖州 313100)
在工業生產活動中,各種重金屬元素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其在金屬冶煉行業、機械制造行業以及礦山開采行業中隨處可見,這些重金屬會與工業廢水混合在一起,形成重金屬廢水,排放到自然界的水循環系統中,會對水環境造成破壞,導致原有的生態平衡被打破[1]。與此同時,重金屬具有難降解的特性,它可以在未來幾年甚至是幾十年的時間里持續表現出毒性。這些重金屬廢水被排放到土壤生態系統中,會被農作物吸收,并隨著人們食用這些農作物或者農產品,通過富集作用進入人體內,危害人類的身體健康。由此可見,對重金屬廢水的處理效果關系到人類社會的發展,關系到生態系統的平衡,同時也關系到人類的生存和健康。
1 重金屬廢水污染概述
1.1 重金屬廢水的來源
在當前的社會背景下,重金屬廢水的來源途徑比較多樣,不同產業在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重金屬種類和數量也存在明顯的差異。目前排放重金屬廢水的行業包括礦山開采、金屬冶煉、電解電鍍、油漆和顏料生產等。雖然國家已經出臺了相關政策對這些企業的污水排放行為進行約束,但仍然存在亂排亂放的問題,還有部分企業存在過度排放和無節制排放的行為。近年來,我國工業發展形式變得越來越多樣,發展規模也在進一步拓展,這使得重金屬廢水的排放量也在增加,水體環境中重金屬的類型也在增加,處理起來更加困難。在處理這些廢水時,要充分關注重金屬的特點,通過轉移重金屬存在的位置和存在形態的方式來只能降低其危害性,無法直接使其被分解和被破壞,這對處理工藝提出了較高的要求。
1.2 重金屬廢水的危害
1.2.1 對人體健康造成危害
從直接的角度來說,在水體被重金屬污染的情況下,如果人們直接飲用就會危害身體健康。重金屬元素進入人體后會抑制酶發揮作用,導致相關生命活動受到影響[2]。同時,重金屬元素還會影響人體的神經系統,尤其是對解毒器官帶來危害,使人體出現一系列的中毒反應。從間接的角度來說,如果灌溉用的水源被重金屬污染,這些重金屬元素就會富集到農作物當中,間接地進入人體。同時,這些重金屬元素也可以存在于水體中的藻類植物和荷塘底泥當中,被水體當中的魚類和貝類吸附,人們食用這些水產品后,重金屬就會進入體內。間接危害通常并不會在短時間內顯現出來,但會帶來長期的影響,降低人體的免疫力,使人體處于亞健康狀態。
1.2.2 對水生植物造成危害
重金屬廢水排放后,不僅會對自然水體造成污染,同時還會影響水體中水生植物的正常生長,抑制水生植物的正常生命活動,比如會減緩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速度。同時,植物體內酶的活性也會受到一定的抑制,這會導致植物的生長速度減緩,嚴重情況下還會導致植物走向枯萎甚至死亡。同一種重金屬對于不同水生植物的影響存在差異,不同重金屬元素對于同一種水生植物的影響也并不相同。
1.2.3 對水生動物造成危害
與水生植物相比,重金屬廢水對于水生動物的影響和危害更為明顯和直接,不僅會影響動物生長發育的速度,同時還會影響其正常的新陳代謝功能。如果水體中重金屬的濃度超過一定的限度,其中生活的動物就會出現中毒的癥狀。比如很多魚類先會掙扎,經過一段時間后死亡,而烏龜等爬行動物的胚胎發育則會受到影響,容易出現畸形胚胎。除此之外,部分重金屬元素還會導致水生動物在發展和繁衍的過程中發生基因突變,導致優質基因無法留存。
2 傳統工藝對重金屬廢水的處理
2.1 物理處理方法
2.1.1 膜分離法
這種處理方法指的是基于外界壓力,使用特殊的半透膜將水體中的溶劑和溶質分離。在分離過程中,溶質的物理狀態可能會發生變化,但化學形態保持不變。在使用這種方法對重金屬廢水進行處理時,需要先通過氧化、吸附等方法進行預處理,使其中的重金屬離子以微粒的形式存在,然后再利用濾膜清除離子。這種處理方式的操作比較簡單,處理成本也比較低,在整個分離過程中都不會造成二次污染[3]。但與此同時,膜組件的設計難度比較高,在前期需要大量的投資,這是阻礙該方法大范圍普及的主要原因。
2.1.2 吸附法
這種處理方法主要是利用具有吸附作用的物質來完成對重金屬的吸附。這些吸附劑中存在活性基團,在遇到重金屬離子后可以發生相互作用,形成離子鍵或者共價鍵,將重金屬廢水中的重金屬吸收,因而去除污染因子。同時,在經過組合之后,這些重金屬離子還會形成特殊的籠形分子,進一步增強了吸附效果。吸附法在實際應用過程中容易受到溫度、酸堿度等因素的影響,處理效果不夠穩定,同時對吸附劑的性能要求也比較高。
2.1.3 離子交換法
該方法通過離子交換,可以將重金屬廢水中的部分重金屬離子交換成其他離子,以此達到降低重金屬濃度的效果。與其他處理方法相比,離子交換法最大的優勢是在對重金屬廢水進行處理的同時可以對其中的重金屬元素進行回收。該方法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是離子交換樹脂,這種材料表現出了較強的可逆性特征,在經過多次使用后仍然可以表現出較好的性能。但這種處理方法的處理成本比較高,前期投入比較大,難以在大規模范圍內使用。
2.2 化學處理方法
2.2.1 電化學法
這種處理方法主要利用了電解的原理,通過形成電解池使廢水中處于游離狀態的重金屬離子在陰陽兩級發生相應的化學反應,達到重金屬被析出的目的。析出的重金屬常會附著在電極表面,或者聚集到反應器的底部形成沉淀。由此可見,這種方法在對廢水進行處理的同時可以達到重金屬回收的目的。但這種處理方法需要大量的能量作為支撐,目前只應用于電鍍重金屬廢水的處理,應用該方法時,工作人員需要對重金屬的回收價值與處理成本進行對比分析[4]。
2.2.2 化學沉淀法
通過在重金屬廢水中投放相應的化學藥劑,可以使其中的重金屬元素通過沉淀的形式被析出,這是化學沉淀法的應用原理。這種處理方法最大的特點就是處理過程比較簡單,沒有復雜的操作。由于大多數的重金屬離子都可以形成沉淀,因此這種方法的適用范圍比較廣。但該方法對沉淀劑的要求比較高,工作人員需要選擇高品質、適用性強的沉淀劑。為了使重金屬離子在形成沉淀的同時不對水體造成二次污染,需要嚴格控制沉淀劑的用量,用量過多或者過少都會帶來不良的影響。
3 新興工藝處理重金屬廢水的方法
3.1 生物吸附法
與物理吸附法相比,生物吸附法是利用生物體特有的化學結構和化學特性吸附重金屬廢水中的重金屬離子,再利用固液兩相分離的形式將重金屬去除。相關人員在研究后發現,自然界存在一些特征性細菌,它們在生長發育的過程中會產生并釋放一種特殊的蛋白質類物質,這種物質可以將水體中的重金屬離子轉化為沉淀,利用這一特性,可以達到重金屬吸附和去除的效果。如果重金屬廢水中的重金屬濃度比較低,生物吸附法可以展現出明顯的優勢,能夠在短時間內完成對重金屬的處理[5]。同時,生物吸附法對于重金屬廢水的酸堿度和溫度的敏感性比較弱,表現出了較強的適應性。與物理吸附劑相比,生物吸附劑能夠直接從自然界中獲取,來源更為廣泛。常見的吸附劑包括腐殖酸、海泡石等。但這些吸附劑對多種重金屬元素會表現出一定的選擇性,通常只能吸附其中的一種或者幾種重金屬。
3.2 生物絮凝法
這種處理方法是利用微生物的代謝產物處理重金屬廢水,這些代謝產物可以使重金屬離子形成絮凝沉淀,最終被析出。這些絮凝劑是由微生物分泌的,成分為多種微分子物質構成的混合物。從分子結構看,該絮凝劑中含有官能團,可以使重金屬廢水中的膠體由懸浮狀態轉變為團聚狀態,最終形成固體的沉降,并通過固液分離操作被去除。實踐證明,有效的生物絮凝作用可以使活性污泥表現出較強的沉降和脫水性能,同時還可以對重金屬廢水處理后的水質進行優化。生物絮凝劑具有生物分解性,不會對水體環境造成二次污染,同時它們的來源比較廣泛,目前已經發現自然界中有17種微生物都可以表現出絮凝作用。但由于生物絮凝劑具有一定的活性,保存起來比較困難,因此難以進行大規模生產。在未來發展過程中,可以通過基因工程對這些微生物進行馴化,培育出具有特殊功能的新菌株,用于特定重金屬廢水的高效處理。
3.3 植物修復法
這種處理方法是利用植物體對重金屬的轉移和富集作用來達到重金屬廢水處理的效果。除了能夠處理被重金屬污染的水體外,植物修復法還可以處理被重金屬污染的土壤。由于植物擁有發達的根系,可以對水體進行過濾,同時植物體還具有吸收、揮發等功能,這是對水體污染物進行分離和去除的基礎。除了吸收重金屬、使其被富集之外,植物還可以降低水體中重金屬的活性,避免重金屬通過土壤浸出或者以空氣作為載體進行擴散[6]。在實際應用過程中,工作人員會將廢水中的元素輸送到植物的根系等位置,或者使其聚集到植物體的枝條上,在完成處理之后再去除這些根系或者枝條,這并不會影響植物體的正常生長,而且還可以降低重金屬廢水中重金屬的濃度。目前,在礦山生態系統修復、人工濕地環境重金屬廢水處理等領域,植物修復法都表現出了明顯的優勢,得到了廣泛的應用。近年來,研究人員還通過盆栽試驗對重金屬的整個遷移過程進行了追蹤,得到了重金屬濃度在不同階段的變化規律和去除規律,并在此基礎上對植物體的修復能力進行了計算,使重金屬廢水處理變得更為有效和精準。
4 傳統工藝和新興工藝處理重金屬廢水的方法對比
通過上文的分析可以發現,在重金屬廢水處理領域,傳統處理方法主要以化學法和物理法為主,受到各種因素的限制,其中化學處理法比較常用,而物理處理方法還沒有得到廣泛應用。這些典型的工藝手段雖然可以達到預期的處理效果,在長期的使用過程中也積累了很多經驗,相關技術逐漸趨于成熟和穩定,相關設備也處于穩定運行的狀態。但在處理過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試劑尤其是化學試劑,如果試劑量控制不當可能會造成二次污染[7]。另外,傳統工藝對設備的依賴性比較強,需要大量的電能作為支撐,這導致處理過程的經濟性較差。除此之外,在使用傳統工藝對重金屬廢水進行處理時,需要嚴格控制反應條件,通常情況下需要先對廢水進行預處理,使廢水的溫度和酸堿度保持在合理范圍內,因而增加了操作步驟。
新興工藝主要以生物處理方法為主,在確保重金屬處理效果的基礎上彌補了傳統工藝的缺陷和不足,提高了重金屬降解的速度和效果,且日常管理過程也更為簡單。在整個處理過程中所產生的能源消耗更低,基本不會出現二次污染,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自然生態環境。但新興工藝主要是利用微生物或者植物的生長代謝活動來對重金屬廢水進行處理,在實際應用過程中需要對特定的微生物進行培養,還要關注微生物的保存問題,因此這種處理方法容易受到自然環境的影響,處理效果不穩定,整個修復過程也比較慢。
由此可見,傳統處理工藝和新興處理工藝的特點不同,二者在具體要求和實際處理效果方面也表現出了明顯的差異。在實際應用過程中,工作人員可以結合實際情況進行選擇,根據重金屬廢水的特點、需要達到的處理效果以及經濟性特征等來選定最適用的處理工藝[8],也可以通過幾種方法聯合使用的形式實現傳統工藝和新興工藝的優勢結合,以達到處理效果優化的目的。
5 結語
綜上所述,在重金屬廢水處理的傳統工藝中,物理處理法存在較多的限制條件,使用范圍比較小,而化學處理法的處理過程比較復雜,容易產生二次污染。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需要更多地應用新興工藝來對廢水進行處理,通過生物處理方法達到無公害化處理的目的,該技術對于復雜重金屬廢水的處理也具有良好的效果。此外,還要持續創新重金屬廢水處理技術,并在其中融入光催化、基因工程等,以達到在去除廢水中重金屬物質的同時回收有價值重金屬的目的,從而實現對廢水的資源化利用,這是未來行業發展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