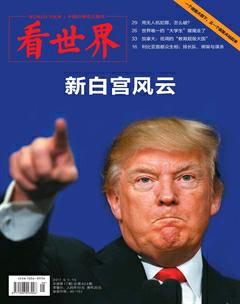蘇聯(lián)時代被禁播的影片(下)
孫越
蘇聯(lián)引進外國電影相當謹慎和苛刻。根據(jù)蘇聯(lián)相關法律法規(guī),青少年滿16歲才可觀看較為“露骨”的外國影片,當然這些影片都是經(jīng)過審查部門精心處理過的。法國導演安德烈·米歇爾1956年拍攝的電影《女巫》就因為片中有裸戲,在蘇聯(lián)引發(fā)了青少年能否觀看的爭議,最終《女巫》事件為蘇聯(lián)調(diào)整引進片的審查尺度和觀影年齡限制的政策提供了依據(jù)。1968年,蘇聯(lián)又發(fā)生了蘇匈合拍片《星與兵》審查事件,這部影片為蘇聯(lián)電影審查部門制定合拍片的審查標準奠定了基礎。
20世紀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世界局勢動蕩,蘇聯(lián)對世界文化思潮更加多疑和防范。蘇聯(lián)當局不斷加強完善引進片的標準,審查也更加嚴格。比如1970年,意大利電影大師貝納爾多·貝托魯奇的影片《同流者》原版影片片長115分鐘,引進蘇聯(lián)后被剪掉32分鐘。審查部門對影片所進行的剪輯完全斷章取義,并將一部彩色電影處理成黑白片發(fā)行,以至于蘇聯(lián)觀眾一直認為《同流者》原本就是一部黑白片。1973年,英國導演林賽·安德森的影片《大都市小人物》引進蘇聯(lián)后,時長183分鐘的影片被剪去了45分鐘,結果完全歪曲了安德森的創(chuàng)作意圖和藝術理念。
日本導演黑澤明1970年拍攝的彩色奇幻電影《電車狂》,引進蘇聯(lián)時被剪去了50分鐘。導演新藤兼人的影片《赤貧的19歲》(1970),盡管于1971年獲得蘇聯(lián)莫斯科國際電影節(jié)金獎,但在蘇聯(lián)公映時仍遭嚴格審查。
波蘭電影大師安杰伊·瓦依達1974年根據(jù)作家瓦迪斯瓦爾·雷蒙特的同名小說改編拍攝了《天堂》,第九屆莫斯科國際電影節(jié)評委會欲授予其金獎,但由于片中有色情鏡頭,評委會便通知瓦依達剪掉相關鏡頭后再送審,莫斯科當局答應他刪除色情片段即授獎。瓦依達同意并剪掉了敏感鏡頭,影片如愿以償獲獎。
蘇聯(lián)解體后,瓦依達又將刪除的鏡頭補上,出了個完整版的《天堂》。他說:“我雖然補上了刪除的色情鏡頭,但是我二十年來一直為這些鏡頭感到羞愧,因為我的電影不是為色情而色情,而是為爭取創(chuàng)作自由。現(xiàn)在我們允許拍攝有色情內(nèi)容的電影,但我卻反對色情。你們現(xiàn)在會覺得我當時很幼稚,但在蘇聯(lián)時代,藝術家創(chuàng)作上的反叛就是最佳抗爭手段。”
意大利導演佛朗哥·澤菲雷里的《羅密歐與朱麗葉》(1968)、波蘭導演羅曼·扎魯斯基的《愛情解剖》(1972)、波蘭導演尤利斯·馬休斯基的《鐵幕性史》(1984)等影片在蘇聯(lián)放映之前都曾遭遇大幅度“剪片”。
那時,蘇聯(lián)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的電影節(jié),都以蘇聯(lián)社會主義道德觀和意識形態(tài)為準則,確立了相同或者近似的審查標準,對于通不過審查的影片,或者禁止在電影節(jié)放映,或者不經(jīng)電影版權方許可直接刪改后再放映和參賽,以顯示蘇聯(lián)電影審查的權威性。
蘇聯(lián)電影審查,刪減鏡頭僅僅是一種審查方式,還有一些更不可思議的處理方式,類似于今天的電腦重新編輯,比如通過聲音等編輯特效技術,將審查通不過的地方進行處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83年捷克導演索庫普執(zhí)導的電影《口袋里的風》,片中有個鏡頭是男主角舉著來信興沖沖地高喊:“姑姑寄來了巴黎的邀請函!”審查官命令電影局技術部門對此句臺詞做聲效處理,改成男主角高喊:“入伍通知書到啦!”
蘇聯(lián)著名導演蓋達依拍攝的喜劇片《鉆石手》也有一個鏡頭被做了聲效處理,因為女主人公的對白中有句 “他去了教堂”,審查未獲通過,因為蘇聯(lián)時代“教堂”屬于敏感詞,無法通過審查,所以只能在音效上處理為“他去找情人”而草草了事。但是觀眾在觀影時卻發(fā)現(xiàn)了這句臺詞語氣銜接上有問題。《鉆石手》中被技術處理過的地方比比皆是,如影片中出現(xiàn)的妓女、酒鬼以及不作為官員等鏡頭均被審查官批評為“形象猥瑣”,堅決剪掉。
盡管蘇聯(lián)電影審查制度嚴厲,不少高水準影片遭遇封殺和被迫修改,但并未阻止一些影片最終沖出樊籠,躋身世界優(yōu)秀電影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