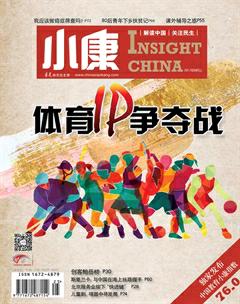兒童劇,喧囂中尋發展
楊柳
暑期來臨,各個兒童劇院的舞臺都在上演著一幕幕熱鬧的劇情。然而,隨著近年來兒童劇市場日益火爆,一些問題也逐漸暴露。喧囂熱鬧的舞臺背后,亟待一場冷思考。
“帶娃看劇”的一百種打開方式,哪種最靠譜?隨著兒童劇以黑馬姿態從國內文化市場異軍突起,形式多樣、百花齊放的兒童劇選擇起來簡直令人眼花繚亂。在狂熱的家長們看來,能從樂趣中感知藝術,享受一段共同的親子時光,大概是兒童劇場最迷人之處。

歡樂時光 在《小兵張嘎·幻想曲》上演之前,“玩”就是第一要務,大人玩得比孩子還要盡興、投入。
“大小通吃” 國外引進劇受熱捧
沒有任何一句臺詞,舞臺布景完全是黑色的,演員也全身蒙著黑衣,通過燈光和經過特殊處理的熒光色彩,演繹出個性鮮明的人物和一幕幕如真似幻的劇情。在走進黑光劇《漁夫與金魚》的劇場之前,孫薇薇一直擔心5歲半的兒子小樹會害怕這種全黑的舞臺,畢竟連她自己也是第一次接觸到黑光劇這種藝術形式,而小樹整場的投入和專注卻令她備感意外,一個小時的演出時間里,小樹幾次連連驚呼“好酷啊”。看著孩子在散場結束后還想要和海報上的城堡合影,孫薇薇覺得120元的票價物有所值,她忍不住在朋友圈轉發了好幾張圖片,并配上了宣傳畫冊上的一句話:“追求物質只能獲得短暫的快樂,自知自愛才是生命的真諦。”
作為第七屆中國兒童戲劇節展演劇目之一,《漁夫與金魚》是一部由羅馬尼亞坦達利卡動畫劇院演出的作品,改編自俄羅斯著名文學家普希金創作的童話敘事詩。故事中的老婆婆總是不滿足,向小金魚提出一個又一個要求,貪得無厭的她最終落得一無所有。盡管沒有一句臺詞,但絲毫不妨礙臺下的孩子們理解劇情。主創團隊坦達利卡動畫劇院是羅馬尼亞戲劇界極具代表性的國家藝術團體,此次黑光劇《漁夫與金魚》并不是他們第一次登上中國劇場。此前,他們就曾帶來《你是誰》《不萊梅的音樂家》等深受小朋友喜歡的作品,甚至還攜手中國兒童藝術劇院,聯合改編創作了更加適應中國市場、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的人偶劇《西游記》。
孫薇薇注意到,《漁夫與金魚》并不是此次中國兒童戲劇節上唯一的一枚“外國月亮”,來自以色列的兒童劇《量身定制》、西班牙的多元兒童劇《匹諾曹》、黎巴嫩的木偶音樂劇《一千零一朵玫瑰花》、荷蘭的肢體劇《會飛的奶牛》、俄羅斯的童話音樂劇《綠野仙蹤》、捷克的提線木偶劇《木偶馬戲團》等9個國家和地區兒童戲劇團體帶來的48部劇目,都在這個暑假來到中國。
舞臺上出現越來越多的國外引進兒童劇,說明了市場的包容和認可。而對觀眾來說,看原汁原味的外國兒童劇,也漸成潮流。
張汀至今還記得2015的夏天,《好餓的毛毛蟲》在北京巡演時一票難求的盛況。“原著繪本太經典了,幾乎每個家庭人手一冊,大家完全是靠著口口相傳去看劇的。”兒童劇《好餓的毛毛蟲》當年首次來華,就創下京、滬、蘇、杭等多地巡演紀錄。舞臺上那只綠色的毛毛蟲,充滿了想象力,整部劇就是一場關于色彩、樂趣、詩意的奇幻故事。張汀也是從那一次開始,“入了國外兒童劇的坑”。張汀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大兒子剛剛8歲,小女兒才3歲,她是一家網絡公司的運營經理,同時也是“甜媽寶貝”群的群主。幾乎每個周末,她都會帶著孩子們參加各種各樣的親子活動,幾年時間內看過了近百場兒童劇,是群里媽媽們公認的帶娃看戲的專家。“其實我看劇也是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張汀告訴記者,現在也有很多“技術分析帖”教媽媽們如何選劇,但因為每個孩子的藝術領悟力不同,“很難去界定什么樣的劇是好劇”。不過張汀也坦承,在媽媽群體中,默認一套不成文的“潛規則”:“不知道看什么劇的時候,就選國外的,至少不會出錯。”
近幾年,引進兒童劇數量不斷增長、類型也多種多樣。例如,上海最受孩子歡迎的親子微劇場“小不點大視界”,最初是由幾位媽媽成立的,創立之初就立足“與國際接軌”,選劇標準十分明確:全球范圍內引進好劇。僅2016年一年,“小不點大視界”就引進了15部國外兒童劇,演出380場次,其中包括澳大利亞與意大利的多媒體旅行劇《魔毯·星空》、英國的親子環球熱舞派對《跳舞吧!寶貝》、西班牙多媒體動畫互動劇《貓飛狗跳》、法國裝置動畫音樂劇《水孩子》等。盡管引進劇存在成本高、檔期短、語言障礙、文化差異等一系列問題,但在“小不點大視界”親子微劇場創始人兼藝術總監陳忌譖看來,國外兒童劇有著定位明確、注重情感的優勢。“國外的兒童劇作品并不刻意要求孩子們看過后學習了什么道理或是記住了什么劇情,更多的是通過多媒體手段打開孩子的想像力和認知度,熱愛自然和世界。讓孩子感受和體驗就好,不一定為了獲取什么。小朋友其實比你想象得更強大,藝術的種子也許就此種下。”陳忌譖說。
原創兒童劇 求新求變求精
在國外兒童劇贏得一片口碑和票房的同時,國內兒童劇卻面臨著一個尷尬的局面。一方面是潛力巨大需求火爆的市場,另一方面是缺乏有創造力的作品和制作團隊。
從題材內容到表現手法,國內兒童劇常常被觀眾吐槽。市面上大多的國內兒童劇劇情雷同,表演和舞美走寫實路線,故事情節和結構缺乏想象。張汀表示,自己就看到過不少“雷劇”,“前幾年‘喜羊羊的IP正熱,劇場里就一扎堆全是灰太狼和喜羊羊;這幾年《熊出沒》的動畫片家喻戶曉,舞臺上又跟風出來很多熊大熊二。不能說全部都是粗制濫造吧,但肯定有些是渾水摸魚的。有些笑點設計,就是故意去‘咯吱你,整場都是聲光電,吵吵鬧鬧演一個多小時,孩子看完,什么也留不下”。

別出心裁 黑光劇《漁夫與金魚》演出現場。貪婪的老婆婆最后失去了一切,只有老爺爺留下來陪她。
“曾經那些‘大頭娃娃劇,以10塊20塊的極低票價,就能迅速讓家長們進劇場。但長期下來是在傷害市場。”鯨魚創藝創始人郭琰說,“‘大頭戲既沒有藝術創作又缺乏舞臺呈現,更談不上演技和內涵,有的稍微改編下經典的童話故事就算創作了。”
鯨魚創藝是精英集團旗下一家從事兒童劇創作和制作的機構。核心團隊成員很多都是《戰馬》的主創、主演,有著豐富的舞臺創作經驗。在郭琰看來,國內兒童劇發展的市場潛力是巨大的,每年6月至8月,向來是兒童劇演出的旺季。根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網站公布的《2016中國演出市場年度報告》分析顯示,2016年專業劇場兒童劇演出場次達到2.06萬場,較2015年上升10.16%,票房收入9.66億元,較2015年上升7.81%。觀眾人數達255.5萬人次,較2015年增長了14.05%。兒童劇市場需求越來越旺盛。并且,這些數字仍在繼續攀升。
火爆的市場背后,需要創作方的冷思考。郭琰指出,近幾年,國內兒童劇的創作也在不斷創新,融入了諸如多媒體、3D、虛擬人物等多種技術手段,演出形式也更加多種多樣,以上海兒童藝術劇場為例,2016年共有40臺220多場演出,包括了戲劇、音樂、舞蹈、多元等四大門類,其中還有現代舞、手影劇、音樂劇、肢體劇、裝置劇等劇目形式。但內容上仍以故事情節為文本,而國外兒童劇有著非常深厚的兒童文學基礎。這是兩者之間最大的區別。國內兒童劇的發展,需要大量的優質原創兒童劇本做支撐。
“據我估計,真正不靠任何IP概念,完完全全原創的劇,大概只有10%左右。”郭琰說,“做原創劇是非常艱難爬坡的過程,但未來一定會成為一個趨勢。”
在樂趣與教育中尋找平衡點
7月9日,松玫帶著兒子飛飛參加了一場特別“嘎”的親子活動,鯨魚創藝團隊的“曉邑哥哥”、“小雄哥哥”和“豆豆姐姐”,帶著小朋友和他們的家長,一起用環保牛皮紙材制作“不一樣”的朋友。大家用奇思妙想和一雙雙巧手,做出了霸王龍、螃蟹老板、火烈鳥、臘腸狗等各種各樣的小紙偶,一起做游戲,一起認識新朋友。鯨魚創藝藝術總監劉曉邑告訴記者,這次的“嘎子”體驗課,實際上也是兒童劇《小兵張嘎·幻想曲》2017年北京首輪演出前的預熱活動之一。
一張桌子、三人一偶,用普通牛皮紙和鐵絲等物件組建的樹木、房屋、碉堡……《小兵張嘎·幻想曲》是一部木偶肢體劇,講述了一段經典故事:抗戰時期,在中國河北白洋淀的鬼不靈村里,有個淘皮搗蛋的小嘎子,他整天下水摸魚,上樹掏鳥蛋,小木槍是他最心愛的玩具。可有一天,敵人進村了,嘎子的奶奶為保護戰斗英雄老鐘叔犧牲了,嘎子擦干眼淚找到部隊一心報仇,心愛的小木槍成了他的武器……這群“85后”的戲劇主創們將《小兵張嘎》從形式到臺詞到舞臺呈現做了一次全方位的創意改編,用肢體讓手中的木偶“嘎子”活了起來,無論是嘎子勇敢應敵,與伙伴嬉鬧,或是耍脾氣鬧小性,都讓觀眾感受到鮮活生命的情感曲線。以肢體劇這樣一種前衛、西方的形式,講述一個根植于中國土壤里的傳統故事,就這樣,誕生于冀中大地的“嘎子”,走出蘆葦蕩,走向英國愛丁堡藝術節、羅馬尼亞錫比烏戲劇節,并獲得國內外觀眾的熱評,引發“嘎子熱”。
“為什么不能給孩子看戰爭戲呢?”在記者問起為什么要選擇一部涉及戰爭題材的劇來改編創作時,劉曉邑如此反問道。戰爭與死亡,這些不應該成為藝術教育的“禁區”。創作者們更不能失去正視歷史、面對問題的勇氣。“劇中有一幕,是一個日本兵發現了躲起來的嘎子,但他并沒有抓嘎子,反而是引開了同伴,客觀上保護了小嘎子。”劉曉邑舉了劇中的一個例子,除了讓小觀眾們領略到嘎子機智勇敢的個性之美外,他們也希望能夠以小見大,反思戰爭對人類肉體的戕害、精神的摧殘,帶出對戰爭本質的懷疑,希冀觀眾無論長幼,都能獲得一些對真善美的認知,和對生命的思考。“一部經典的好戲生命周期是很長的。隨著時代審美的變化、團隊的成長,戲本身的內容也在不斷調整。它有創作者和演員為之付出心血的痕跡,生命力和情感是觀眾能夠在劇場感受到的。”劉曉邑說。
在“樂趣”與“教育”中尋找平衡點,是觀眾和創作者之間一個共同“糾結”的問題。松玫是一家幼兒園園長,由于職業的關系,她在給飛飛選劇時十分挑剔,松玫說,她最反感的就是強行說教的劇,“低質的劇,往往也是低智的劇,故事都還講不好,就硬在里面灌輸一些道理。”飛飛今年8歲了,松玫已經開始帶他看一些昆曲、京戲,“傳統戲曲中有很多真善美的東西,帶孩子接觸兒童劇或戲曲,其實都是在向孩子傳遞審美觀,而且大人千萬不能低估孩子的理解力”。
一部好的兒童戲劇,它的教育功能應該是潤物細無聲的。逗笑孩子并不難,難的是要觸動、激發孩子的內心情感和藝術共鳴。而如何為孩子們打造出優質的兒童劇?郭琰分享了一套自己的觀點:“作品的藝術性、創新性、敘事能力,對于觀眾是不是有教育性、是否具有市場推廣性,能否進行市場巡演等等都可以作為參考。但檢驗作品最好的視角,就是從觀眾的角度來思考。我常和創作團隊講一句玩笑,所有讓家長低頭刷手機的劇,都是創作人員的失敗。現在的家長成長得太快了,必須要尊重挑剔的市場、尊重挑剔的家長,才能做出好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