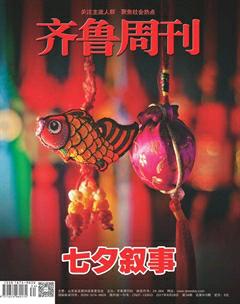豆棚瓜架下的七夕往事
吳永強
相對于諸多繁復的農耕節日,七夕算不得什么,不過在這難得的夏日閑暇時光,談情說愛必不可免。即使是被禮教束縛的近古時代,情人節自動演化為女兒節,于是,在專屬于女人們的夏天的夜晚,小兒女談情說愛,小少婦比賽針線,老女人聊天嚼舌頭,幾千年歷史倏忽而過。那些豆棚瓜架下的閑扯也并不是全沒有用處,它不僅愉悅了身心,還奉獻出一部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影響了一個時代的文學發展。
怨婦與婦女楷模的身份轉換
一個叫氓的男人,因為天太熱,想買一件蠶絲被,晚上蓋著很舒服。于是,他拿了幾尺布,去買蠶絲。那時候,布可以當錢用,如同在海邊的人,可以撿貝殼當錢花。買了蠶絲,小伙還不愿意走,原來他看上了賣蠶絲的女孩。
女孩也看上了他,兩人把蠶絲和布放到一邊,談起了戀愛。此處刪去五百字,過程不表。后來女孩送小伙回去,戀戀不舍,過了一條河,到了一座小山包。女孩說:“不是我不想嫁給你,你家太窮了,你媽事又多,不好伺候,等你找媒人再來提親吧。”小伙急了,說:“你媽也不是省油的燈。”女孩說:“你別犯傻,我媽那是為我好,秋天收完莊稼你就來提親吧。”
小伙滿心歡喜,唱著小曲回家了。
終于到了秋天,小伙開著車來到女孩家。車里是空的,沒有聘禮,但走的時候是滿的,不僅裝下了新娘子,還有滿車的嫁妝。
婚后生活如何?女孩幸福嗎?兩千多年前的女孩,在經歷了男人的花言巧語之后,說出了情愛中的經典總結:“男人喜歡女人,很容易解脫;女人喜歡男人,就沒法脫身了。”從天真的少女成長為怨婦,需要一個花心男人的鼎力相助。
憨厚小伙終于成長為情場老手,小三小四不斷冒出來。婦人整天孝敬公婆,忙家務,疏于打扮,最終淪落為喂豬娘們。再次經過那條小河,是離婚后回娘家。一生的傷痛就此深埋心底,可憐的女人,哀怨了兩千年。
遙遠的夏天的愛情,出現在她的記憶中。那是什么時候?牽牛星與織女星相會的夏日,愛情的起點何其美好,而終點充滿悲劇。
《詩經》里的愛情,總有那么點兒不真實。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到之后呢?其結果會是什么樣子?難以想象,或者已經可以想到結果。所以,《詩經》是屬于少男少女的,少了生活的磨礪,多了河洲上的青草,夜晚天河就像一面鏡子。
無論如何,愛情總會成為兩性話題的高潮。從詩歌出現的那一刻起,便有了牛郎和織女,《詩經》里最早記錄了這對冤家:“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隔著漫漫天河遙相對應的兩個星座,將遠古時人的觀感體現得淋漓盡致,同時萌發了愛情不得的苦楚。
到了漢代,著名的《古詩十九首》更進一步演繹了愛情的細密和絕望:“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此時,牛郎織女的故事即將成型,西王母或者王母娘娘的女兒即將下嫁人間。所以,相對于《詩經》的大而化之,此時的兩者有了更多的細節,心靈手巧的織女,一邊哭著一邊織布,她的情郎還在河的對岸,遙遙相對,卻不能說話。
本來兩者只是純粹的愛情故事,但在中國的愛情想象里,生殖有著恒定的主題,所以愛情的雙方要結婚、生孩子,進入俗世生活。接下來,南朝梁殷蕓的《小說》里,詳細記錄了他們的故事:“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機杼勞役,織成云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后遂廢織妊。天帝怒,責令歸河東,但使一年一度相會。”
何以相會?唯有鵲橋。東漢《風俗通》說:“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為橋。相傳七日鵲首無故皆髡,因為梁以渡織女故也。”為架橋讓織女渡河,喜鵲的頭上都沒了毛。
我小時候,七月初七這一天總會在村巷間尋找喜鵲的身影,往往找不到。老人說不光喜鵲去架橋了,除了麻雀,別的鳥兒都走了。我們信以為真,仰頭看天,沒看到鵲橋。等到傍晚遇見一只喜鵲,就知道它搭橋歸來,一定經歷了很多故事。
可惜,因為織女善于機杼,還能“穿七孔針于開襟樓”,后來演變為著名編織藝術家。故而后世女子以她為榜樣,開始“乞巧”,學習針線活,立志三從四德,那種野性的味道就蕩然無存了。比如在膠東,至今還流傳一首歌謠:
天皇皇,地皇皇
俺請七姐姐下天堂。
不圖你針,不圖你線,
光學你七十二樣好手段。
豆棚下談戀愛的女人們
經歷了春天的約會,到了夏天,便開始轟轟烈烈談起戀愛。這也和農時有關,農歷七月份,莊稼已然進入繁盛期,距離收獲還有一段時間。不只有莊稼,一切植物都已經到了生命的頂點,接下來就是逐漸萎縮和枯萎。瓜果梨桃則已經成熟,氤氳在草木間的,是暑氣有氣無力的呻吟。
此時,遍布中國鄉村,一種特殊的建筑——豆棚,開始成為娛樂界的主會場。這是一種用竹木搭起的小棚,供豆藤攀附生長,一般在房前屋后,夏天豆藤長到最繁盛的時候,遮下一片陰涼。不論白天還是午后,總會有人躲進豆棚里納涼。
農作物越來越多,是接下來故事發生的前提之一。相傳七夕夜里,戀人在豆棚下能聽到牛郎織女的對話。此時,晴朗的天空中,銀河分外明顯,分別代表男女的兩顆星也最亮。旁邊的月亮里,嫦娥和吳剛出現了,紡線的老奶奶坐在織布機旁,盯著遠處相會的夫婦,以及近處的小白兔。
七七意味著什么?七是生命的數字——正月初七是人日,人有七竅,中醫有七傷,人出生后經七七四十九天魂魄成,死后也要七七四十九天魂魄散。兩個七相遇,就成了七夕。
《黃帝內經》里說:“男不過盡八八,女不過盡七七,而天地之精氣皆竭矣。”男子以八歲一個周期,女子以七歲一個周期。男子六十四歲后,精氣衰竭;女子四十九歲后,精氣衰竭。
重點說女子:七歲腎氣盛,換牙齒頭發變長;二七天癸至,任脈通,來月經,可以生子;三七腎氣平均,最后的牙齒長齊,發育完全成熟;四七筋骨堅,頭發長極,身體盛壯,到了頂點;五七陽明脈衰,面容開始焦黃,頭發開始掉;六七三陽脈衰于上,面皆焦,發始白;七七任脈虛,太沖脈衰,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endprint
一個七的輪回是結束,兩個七在一起就是結束后的重生,所以,七七四十九天魂魄散盡,又七七四十九天魂魄豐滿。于是,愛情來了。
除了草木葳蕤,很多花也在這個月盛開,馨香無比,所以七月又叫蘭月。這暗含了女性的意思,故而七夕不僅是情人節,更是女兒節。
那些出嫁、未出嫁的女子,就有了一個專屬于自己的節日。
在我老家,女人們比賽針線活之外,攤煎餅也是一項重要的考量標準。因為煎餅是主要的食物,一個未出嫁的女人如果掌握不了這項技能,很難嫁出去,即使嫁出去了,也要盡快熟悉。要不然,一家老小就沒得吃了。
再過幾天,到了七月十五,就是鬼節。美麗的女子和美好的愛情終于遭遇陰間的考驗,這一天,中元法事開始赦免亡魂們的罪過,讓他們減輕痛苦,早日安息。
聊出來的文學史
豆棚瓜架,并非只有談情的男女,其外延更是進入了中國文學史。
王漁洋評價《聊齋志異》:“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聊齋故事很多就來自于豆棚瓜架下的聊天。經歷了上元節的第一次相會,王子服對嬰寧一見鐘情,在接下來的春天、夏天,兩個人的故事逐漸向深處發展,最終結為夫婦。寧采臣來到蘭若寺,看到寺中殿塔壯麗,而院中茅草卻有一人多高,草木把人阻擋。于是,這個夏天的許多個夜晚,聶小倩橫空出世。
有一年八月十五,老年蒲松齡和妻子孩子坐在豆棚下吃棗聊天,享受天倫之樂。這是他一生中少有的閑適時光,勞作一生的妻子擁著小孫子,臉上的皺紋泛出慈祥的銀光。這個古往今來第一豆棚作家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臉上也浮現出難得的笑容。可惜第二天,因為昨夜感了風寒,妻子病倒了,沒過多久便去世了。
從此之后,豆棚下只剩了蒲松齡孤單的身影。兩年后,他也去世了。
幾百年后,蒲松齡的一個民國粉絲,出于對《聊齋志異》的崇拜,寫了本《女聊齋志異》,從娥皇女英開始,寫盡了歷朝歷代才女、俠女、貞女、情女。
到了乾隆年間,山東嘉祥人曾衍東寫出了一本《小豆棚》,顯然是對《聊齋志異》的模仿,又有所發展,起碼高于同時代的《閱微草堂筆記》。曾衍東說:“我平日好聽人講些閑話;或于行旅時見山川古跡、人事怪異,忙中記取;又或于一二野史家抄本蛤錄,亦無不于忙中翻弄。且當車馬倥傯,兒女嘈雜之下,信筆直書。”
忙里偷閑的小書,塑造了一些光彩奪目的婦女形象,在她們身上所表現出的智、謀、勇,可使須眉黯然失色。
不只有婦女的故事,書里還記載了一些男人。錢塘秀才楊大本,狂放不羈,癡迷寫詩,又好酒。七夕節這天他又喝了酒,寫了一首詩,為天下單身狗鳴不平:“一拳打破支機石,兩手拆坍烏鵲橋。四十鰥夫猶未返,雙星不許度今宵。”
這簡直是大逆不道,拆散牛郎織女還在其次,毀了織女的織布機,讓天下乞巧的女人們怎么活?當然,如果你真能體會到四十歲老光棍的空虛寂寞,這一對你儂我儂的男女當著他的面滾床單就是一種犯罪。
除了以上幾本小說,還有一本《豆棚閑話》,采用人們在豆棚下輪流說故事的方式,串起十二篇故事,類似于《一千零一夜》《十日談》。
彼時,豆棚瓜架成為小說的代名詞,也成為一個時代文學變遷的代名詞。清代,大江南北一個又一個豆棚瓜架下,躲藏著一個個蒲松齡、曾衍東,他們支棱著大耳朵捕捉著婦人口中漏出的故事。那些鄉村“閑話中心”發出的輿論,經過他們的加工,登堂入室,成為文學殿堂里不朽的篇章。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