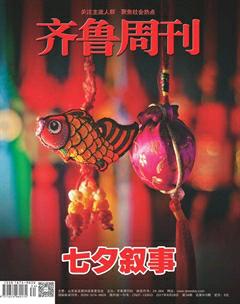信物變遷史
許諾
中國人互贈信物的歷史可以上溯到遠古,不同的人選擇的信物都與其身份相配,與古老的信仰相關。信物是情感的承諾和期許,更是中國式愛情的見證和傳承:所謂定情信物,“情”者,真情也,“信”者,憑證也,既為“定”,不可悔也。
《詩經》時代的情與價
《詩經》中的《靜女》,大概最早記載了美女向男青年贈送禮物的經歷:“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在城邊等待心上人的小伙子得到一支“彤管”,于是有點狗腿的感慨:“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從搔首踟躕到心曠神怡,原因無他,這“彤管”乃定情之物。
“彤管”即白茅,外部紫紅皮,剝開后草芯沁香怡人。因其“根結連理”,所以古人相信,在典禮中用白茅,可以使參與的兩人心相連接。且白茅氣味芬芳,古人講這種芳香之草皆稱為“蘭”,《系辭》亦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白茅還有一用途:分茅裂土,天子以白茅包好一方土壤,分給有功者。獲得這一信物者,就成一方諸侯。以白茅包裹象征天子與諸侯同聲同氣。
《野有死麕》中也提到白茅: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吉士是古代對男子的美稱。但這里的主角不只白茅,還有以白茅包裹的“死麕”:白茅是婚典圣物,鹿則是上古定情的關鍵物品之一。《禮記》記載,婚禮納征也就是下聘禮的環節,鹿皮是男方送給女方最必要的禮物,古人還確信,這鹿皮定情,是先皇伏羲定下的規矩,華夏一族就是受到神鹿庇佑才能如此繁盛萬代。因此詩中小情侶的會面非同尋常,吉士此行,來下聘禮,婚期就在眼前。
除了鹿,據《禮記》記載,古代男女第一次見面到婚禮完成,幾乎每次活動都必不可少的禮物是大雁,祝福婚后夫妻和睦家庭秩序井然。時至今日,民間還有類似“奠雁禮”,不過大雁珍惜,人們便用雞鴨鵝替代。這一習俗傳到韓國,他們婚禮信物則是大雁形的漆器。
實際上,除了習俗、財富的差別,信物也因社會地位而異。比如玉器并非普通人可用,一般情況下更不能贈與女性。為了凸顯貴族特權,天子諸侯在娶妻時向女性贈玉,但女性平日仍不得佩戴。《國語》記載,魯桓公的后宮嬪妃佩玉,被指責為“敗禮”。而在社會分工中負責生產的女性們,則以農耕的勞動成果,特別是水果為身份象征。所以士子贈瓊瑤,女子回報以“木瓜”“木桃”或“木李”。一直到東晉,美男潘安上街一趟,還能收獲一車的水果。
《詩經》時代的戀人,用各種信物盟誓來篤定情緣。這些信物講究“情”而不講究“價”,好似順手拈來,實則無不與信仰相關,它們最終成為中國傳統信物的奠基石。
從“定情”到“納征”:一件信物的自我修養
及至東漢,才子繁欽在長詩《定情詩》中描述了一對戀人定情的經過,其中雙方互送禮物的情節尤其動人。因此,詩中提及的臂釧,戒指,耳環,香囊,手鐲,玉佩,同心結,簪釵,裙,中衣等物件,也成為中國古人定情的十大信物。
實際上,中國古代有大量與定情信物有關的傳說和故事,信物在抒情文學中的出鏡率最高。尤其是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說,簡直到了“無信物、不成書”的地步。曹雪芹總結的到位:“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表定情,或做婚約,雖然是為情節而設,卻也折射出當時社會生活的一個角度。
梳理這些小說中的定情信物,大多是金玉、珍珠、紙布等材質,并以日常用品為主,日久便形成了特定的寓意。如扇與善同音,鞋表示永諧連理等。在互送信物中,女性比男性更加主動,這是因為女性情感細膩,在古代的婚姻關系中,對誓約也更加依賴。總體而言,中國式的愛情信物,大多物微義重,它們精巧,便攜,且持久。
用作山盟海誓的信物不可謂不多,除了私相授受的以外,男方聘禮也屬于信物的范疇,且是非常嚴肅的信物。
中國家族締結婚姻須符合“六禮”,其中“納征”一項最為關鍵,是在“納吉”(合婚)之后,男家下聘禮,女家接受,既是定婚,雙方均不可反悔。聘禮價值一般較高,代表男方誠意,金玉珠寶是主要內容,或許是根據金玉昂貴,其質堅硬難以毀壞的特點,來強調定婚的嚴肅性。
最常用的形式則為簪釵,這是最“正室范兒”的信物,它貼近身體發膚,日夕耳鬢廝磨,完成對永恒的見證。陸游和唐婉的定情物釵頭鳳終因特殊性取代了《擷芳詞》的詞牌;唐玄宗與楊玉環的鎮庫紫磨金步搖成為情感的重要物證,白居易安排他們在《長恨歌》里重逢,也是先要“鈿合金釵寄將去”。清代李漁《閑情偶寄》中便感慨:“一簪一珥,便可相伴一生。”其對簪釵的愛惜和不離不棄,恰如現代婚姻關系中的鉆戒與對戒。
沒有媒妁之言的小情侶要定終身,需借助私密的愛情信物為媒介,或者愛人之間傳遞感情信息,一方手帕頗具此功能。
作為愛情信物,古今中外對手帕有共識。從莎士比亞的《奧賽羅》到狄更斯的《雙城記》,一方手帕都牽動著主人公的命運。而在中世紀,手帕幾乎相當于定婚的戒指,騎士出征前會把繡著自己名字第一個字母的手帕贈送戀人,意思是“讓它代替我,守在你身邊”。與中國不同的是,西方愛情中的手帕較少詩情畫意,更注重人物身份地位,人們紛紛在手帕上繡名字與家族徽章。
另一方面,手帕具有私密性,其蘊含個人的獨特心理,是人內在情感的載體,甚至可以說手帕是人類軀體文明的物化符號。
尺素傳書的文化傳承
有一部電影叫做《愛情的牙齒》,其中一個情節,主人公分手前,用鉗子拔下自己那顆被戀人夸贊的虎牙送給對方,并說,只有疼痛才能讓我記住你。當真是“沒齒難忘”。
上海人將智齒叫做情根齒,據說在懂得愛情的時候才會長出來。當身外之物終究離散,剪下的青絲俱已成灰,當時間讓一切都在爛泥之下衰敗腐朽,牙齒卻永不朽壞。
實際上,定情信物一詞,“情”者,真情也,“信”者,憑證也,既為“定”,不可悔也。既然強調承諾與持久,“沒齒難忘”固然無錯,卻稍顯簡單粗暴。相比之下,信箋則是另一種更具文化傳承的意象。
古人的生活節奏慢,感情的發展也慢,男女情絲便流瀉在信箋上。寫情但覺香箋短,遙以信箋訴衷腸。紙墨文字見證情感,可謂真摯又濃烈的信物。
從古至今,中國不乏信箋定情的故事。烏絲絹上霍小玉癡心成災,碧苔箋后步非煙相思成疾。李清照與趙明誠分離多年魚傳尺素,盛世中訴說與子成說的癡情繾綣,亂世里敘述掩袖伏嘆的情長思戀。及至現代,朱生豪英年早逝,除了一套《莎士比亞全集》,留存的還有寫給妻子的三百份情書。王小波的“愛你就像愛生命”至今是文藝青年們爭相模仿的經典。
斯人已逝,情箋長存。
然而正如魯迅在《北平箋譜》中所言:“文翰之術將更,則箋素之道隨盡”。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花箋上的文才情思,已逐漸被電郵、短信、微信等現代通訊方式所取代,舊日絢爛,在時代面前黯然神傷,徐徐褪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