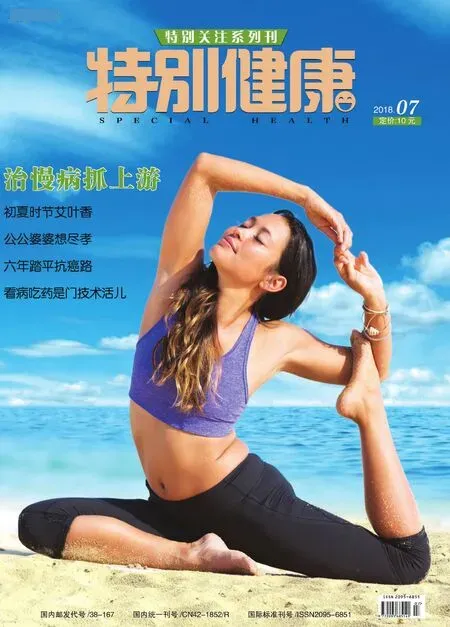我的人死觀
◎王輝
我的人死觀
◎王輝

看到我的這個題目,一定有人說:“你王老漢亂彈琴,人們都講人生觀,你卻講人死觀!”
德國詩人歌德說過:“人活到75歲,總不得不時時想到死,我卻不因此而不安。”所以我講人死觀并不奇怪。對于死亡的徹悟是理性地思考死亡,是宣揚“崇生重死”的人死觀。我聯系耄耋之年的切身感受,提出“三感四不”。
先說三感。首先是超越感。2010年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達到74.83歲,世界各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最高的是日本,達到83.4歲。我87歲,已經超越了我國乃至各國最高平均預期壽命。記得1954年底,我作為南開區委辦公室主任調市委辦公廳工作時,我們共10人曾合影留念。其中5位比我歲數大的,兩位同歲的,兩位比我年歲小的。如今再看那舊照,只有我等三人還在人間。在感慨人生苦短的同時,也萌生一種莫名的超越感。人生就是一場馬拉松長跑,盡可能多跑幾年也好。
其次是了結感。人作為一個社會成員,與他人包括親友之間,與社會組織之間,總是有割舍不斷的聯系。以過春節來說,高齡老人不再考慮登門拜年了,然而電話拜年要考慮先給誰打電話?即使退休在家的老人也需要考慮。人際交往,人情債如何處理?與社會組織的關系,社區有活動參加不參加?你承諾了什么如何兌現?比如我要經常考慮完成我的專欄寫作,經常考慮準備為電臺專欄的講稿……了結一件是一件。拿得起是一種能力,有必要;放得下是一種智慧,更必須。至于未了之事,“人死如燈滅”,只有走人,才徹底了結,至死方休。
第三是歸屬感。人總是要死的。“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我等老人當然“非命促”,更是“任去留”了。英國學者傅勒說:“死亡是最偉大的平等。”印度大詩人泰戈爾說得更有趣:“死亡宛如誕生,都隸屬于生命,正如走路需要抬起腳來,也需要放下去。”我抄錄了這些名言,無非是說人一生忙碌折騰一輩子,最終是要安息的,壽終正寢是幸福的歸宿。以前如行逆水而發奮問知,如今心靈平靜而魂歸未知。
那“四不”是什么呢?
一是不想死,要好好活著。人生都是路過世界,爭取看完更多的風景,這主要不是物質需求,而是精神需求,如果近幾年走人至少就看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了。
二是不找死。如果胡吃海喝,為嘴傷身;邁不開腿,懶動生病,自作自受,自己受罪,“應憐半死白頭翁”。
三是不等死,慎獨其行。不要天天窩在房間里,無所事事,百無聊賴,身心先于生理老化,等待生命盡頭。
四是不怕死,人如太恐懼于死亡,精神便有負擔,心理便會失衡,便影響精神快樂和身體健康。所謂撒手閉眼,不過彈指一揮間,何懼之有?
據托馬斯的統計,地球上“每年有逾5000萬的死亡,在相對悄悄地發生著”。生命是生與死的經歷,是來和去的過程。我們雖來無目的,但愿去有意義。如果有朝一日生命不再有質量,那么在人生的舞臺全身謝幕,視死如生,天之德大矣。天地之間生生不息,死死不已。
摘自《中老年時報》圖/童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