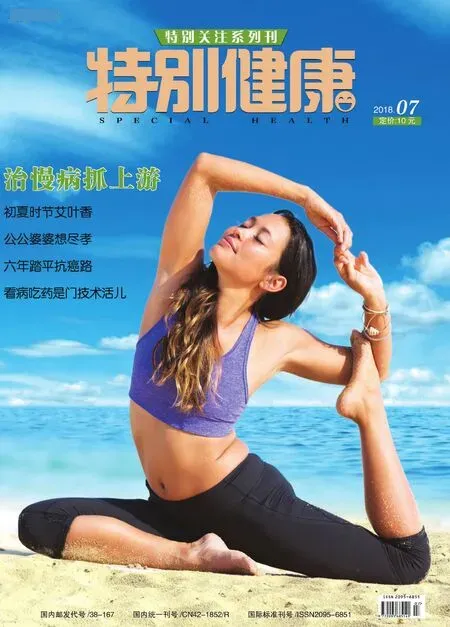少年遇貴人
◎步雄
少年遇貴人
◎步雄

餅里的學問
1970年,我中學畢業,被分配在右安門橋頭兒的“北京汽車修理四廠”炊事班做飯。
張樹勛是食堂的管理員,年近50,胖大,面黑且兇。一天,幾位師傅正教我“卷大炮”(用報紙卷煙葉抽),他見了大罵:“還有良心嗎你們?憋著毀了人家孩子!你小子才多大?混到哪天算一站?要是我兒子,非抽你不可!以后不準瞎胡混,給我學真本事!”這醍醐灌頂的一罵改變了我的一生。
那天,張管理員氣哼哼地教我烙餅。先是和面。他把一袋面倒進碩大的缸盆,面水相兌,馬步弓身、聚神斂息、氣運丹田、雙臂翻花,好似兩條玉龍缸中縱橫,四下里敗鱗殘甲紛然飄落。我這里看得正呆,他“啪”地一個抖腕,白生生、滋潤潤的一團餅面已然飛上案頭。再看那盆中已是盆干面凈。師傅指著說:“看見沒?面是筋骨,水是魂兒,和好面先得兌好水,水要一次兌準,多了沾手,水少了皴皮兒。咱干‘白案兒’的講究個‘三光’——盆光、面光、手光。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行千里路,看第一步。你小子剛參加工作要是百事糊弄,不求上進,將來一準樣樣稀松。”
我墊好了餅,剛要下手搟。師傅用翻餅的大鏟把餅鐺砸得山響,沖我吼:“急什么,多墊幾個,讓它們醒著,這剛墊好的面都有點子筋巴勁,搟得勁小了往回縮,勁大就軋死了不起層。好比你們這些剛剛參加工作的小年輕兒,都有股子浮躁張狂勁。甭急,扔那兒甭理它,讓它自己醒醒。過不了多一會兒就柔了骨、散了神兒,到那時再搟不遲。”
搟餅時,我用搟面杖從那墊得鼓鼓的小墳包似的餅劑子中間往下壓。師傅又急了,他搶過搟面杖,教我從四周圍往中間一圈圈地搟。他說這叫“暈搟”——月暈而風、礎潤而雨,千萬使不得蠻勁。一杠子從中間壓下去,那餅就死了,不起層,要留它心中一口氣在,運上火兒,滿肚子鼓脹起來才能串個層層疊疊。人活著,也就是一口氣,有點毛病說他、勸他,哪怕罵他,也是為他好,都是為激起他那胸中一股陽剛之氣——得,老人家是躍馬縱槍十二招,招招不離我的后腦勺。
幾十年過去了,師傅“以餅悟世,以餅育人”和“醒面”“暈搟”中的哲理,我仍記憶猶新。
十缸清水練秀才
那年頭兒看書犯禁。師哥劉力力有庫房鑰匙,那里面竟堆著很多被查抄和封存的舊書。借上夜班的機會,我竊出很多,一點一點夾在一個紅彤彤的塑料皮里往家拿,不想被張管理員發現了。
“悶頭看,誰也別說,誰也別借!漏了,就得坐飛機(挨批斗),知道嗎?”管理員小聲告誡我說。
一有機會,管理員也幫我往外順,那書雜然相兼,有《悲慘世界》也有《科學育秧100例》。我說:“師傅,想讓我當農民啊?”師傅說:“農民怎么著,沒聽說開卷有益嗎?只有沒用的人,沒有沒用的書,有意思的你給我當故事看,沒意思的你給我當字兒念。記住一個是一個,沒有多看書的不是。”這種秘密的“黑色收授”持續了一年多。
“我就不信十缸清水練不出個筆墨秀才來。”張師傅一股腦兒把食堂里各種文墨活計交給我。從決心書、倡議書、總結、報告,到替師傅們寫的困難申請,文債滾滾而來。寫出的東西,都要先念給他聽。若不好,他沉吟良久說:“不行,疙疙瘩瘩,欠揉。”若文從字順,他當即就捏著我的臉蛋兒叫好:“行,好活兒!”
漸漸地,我養成了一次成功的心性,只為聽到師傅那中氣十足的一聲“好活兒”!直到他逢人就講:“這小子越來越行了,我算整治不了他了。”
回味不夠學廚時光
我渴望上學,機會真就來了。那年,北京經濟學院的招生老師來到工廠招一名“工農兵大學生”,管理員領著食堂的一幫老少堵著門去推薦我。真就事成,貼出了紅榜,可惜臨開學說我肝脾腫大給退了回來。我不服,接連拿下幾個醫院的合格證明,哪里還用得上,是讓人家給“頂”了。
后來,管理員給我找了一間小屋,下班就在里面看書。一個寒夜,屋里很冷,鞋里塞上刨花,正瑟瑟著,管理員給我推來一車“大同塊(煤)”。那煤是從鍋爐房“偷”來的,燒鍋爐的老馬臉酸得很,逮誰罵誰,管理員為了我也是拼了。
我開始經常被借調去辦各種活動、展覽,明白人跟我說,都是你們管理員向著你,見天兒到領導那里坐著說你的好哩。
一天,管理員和我蹬三輪車到很遠的地方去拉糧食,他對我說:“這回,我到底把你給‘鼓搗’出去了,明天會有一個高人領你走的。記住,‘在行恨行,出行想行’,甭管走到哪里,永遠別忘了你的這段廚子的經歷。”我的淚珠子頓時就掉出來了。
第二天,我正在烙餅,一個身著舊軍裝、年屆40的老帥哥兒,走到我跟前,一眼高一眼低地瞄看我。許久才說,“你就是管理員說的那個小秀才嗎?你是喜歡繼續烙餅啊,還是愿意跟我學‘吹喇叭’‘抬轎子’?”看我疑惑,老帥哥仰天大笑說:“一看就是一老實巴交的孩子,走,跟我干吧!”
他叫徐聲桐,參加過抗美援朝,時任我們廠的宣傳科長。當天,我被調到了宣傳科。幾年后,我終于考上了夢寐以求的北京經濟學院。
“在行恨行,出行想行”,離開百味雜陳的廚房已經是幾十年前的事情了,但總是回味不夠。那里的人情世故濃縮著煎、炒、烹、炸的人間百味,此后不曾有過。張管理員學徒出身,吃過大苦,不愿我重蹈他的覆轍,像疼兒子一樣疼我。少年遇貴人,我之大幸!
摘自《北京紀事》2016年第7期 圖/袁大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