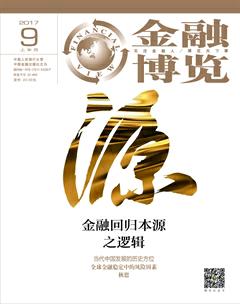父親的節日
翟海濤
今年父親節來臨的前幾天,出差的路上,兒子打來電話,向我問候。感動之余,不禁想起我的父親來,長這么大,我幾乎沒有給他過過父親節。這個西方傳來的節日這些年很流行,但我這個喝過洋墨水的兒子除了打個電話說幾句父親節快樂之類的話,大都不在他身邊,反倒是沒受過西方教育的弟弟妹妹每年為父親過節。
若從上大學那年算,我已離家31年了。上學期間每年只有兩個假期回家和父母在一起。后來出國留學、工作,離父母越來越遠,見面越來越少。起初他們每年還愿意過來和我們住上一段時間,之后年邁的父母就不太愿意動了。
父親出身貧寒,幼年是個苦命的孩子,饑荒無情地奪去了他的雙親。我記得小時候看到他的兄弟都比他高很多,一度懷疑他不是我從未見過的爺爺奶奶親生的,后來才知道他是發育不良。幼時羸弱的父親性格倔強,天資聰穎,他通過刻苦學習成為村里歷史上第一個大學生。窮得丁當響的家里哪有錢給他路費?東借西湊也才從全村“眾籌”到五塊錢。我至今都沒弄清楚他是怎么從豫東偏僻的鄉下到達開封的。
父親大學的專業是中文,他寫得一筆好字,尤其喜愛古文和格律詩詞。這個大學時期培養的愛好讓他受益終生,特別是退休以后,認真的父親花了很多功夫研究格律,以詩會友,不恥下問。有心人終修成正果,他在七十歲時出版了詩集。我們做子女的看到他晚年能保持如此雅興,并且有益于身體健康,一方面高興,另一方面也不禁自問:當自己退休了,能像父親這樣充實么?
父親年輕時性格比較急,時不時發脾氣,只有對小妹是例外。這種重女輕男的家風被我毫無保留地繼承下來,以至于我的心被公認為偏得厲害。但除這一條外,父親曾是一個典型的大男子主義者,年輕時鮮有動手做家務,恪守“大男人遠廚房”的信條。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到了晚年,父親卻是頻頻出入廚房,冬天基本上都是他做早飯,蒸饅頭和面這類重活更是一手包辦,怕累著母親。我跟他開玩笑:人一輩子要干的活是定好的,就像能量守恒,年輕時候干得少,以后就得補上。不過我也時常以此為戒。
年逾古稀的父親不僅身子骨硬朗,更難得的是他還保持一顆年輕的心和積極擁抱新鮮事物的精神。他比我更早學會用微信,而且用起來得心應手。他是他們大學班級的群主,已經組織了好幾次聚會活動;他的新作都是在微信朋友圈里首發,還組建了研究格律的群;他和母親外出旅游,都是以圖片甚至視頻來報平安……
和中國大部分父親一樣,我的父親經歷了從“嚴”到”慈”的轉變。我很小的時候父親便每天手抄幾首古詩詞,作為我的晨起必背;而我盡管不情愿,卻不敢稍有懈怠。那時候就想,長大了一定要考出去,逃脫這日復一日的精神折磨。直到多年以后我才體會到,正是兒時這般填鴨式的教育幫我打下了扎實的文字功底。后來我自己成了人父,發現對付兒子的招數基本上是抄襲幾十年前父親用過的。好笑的是,父親這時候反倒來勸我:對孩子不要太嚴厲,要順其自然……
和中國大部分兒子一樣,我也經歷了對“父愛如山”這個詞的不同理解。小時候覺得這座山很高大、威嚴;進入青春期,便逐漸覺得這座山擋道、礙事,要繞過去;自從上了大學,更是以為在精神和思想上獨立自主了,不需要再聽父親的訓導了;工作、成家以后和父親交流就更少了。奇怪的是,步入中年以后,那種久違的對父親的依賴感覺不知不覺又回來了,有時候主動想聽聽他對某些事情的看法,哪怕聊一聊也好。與此同時,自己也感受到了作為父親的那份如山的責任、壓力和擔當。
父親常跟人說,他這輩子最驕傲的是子女超過了他。其實,如果沒有他和母親的培養,哪有我們的今天!我年少輕狂之時對此體會不深,仿佛自己就是那只從石頭里蹦出來的猴子。步入中年,愈發感覺到父親的影響和呵護無時無刻無處不在!
記得有一次幫女兒補習中文,讀朱自清先生的《背影》。當讀到“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我也不禁淚眼婆娑。我想起了上大學報到的那一天,父母親把我送進宿舍。父親一口氣沒歇,便爬到我分得的上鋪,為我整理東西。空間狹促,好幾次頭都碰到天花板……
又是一年父親節,我會大聲說:爸爸,我愛你!(作者為春華資本CEO)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