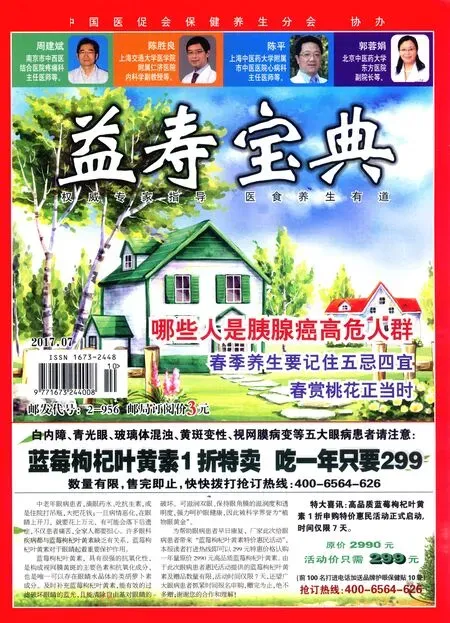老年十忌
文/季羨林
老年十忌
文/季羨林

忌,就是禁忌,指不應該做的事情。人的一生,都有一些不應該做的事情,這是共性。老年是人生的一個階段,有一些獨特的不應該做的事情,這是特性。老年禁忌不一定有十個,我因受傳統的“十全大補”“某某十景”之類的“十”字迷的影響,姑先定為十個。
一忌說話太多
說話,除了啞巴以外,是每人每天必有的行動。有的人喜歡說話,有的人不喜歡,這決定于一個人的秉性,不能強求一律。我在這里講“忌說話太多”,并沒有“禍從口出”或“金人三緘其口”的含義。說話惹禍,不在話多話少,有時候,一句話就能惹大禍。口舌惹禍,也不限于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年人都可能由此致禍。
我編了四句話。奉獻給老人:年老之人,血氣已衰;煞車失靈,戒之在說。
二忌倚老賣老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周恩來招待外賓后,有時候會把參加招待的中國同志在外賓走后留下來,談一談招待中有什么問題或紕漏,有點總結經驗的意味。這時候剛才外賓在時嚴肅的場面一變而為輕松活潑,大家都爭著發言,談笑風生,有時候一直談到深夜。有一次,總理發言時使用了中國常見的“倚老賣老”這個詞兒。翻譯一時有點遲疑,不知道怎樣恰如其分地譯成英文。總理注意到了,于是在客人走后就留下中國同志,議論如何翻譯好這個詞兒。
平心而論,人老了,不能說是什么好事,老態龍鐘,惹人厭惡;但也不能說是什么壞事。人一老,經驗豐富,識多見廣。他們的經驗,有時會對個人甚至對國家有些用處。但是,這種用處是必須經過事實證明的,自己一廂情愿地認為有用處,是不會取信于人的。另外,根據我個人的體驗與觀察,一個人,老年人當然也包括在里面,最不喜歡別人瞧不起他。一感覺到自己受了怠慢,心里便不是滋味,甚至怒從心頭起,拂袖而去。有時鬧得雙方都不愉快,甚至結下怨仇。這是完全要不得的。一個人受不受人尊敬,完全取決于你有沒有值得別人尊敬的地方。在這里,擺架子,倚老賣老,都是枉然的。
三忌思想僵化
人一老,在生理上必然會老化;在心理上或思想上,就會僵化。此事理之所必然,不足為怪。要舉典型,有魯迅的九斤老太在。
從生理上來看,人的軀體是由血、肉、骨等物質的東西構成的,是物質的東西就必然要變化、老化,以至于消逝。生理的變化和老化必然影響心理或思想,這是無法抗御的。但是,變化、老化或僵化卻因人而異,并不能一視同仁。有的人早,有的人晚;有的人快,有的人慢。所謂老年癡呆癥,只是老化的一個表現形式。
四忌不肯服老
服老,《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承認年老”,可謂簡明扼要。人上了年紀,是一個客觀事實,服老就是承認它,這是唯物主義的態度。反之,不承認,也就是不服老,倒跡近唯心了。
中國古代的歷史記載和古典小說中,不服老的例子不可勝數,盡人皆知,無須列舉。但是,有一點我必須在這里指出來:古今論者大都為不服老唱贊歌,這有點失于偏頗,絕對地無條件地贊美不服老,有害無益。
也有人過于服老。年不到五十,就不敢吃蛋黃和動物內臟,怕膽固醇增高。這樣的超前服老,我是不敢欽佩的。
然則何去何從呢?我認為,在戰略上要不服老,在戰術上要服老,二者結合,庶幾近之。
五忌無所事事
現在我只能談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分子,因而我是最了解情況的知識分子。國家給年老的知識分子規定了退休年齡,這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知識分子行當不同,身體條件也不相同。是否能做到老有所為,完全取決于自己,不取決于政府。自然科學和技術,我不懂,不敢瞎說。至于人文社會科學,則我是頗為熟悉的。一般說來,社會科學的研究不靠天才火花一時的迸發,而靠長期積累。一個人到了六十多歲退休的關頭,往往正是知識積累和資料積累達到爐火純青的時候。一旦退下,對國家和個人都是一個損失。有進取心有干勁者,可能還會繼續干下去的。可是大多數人則無所事事。我在南北幾個大學中都聽到了有關“散步教授”的說法,就是一個退休教授天天在校園里溜達,成了全校著名的人物。我沒同“散步教授”談過話,不知道他是怎樣想的。估計他也不會很舒服。鍛煉身體,無可厚非。但是,整天這樣“鍛煉”,不也太乏味太單調了嗎?學海無涯,何妨再跳進去游泳一番,再扎上兩個猛子,不也會身心兩健嗎?
六忌提當年勇
在蕓蕓眾生中,特別是在老年中,確有一些人靠自夸當年勇來過日子。我認為,這也算是一種自然現象。爭勝好強也許是人類的一種本能。但一旦年老,爭勝有心,好強無力,便難免產生一種自卑情結。可又不甘心自卑,于是只有靠自夸當年勇,來聊以自慰。對于這種情況,別人是愛莫能助的。“解鈴還須系鈴人”,只有靠自己隨時警惕為宜。
現在有一些得了世界冠軍的運動員有一句口頭禪:從零開始。意思是,不管冠軍或金牌多么燦爛輝煌,一旦到手,即成過去,從現在起又要從零開始了。
我覺得,從零開始是唯一正確的想法。
七忌自我封閉
能活到老年,是一種幸福,但也是一種災難。并不是每個人都能活到老年,所以說是幸福;但是老年又有老年的難處,所以說這又是災難。
老年人最常見的現象或者災難是自我封閉。封閉,有行動上的封閉,有思想感情上的封閉,形式和程度又因人而異。老年人有事理廣達者,有事理欠通達者。前者比較能認清宇宙萬物以及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了解到事物的改變是絕對的,不變是相對的,千萬不要要求事物永恒不變。后者則相反,他們要求事物永恒不變;即使變,也是越變越壞,上面講到的九斤老太就屬于此類人。這一類人,即使仍然活躍在人群中,但在思想感情方面,他們卻把自己嚴密地封閉起來了。這是最常見的一種自我封閉的形式。
我認為,老年人不管有什么形式的自我封閉現象,都是對個人健康不利的。我奉勸普天下老年人力矯此弊。同青年人在一起,即使是“新新人類”吧,他們身上的活力總會感染老年人的。
八忌嘆老嗟貧
嘆老磋貧,在中國的讀書人中是常見的現象,特別在所謂懷才不遇的人們中更是突出。
中國知識分子一向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今天,時代變了。但是“學而優則仕”的幽靈未泯,學士、碩士、博士、院士代替了秀才、舉人、進士、狀元。骨子里并沒有大變。在當今知識分子中,一旦有了點成就,便立即戴上一頂烏紗帽,這現象難道還少見嗎?
今天的中國社會已能跟上世界潮流,但是,封建思想的殘余還不容忽視。我們都要加以警惕。
九忌老想到死
好生惡死,為所有生物之本能。我們只能加以尊重,不能妄加評論。
作為萬物之靈的人,更是不能例外。俗話說:“黃泉路上無老少。”可是人一到了老年,特別是耄耋之年,離那個長滿了野百合花的地方越來越近了,此時常想到死,更是非常自然的。
老年人想到死,是非常自然的。關鍵是:想到以后,自己抱什么態度。惶惶不可終日,甚至飲恨吞聲,最要不得,這樣必將成陶淵明所說的“促齡具”。最正確的態度是順其自然,泰然處之。
我在這里誠摯奉勸普天之下的年老又通達事理的人,偶爾想一下死,是可以的,但不必老想。我希望大家都像我一樣,以陶淵明《神釋》詩最后四句為座右銘(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十忌憤世嫉俗
憤世嫉俗這個現象,沒有時代的限制,也沒有年齡的限制。古今皆有,老少具備,但以年紀大的人為多。它對人的心理和生理都會有很大的危害,也不利于社會的安定團結。
我也算是一個知識分子,姑以我自己為麻雀,加以剖析。憤世嫉俗的情緒和言論,我也是有的。但是,我又有我自己的表現方式。我往往不是看到社會上的一些不正常現象而牢騷滿腹,怪話連篇,而是迷惑不解,惶恐不安。我曾寫文章贊美過代溝,說代溝是人類進步的象征。這是我真實的想法。可是到了目前,我自己也傻了眼,橫亙在我眼前的像我這樣老一代人和一些“新人類”“新新人類”之間的代溝,突然顯得其闊無限,其深無底,簡直無法逾越了,仿佛把人類歷史斷成了兩截。我感到恐慌,我不知道這樣發展下去將伊于胡底。我個人認為。這也是憤世嫉俗的一種表現形式,是要不得的;可我一時又改變不過來,為之奈何!
我不知道,與我想法相同或者相似的有沒有人在,有的話,究竟有多少人。我想來想去,覺得還是毛澤東的兩句詩好:“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常宜放眼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