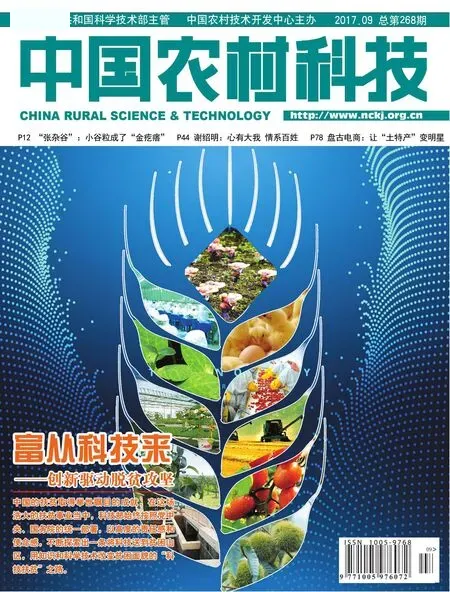謝紹明:心有大我 情系百姓
本刊記者|王雯慧
謝紹明:心有大我 情系百姓
本刊記者|王雯慧

2006年4月,原國家科委顧問謝紹明以82歲高齡重返大別山,關心農民的產業發展和脫貧增收情況。
他出生于革命家庭,全家有九口人為了革命流血犧牲,深植于血液的信仰讓他時刻掛念著貧苦農民。他曾到蘇聯留學,為我國的航空工業做出貢獻。他是科技扶貧的率先探索與實踐者,從南到北、由東至西,他走遍了中國這片土地上最貧窮的地方。他說,唯有科技才能真正解決貧困,讓老百姓富起來。
于漫漫歷史,人生何其短暫,于浩渺星空,人是如此渺小。但有一些人,他們心有大我,對貧苦百姓愛得深沉,他們將情懷付諸實踐并為此奮斗一生,這樣的生命注定不平凡。
1925年,謝紹明出生于陜西延安。他是謝子長將軍的兒子,十四歲即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去蘇聯留學,為我國的國防事業做出貢獻。他是科技扶貧的率先實踐和推動者,從戰爭到和平,他的命運跌宕起伏……
2017年7月,記者第一次見到了謝紹明。如今已經92歲的他,眼角和臉部的肌肉有明顯下垂的痕跡,背有些曲駝,兩鬢皆霜,他的身上散發出一種久經歲月沉淀的柔和與淡然。
“現在扶貧工作做得怎么樣?老百姓生活過得怎么樣?”還不等記者做完自我介紹,謝紹明便急切地問詢起身邊的工作人員扶貧情況。
他聽得很仔細,隨行的一名工作人員說到“掛職”一詞時,謝紹明連忙打斷:“扶貧有沒有掛職的,都在哪里掛職?有沒有好好干?”說起與扶貧有關的事,他的眼睛亮了起來,那顆心系貧苦百姓的赤子之心從言語間流露……
賡續信仰 心系貧苦農民
大雪了無痕,英雄有跡可循。一個人的信仰與情懷總是與其獨特的成長環境和心路歷程有關。
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陜北延安,有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他面對敵人時像雷電一樣凜冽,對待貧苦百姓像親人一樣溫暖。這便是謝紹明的父親——謝子長。
謝子長出生于1897年,他和劉志丹一起創建了西北革命根據地,是陜北紅軍和蘇區主要創建人和中國工農紅軍高級將領。他組織創辦農民講習所,組織農民協會,領導人民參加反帝、反軍閥運動,被當地百姓親切地稱為“謝青天”。1934年謝子長在河口之役時負傷,1935年2月因傷與世長辭,年僅三十七歲。為了紀念謝子長創建陜北根據地的功績,中共西北工委把他的家鄉陜北安定縣改名為子長縣。

謝紹明
謝紹明說,“在我八九歲的時候,我們老家就被國民黨占領了。因為我父親的緣故,敵人圍剿時只要是跟謝家有關系的人,抓住就殺。我家直系親屬中,參加革命17人,為革命流血犧牲的就有9個。在我父親養傷期間,我一直和他在一起,他告訴我,要為人民做事。”
往事娓娓道來,仿佛看到了黎明前的延河故土,那些懷揣民族大義的有識之士與敵人殊死搏斗的身影。
謝子長去世時,謝紹明剛剛10歲。“我父親在彌留之際說的最后一句話就是,‘我對不起眾鄉親,我為他們做的事情太少了!’”父親臨終前的牽掛,根植于謝紹明的記憶之中,也成了他日后的精神指引和人生所向。
攻堅克難 為航空工業添磚加瓦
謝紹明在革命家庭中鍛煉與成長,從八九歲開始,兒童團、雞毛信、放哨、捎路條……這些電影里的情節是他真實的童年記憶。
1939年,十四歲的謝紹明加入中國共產黨。1945年日本投降,年僅20歲的謝紹明成為中共中央派往東北的干部之一。1948年,為了給即將成立的新中國培養一批高層次的建設人才,中共中央選派謝紹明、李鵬、鄒家華等人赴蘇聯莫斯科大學學習。1954年謝紹明第二次留蘇,回國后,先后擔任哈爾濱飛機發動機廠副廠長、沈陽一一九廠廠長等職。那時候,廠里隨處可見蘇聯專家的身影。

謝紹明(左二)深入大別山區走訪貧困戶
到了1960年,中蘇關系惡化,蘇聯專家撤走,可是很多技術都到了緊要關頭。不服輸的謝紹明心懷黨和國家對他的期望,他深知航天工業對祖國意味著什么。他組織攻關小組攻堅克難,和工人們同吃同住,咸菜就著窩窩頭,經常是饑一頓飽一頓,在廠里一住就是幾個月,就連妻子分娩也錯過了。
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1963年,地對空戰術導彈的心臟——自動駕駛儀終于在一一九廠研制成功。1975年,謝紹明調入北京,參與國防工辦主持的《戰術導彈十年規劃》。1981年謝紹明調入國家科委,直至離休時任國家科委顧問。
篳路藍縷 從大別山開始科技扶貧之路
春秋荏苒,謝紹明為國家的航空工業耕耘幾十年,但他始終記得父親遺愿。他說:“開頭幾十年我一直在軍工部門,從航空工廠到導彈工廠,這是國家的需要。為貧苦老百姓做事,才更是我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我們什么時候也不能忘了農民。”
1986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萬里給國家科委主任宋健出了個題目:“能不能用科學技術幫助革命老區百姓解決溫飽問題?”這一年,謝紹明61歲,他主動參與到國家科委的科技扶貧領導工作中。
老百姓到底過得怎樣?怎樣用科技的力量幫助老百姓脫貧致富?謝紹明帶著調查組來到大別山區。
“我們先去了大別山地區轉了一圈,首先是到了湖北黃岡的英山縣、羅田縣,安徽省的金寨縣、潛山縣和太湖這幾個地方,還到了河南的信陽。”
謝紹明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解放快40年了,大別山的老百姓還是那么窮。“吃飯沒有米,穿衣沒有布,房子還是土胚房。我去到一戶人家,吃的還是政府的救濟糧,一塊豬皮就是一家人半年的食油,還有些人家連個灶臺都沒有,幾塊石頭支起一口鍋……”直到現在,謝紹明還清楚地記得第一次到大別山的情景。
從大別山回來后,謝紹明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大別山培育過多少優秀的戰士啊!他們為了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而流血犧牲,可是如今,解放快40年了,大別山的老百姓還是這么窮!
懷揣著對貧苦百姓的悲憫和愛,謹記父親的遺愿,謝紹明全身心投入到科技扶貧工作中來,他要讓革命老區的貧苦百姓過上好日子。“我們不能忘了貧苦農民,不能對不起他們。”
經過實地走訪調研,謝紹明了解了大別山地區的基本情況。“大別山以南屬于長江流域,以北屬于黃河流域。老百姓世代以種桑養蠶為生。在英山縣,一些農戶種茶賣茶葉,我們到賣茶葉的市場上看,都是一些比較粗糙的老茶,賣幾分錢一斤都沒人要……在羅田,板栗樹倒是很多,但是產量不高,一棵樹上就結幾斤板栗。”
知道了問題所在,才能對癥下藥。謝紹明帶著這些問題反復和國家科委領導及地方領導、科技人員研討。沒過多久,他再次帶隊來到了大別山,這次一同進山的還有來自農業大學、地方農科院的一批科技人員。
“我們調了一批科技人員,分別到大別山區的六個縣。那時候一個縣里面只能派一名科技人員,最多兩名,人多了連路費都出不起,條件很艱苦。就這樣我們國家科委派的人和鄂豫皖三個省派的人,慢慢形成科技扶貧團……”謝紹明回憶道。
不辭辛勞 踏遍山河萬里
從大別山開始,科技扶貧的序幕由此拉開。從此,一年四季,不論嚴寒酷暑,不懼山高路遠,謝紹明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他的心里始終惦記著貧困百姓。
“有一次我到安徽金寨訪問的時候,一個老太太問我,外面是不是又打仗了,你們沒處跑了又跑到我們這里來了?”
“還有一次我去湖北鄖西縣考察,我們就走路到村子里。山坡上有那么幾戶人家,我去院子里一看,站著一個30多歲的男的,旁邊站著一個十來歲的小姑娘,還有一個瞎子老頭,地上有一小堆地瓜,還有一小堆苞米。我就問老太太,你怎么睡覺?她指著一堆稻草說,那就是我睡覺的地方。”
謝紹明一次次被眼前這些貧窮所震撼。“他們過得實在是太苦了。”因此,他的腳步不斷向前。
1992年,謝紹明來到青海牧區調研。“宋健讓我去青海牧區看看,說是牧民的皮毛都讓小商販把錢賺了。”這一次到了牧區以后,謝紹明走訪當地的牧民了解情況,去市場上了解行情。然后向牧民提出組織牧民合作社的建議。“這樣牧民就可以自己組織起來,把皮毛拿到市場上去賣,錢就不被小商販賺了,牧民手里才能有錢。”青海牧民合作社便由此成立。
年復一年,謝紹明幾乎走遍了祖國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最窮的地方。他的腳步從大別山、井岡山、到陜北延安;從貴州黔西南苗族地區,到北方邊疆的赫哲族地區,和南邊的海南黎族地區。很多地方連路都沒有,步行兩三個小時是平常事。一遍遍的走訪調研,了解情況,根據當地的自然資源和環境對癥下藥,引進新品種和新技術,示范推廣,發展產業,讓科技發揮最大的作用。湖北羅田的板栗,陜北的紅棗,英山的茶葉,這一個又一個的產業無不凝聚著科技人員的心血。
身體力行 凝聚社會力量
消除貧困是人類共同的事業,中國的科技扶貧從革命老區拉開戰線,逐漸擴散到全國,也感染了一大批心系祖國貧困地區發展的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
1992年,香港浸會大學理學院院長吳清輝教授組織“香港學者協會大別山考察團”,對大別山地區的科技扶貧工作進行了實地考察。通過這次考察,學者們一致認為科技扶貧是偏遠貧困地區發展的可行路子。
為了號召社會力量廣泛參與到科技扶貧工作中來,1993年6月,謝紹明率團赴香港,向香港各界介紹科技扶貧的情況與成果,與香港實業界座談。同年12月,香港學者協會發起和籌集正式設立了“振華科技扶貧獎勵基金”,用于獎勵在扶貧第一線的科技人員。
只有科技人員得到相應的待遇,才有勁頭才能更好地為農民辦事。謝紹明惦記著貧苦農民,也惦記著那些為農民做事情的人。1995年,在謝紹明的積極奔走下,“王義錫科技扶貧獎勵基金”成立。
“王義錫是一位老黨員,也是大型民營企業—青島面粉機械廠原廠長,是一位優秀的民辦科技企業家。王義錫捐的錢用來鼓勵和支持在老(革命老區)、少(少數民族地區)、邊(邊疆地區)、窮地區科技扶貧工作的科技人員。”
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到科技扶貧事業,越來越多的社會力量廣泛參與到扶貧中來。謝紹明的心里是欣慰的,因為在他的心里,沒有比讓貧苦農民過上好日子更重要的事情。
赤子之心 識人與諫言
如果一個人對信仰保持執著,對世界保持單純與熱情,這種感情我們常常稱之為“赤子之心”。謝紹明便是這樣一個人,在他的心里,誰對老百姓好,對農民好,誰就是一個很不錯的人。他說,自己記性不好了,不如從前了。但說起扶貧的事,講起扶貧的人,他的記憶無比清晰。
董水根就是謝紹明口中那個不錯的人。

謝紹明與本刊記者(拍攝于2017年7月)
“董水根這個人很不錯,他原來是安徽農科院派去潛山縣搞扶貧的,掛職副縣長。他去以后,大力發展茶葉,搞了一種叫做劍毫的茶葉,這種茶葉泡在水里能豎起來,跟劍一樣。他把這種茶葉用天柱山命名,叫天柱山劍毫。后來這個地方的茶一下子從幾塊錢一斤賣到了八九百塊一斤。他本來是掛職副縣長,后來老百姓舍不得他走,他就把老婆孩子都帶到那兒去了。再后來他得了癌癥去世了……天柱山劍毫茶葉到現在還很有名。”
“張力田也是個很不錯的人,張力田是湖北省農科院的一位科技人員、板栗專家。他剛到羅田縣那一年,跑到山上去一看,一棵樹上就掛幾顆板栗。原來是樹的雄花多,雌花少,問題就出在這兒。他研制了一種藥水,滴在板栗樹的根上,第二年雌花就多了,雌花多了掛果就多了。后來他長期駐扎在羅田縣,教老百姓技術,發展板栗產業,現在羅田已經成了主要的板栗供應基地……”
對于關心老百姓的人,謝紹明總是不吝贊美,這是因為他對貧苦百姓愛得深沉,也源自于從小根植于內心的信念。
“我受的教育就是共產黨都是農民的孩子,都是窮人的孩子,所以我們不能忘了農民!”謝紹明說,“那一年我給胡錦濤寫過一封信,我的建議就是要減輕貧困地區農民的負擔。”
事實上,這并不是謝紹明第一次給領導人寫信。早在1994年,謝紹明在給國務院領導的報告中建議,組織向貧困地區捐贈衣物的活動。這份報告得到了國務院領導的批復,由此,中央各機關、軍委各單位、北京及省委等單位掀起了一場向貧困地區捐贈愛心衣物的活動,這場愛心義舉活動為貧困地區的兒童送去了溫暖。
“你們要替我到大別山去看一看”
聽謝紹明講過去的往事,仿佛看到了十來歲的他在延安當“小兵張嘎”時的意氣風發,又仿佛看到了他在青年時期為了建設新中國的闖勁兒,亦或是61歲的他踏上大別山時的情景。那些真實發生過的場景時而清晰時而模糊,但走過的路不會不留痕跡。
謝紹明說:“我最后一次到大別山是2006年,那是在我做完心臟搭橋手術以后,我就想去看看大別山怎么樣,有沒有變化。我看到老百姓把土坯房子都變成了磚瓦房,茶園也管理得很好,板栗也長得好……我們還是做了一點事情的,還是有一點收獲的。”
他的臉上露出些欣慰的神情,語速加快,聲音變得昂揚。
“‘房子可以沖掉,田地可以沖掉,但是我腦子里的科技沖不掉!’這是一位因科技扶貧而富強起來的農民在遭受洪災而一無所有時說的話。”謝紹明一直清楚地記得那位農民說這句話時的自信和堅強。
“依靠科技脫貧致富,我到現在還惦記著這個事情。現在國家富裕一點了,錢多一點了,政策也很好了。我覺得科技扶貧的力度可以再加大一點。”謝紹明說。
同行的人說,“謝老一說起科技扶貧就激動,他現在身體不適合長途跋涉……”采訪結束時,謝紹明站起身來送記者。他的背有些曲駝,行動也有些緩慢。他說,“我還想到大別山去……我走不動了。你們要多到貧困地區去走一走,替我去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