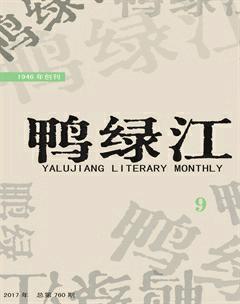詩人汪國真鮮為人知的小說和日記
眾所周知,汪國真先生是一位深受廣大讀者喜愛、作品暢銷國內圖書市場、影響了成千上萬名詩歌愛好者的優秀詩人。他創作的《我微笑著走向生活》《熱愛生命》《山高路遠》《如果生活不夠慷慨》《只要彼此愛過一次》《感謝》等一批抒情勵志、膾炙人口的詩歌作品曾經風靡上世紀90年代中國詩壇,并在全國掀起了一浪高過一浪、一波強過一波的“汪國真詩歌熱”,影響了整整一代讀者。
然而鮮為人知的是,在汪國真先生寫詩成名之前,在暨南大學讀大學的他曾經在母校編印出版的文學作品集中發表過一篇短篇小說、兩首詩歌和三則日記。
要說發現汪國真的小說、詩歌和日記這件事的來龍去脈,話就長了。
那就要從我和汪國真的交往說起。
2012年10月,在我創辦的八十年代詩歌紀念館開館前夕,我給汪國真老師發去短信,請他來大興安嶺參加開館儀式。然而,由于工作太忙,無法抽出時間,他表示以后有機會再來看看我的詩歌館。10月10日,詩歌館開館前,我意外地收到了他從北京發來的賀電,令我喜出望外:“上世紀八十年代,是一個詩情澎湃新人輩出的年代。在此八十年代詩歌紀念館開館之際,謹表祝賀!”
2013年6月16日,我在孔夫子舊書網上買到了一本暨南大學中文系1982年6月編印的文藝作品集《鴻爪》,發現里面居然刊登著汪國真在大學時期創作的短篇小說《丹櫻》、詩歌《鄉思》(二首)和《僑校生活日記三則》。于是,我給他發去短信告訴這個好消息,他收到我的短信后十分驚訝,也非常高興:因為這本書已經出版了三十多年,現在能保存下來的已屬鳳毛麟角,而且他自己都沒有這本書了。
說到汪國真的小說、詩歌和日記,那就不能不提到他的大學時代。
1978年10月,汪國真從北京踏上了南行的列車。這次南行,完成了他人生旅途的一個重大轉折——從一個普普通通的年輕人,一躍成為令許多年輕人都羨慕的暨南大學中文系學生。
暨南大學位于廣州南郊,“文革”期間曾長期停辦,這年10月,暨南大學迎來了她復辦后的第一批大學生。
暨南大學的校園是美麗的,波光瀲滟的明湖、郁郁蔥蔥的桉樹組成的林蔭道、淡黃色的學生宿舍樓、外形很像蒙古包造型別致的學生飯堂,以及在廣東高校中最為漂亮的游泳池,這些都給初入校門的汪國真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進入暨南大學讀書之后,汪國真在學習之余最大的愛好就是跑圖書館和閱覽室,看他喜歡看的文學類圖書和文學類報刊。在他們的六人寢室里,汪國真是借閱圖書和雜志最多、最勤的一個。
1978年,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指引下,社會的改革開放,思想解放的潮流,以及各種文化思潮的碰撞,對剛剛考入大學的大學生們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受這股思想解放、改革開放浪潮的影響,全國各地高校大批熱愛文學、有理想、有抱負、有頭腦、有才華的大學生猶如火山噴發一樣,自發地掀起了文學刊物創辦熱潮。其中,有曲阜師院創辦的《五四詩刊》,北京大學創辦的《早晨》,福州大學創辦的《春潮涌》詩叢,武漢大學創辦的《珞珈山》等一批學生參與創辦的詩歌刊物和文學刊物。據不完全統計,1978年—1979年全國有一百余所高校編印出版了大學生文學刊物二百余種。大學生文學刊物的創辦,給大學生帶來了文學啟蒙、精神創新和思想解放,在校內引起了強烈反響,而且在校外也產生了巨大影響,并成為當年最流行的一種主流文化現象。
受這種辦刊熱的影響,一批愛好詩歌的暨南大學學生也投入到辦刊潮中。在汪國真進入暨南大學不久,系里的同學們自己編輯了一份油印刊物《長歌》詩刊。由于這份刊物傾注了同學們的熱情和心血,大家都很珍視這份刊物,也樂意把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拿到刊物上發表。當時,汪國真寫了一組詩,叫《學校的一天》,發表在《長歌》詩刊創刊號上。捧著那期散發著油墨香的刊物,汪國真甭提有多高興了!因為這是自己的詩歌作品第一次在刊物上刊登,盡管,這是一本僅僅在校內發行的油印詩歌刊物。
讓汪國真更高興的事還在后頭。
1979年4月13日中午,他正在學校飯堂吃飯,系里的同學陳建平興沖沖地跑來告訴他:“汪國真,你的詩在《中國青年報》發表了。”“你別騙我了,我從來沒有給中青報投過稿。”“真的,一點不騙你。”陳建平一臉正經,一點開玩笑的意思都沒有。“是什么內容的?”汪國真有點半信半疑了,腦海里瞬間閃過種種猜測。“好像是寫校園生活的,是由幾首小詩組成的。”陳建平說。聽了陳建平的話,汪國真信了。因為他知道自己寫了這樣一組詩。
當時學校為系里的學生訂了幾份報紙,男生宿舍訂的是《南方日報》,女生宿舍是《中國青年報》,汪國真要看到這張紙必須去女生宿舍找。于是,他跑到女生宿舍找到了報紙,匆匆瀏覽了一下,很快找到了印有他作品的那一版。“我借去看一下。”在征得了女同學的同意之后,他懷著一種極其興奮的心情跑出了女生宿舍樓。“我的作品發表了!”手中拿著那張報紙,他激動地喊了起來。“我最初的文學生涯便是從這組詩開始的,連我自己也沒有想到的是,正是這組詩的作者,在十二年后,在中國大地上掀起了人們稱之的‘汪國真風潮。”
汪國真的這組詩是由五首小詩組成的,題目叫《學校的一天》,發表在《中國青年報》1979年4月12日第三版《校園生活》專欄。在那期專欄的《編者的話》中,編輯寫道:“讀了這一組稿子,校園里的青春氣息撲面而來。學生時期精力旺盛、活潑好動,在功課既完而有余暇時,團組織為他們組織一些時事報告會、文學作品分析會、音樂欣賞、知識游戲等生動、有趣、吸引人的活動,既可以豐富同學們的課余生活,又擴大了學生的知識面,還可以培養學生高尚的情趣,文明的習慣,促進身心健康發展。開展這些活動也使一些同學的個人愛好和才華得到施展和提高。”
下面,讓我們欣賞一下汪國真的這組詩:
晨 練
天將曉,
同學醒來早。
打拳、做操、練長跑,endprint
鍛煉身體好。
早 讀
東方白,
結伴讀書來。
書聲瑯瑯傳天外,
壯志在胸懷。
聽 課
講壇上,
人人凝神望。
園丁辛勤育棟梁,
新苗看茁壯。
賽 球
籃球場,
氣氛真緊張。
龍騰虎躍傳球忙,
個個身手強。
燈 下
星光閃,
同學坐桌前。
今天燈下細描繪,
明朝畫一卷……。
盡管,在時隔三十八年之后閱讀汪國真的這組詩,我們會覺得這組詩十分稚嫩,與他后來的詩歌作品實在難以相比;但是,對于當時的汪國真來說,卻對他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他從此更加熱愛詩歌創作。要知道,當年的《中國青年報》可是發行量達到一百萬份以上、具有全國性影響的大報啊!能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詩歌作品,那可是一種巨大的榮譽啊!
發表汪國真處女作的編輯叫梁平。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梁平得到了一本暨南大學中文系學生創辦的油印詩歌刊物《長歌》,在那上面,他選載了汪國真的五首短詩發表在《校園生活》專欄上。1980年,梁平在他主持的《校園生活》專欄上又發表了汪國真寫于1979年的《僑校生活日記三則》:
1979年×月×日
時間過得真快呀,半年前,我和同學們都還分布在世界的各個角落,現在卻親密無間地在一起學習、生活了,我們六十多人的中文系,可以說是個小小的外語學院。啟光是個印尼歸僑,講得一口頂呱呱的印尼語;朝鮮來的小管,會寫一手漂亮的朝文;幾個加拿大和港澳來的同學,還當過英語教師呢。生活在這樣一個大集體里,真有意思!
1979年×月×日
新聞系的同學不愧是行家里手,辦的墻報吸引了那樣多的觀眾。頂有趣的是一篇《青年發福并非福》的小短文,短文中說,入學以來,同學們都普遍發胖了,但青年時期發胖并不是件好事。文章建議大家加強身體鍛煉,來個“降肥”運動。我記得剛入校時,聽海外同學講,父母怕他們不習慣國內生活,會把身體弄瘦了。他們哪里知道,眼下自己的孩子正為如何“降肥”發愁呢!
1979年×月×日
看了今年第一期《電影新作》里的劇本《琴童》。劇本描寫了一個名叫晶晶的孩子,他拉得一手出色的小提琴,但是在“四人幫”時期,因有海外關系,幾次都未被音樂學院錄取。看了真令人憤憤不平。系里有些同學的經歷和晶晶差不多,讀完掩卷深思,更加感謝我們的黨落實了僑務政策,把我們這些“海外游子”和有所謂“海外關系”的人從“四人幫”的桎梏下解放出來。我們要在祖國母親的懷抱里刻苦學習。
在《中國青年報》上接連發表詩歌和日記,對汪國真來說無疑是一種巨大的鼓舞。在這種精神動力的鼓舞下,汪國真在大學期間的詩歌創作不斷進步,并寫出不少好詩。其中,比較有影響的兩首詩是1980年10月23日發表在《廣東僑報》上的《鄉思》(二首):
望
他獨自徘徊在海灘上,
極目向海天盡處眺望。
呵,對面那金色的海岸,
就是美麗富饒的家鄉。
海潮沖掉了他深深的腳印,
卻撫不平他那深深的憂傷。
因為在他的心房里
有一個燃燒了三十年的愿望……
夢
他在夢中甜甜地微笑,
夢見自己化作一只海鳥,
展翅飛過波濤洶涌的大海,
撲進故鄉溫暖的懷抱……
用顫抖的雙手
撫摸家鄉的一巖一峭
用含淚的雙眼
辨識久別的一徑一道。
用嗚咽的聲音
喊出埋藏已久的話——
啊!故鄉,故鄉!
游子回來了!
這兩首詩發表后,不但受到了同學們的好評,也得到了廣大讀者的喜歡。從此,汪國真正式走上詩歌創作道路。
作為汪國真詩歌的忠實讀者,我除了喜歡他的詩歌之外,同樣喜歡作為書法家的他創作的書法作品,更夢寐以求得到他的墨寶。
在收到從孔夫子舊書網上買來的《鴻爪》那天,我給他發去一封短信,說出了埋藏在心中很久的心愿,希望求汪國真老師一幅字,做八十年代詩歌紀念館的鎮館之寶。沒想到,汪國真老師很爽快地答應了。經過日思夜念熱切的期盼,6月25日,我終于收到了汪國真從北京寄來的一幅珍貴的書法,上面寫著:“八十年代,是一個詩情噴涌的時代——書贈八十年代詩歌紀念館。”和墨寶一起寄來的還有他的一本書名為《汪國真書畫作品集》的書畫冊,兩盤題名為《汪國真音樂作品》《感悟汪國真》的音樂光盤,一張外交部禮賓司發給他的關于他的書法作為國禮的榮譽證書。捧著汪國真老師寄贈的珍貴的墨寶和珍貴的禮物,我感動得不知如何是好……
汪國真老師不但對我創辦八十年代詩歌紀念館給予了無私的幫助,而且對于我從事大學生文學史和詩歌史的研究事業也非常關心、非常支持。2014年4月,我編著了一本有關七七級、七八級大學生文學活動的書稿,選入了他的文章《我最初的文學生涯》。4月24日,我給他發去電子郵件征求他意見的時候,他十分體諒和理解我編著出版文學史料類書稿的種種辛苦和種種難處,對我的工作給予了無條件的支持。4月25日,他回信給予我滿意的答復:“本人同意姜紅偉先生在編著的《文學年代——中國高校1977級1978級大學生文學生涯備忘錄》(暫名)一書中收入我的文章。為了支持該書的出版,本人同意放棄該書的稿費。”通過這件事,我對汪國真老師的敬意更加深了。
2014年7月,我策劃了《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訪談錄》一書,由于汪國真老師在暨南大學中文系78級上學時就開始發表詩歌作品,經歷了大學生詩歌運動的初期階段,因此,我請汪國真老師做一個訪談。當時,汪國真老師雖然工作很忙,身體不好,但是卻依舊認真為我準備了訪談材料,使我得以順利完成這次訪談。沒想到,這篇我們共同完成的題為《沒有比人更高的山——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訪談錄之汪國真篇》居然成了汪老師生前最后一次關于詩歌的訪談。endprint
2014年9月,由我編著的書稿《大學生詩歌家譜——〈飛天·大學生詩苑〉創辦史(1981—2014)》由廣東人民出版社決定出版。在和廣東人民出版社簽訂完出版合同后,我將這本書稿發給了汪國真老師,請他提出寶貴的意見和建議,并希望他能和其他著名詩人一起聯袂推薦這本書。9月15日上午9點25分,我收到了汪國真老師的短信,他在看過書稿后欣然同意向廣大讀者推薦這本書,再一次給予了我莫大的鼓勵。
然而,就在這本書進入編輯出版程序的時候,2015年4月26日,從北京傳來噩耗,汪國真老師因患肝癌不幸去世,年僅五十九歲。
在我心目中,汪國真老師既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著名詩人、書畫家、作曲家,也是一位為人正直、善良、低調、謙遜的好人,又是一位善待后學、樂于助人的詩壇前輩,更是一位值得我敬仰、值得我感恩的恩師。
附錄:
編者按——
前文提到的汪國真先生的短篇小說《丹櫻》,既是他的短篇小說處女作,又是他生前唯一一篇公開發表的短篇小說。這篇小說講述了一位在20世紀80年代初,一位華僑女學生毅然放棄日本優越的學習環境,堅持回到祖國學習并決心在畢業后投身于祖國“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故事,塑造了一位感人至深的愛國女學生形象。小說立意鮮明,語言生動,筆觸細膩,形象鮮活,是一篇充滿了反思“文革”和謳歌改革開放的比較優秀的小說作品,從中可以看出時代的遷跡和汪國真早期的創作思想,應該說是一份很重要、很珍貴的文獻,對于今后研究汪國真文學藝術創作歷史來說,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和研究價值。現附錄于此,以饗讀者。
丹 櫻
汪國真
嘈雜聲停止了。帷幕拉開了一道縫隙,穿著文雅、素潔的女報幕員輕捷地走了出來。她用標準的普通話報幕:“歡迎新同學文藝晚會現在開始!”臺下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第一個節目:大合唱……”
節目一個個地演下去。最初的幾個節目都是我們這些二三年級的學生精心排演的。最后的幾個節目輪到新生表演了,我們都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舞臺。
“下一個節目,女聲獨唱。演唱者:光學系一年級新生——劉丹櫻。”“劉丹櫻?”我不覺心頭一動,腦中閃現出一個女孩子的形象。難道是她?我焦灼地等待她出現在舞臺上。
天鵝絨的帷幕徐徐拉開,一個身材頎長的姑娘輕盈地走向舞臺。她走到麥克風前,深深地向臺下的觀眾鞠了一躬。這特別的禮貌立刻引來了一陣熱烈的掌聲。當她抬起頭的時候,我看清楚了她的面容:細而長的眉毛,泉水般清澈的眼睛,紅潤小巧的嘴唇……
“呵,是她!一點不錯,是她——劉丹櫻。”我歡喜極了。
她開始演唱了,她唱的歌叫《祖國情思》。
“……
捧起一把祖國的泥土啊,情無限,
喝上一口家鄉的井水啊,蜜般甜。
祖國的山水草木呵,緊連著海外赤子的心……”
淚水從她那顧盼生輝的眼睛里緩緩流淌下來。歌聲、淚珠灌進了我的心,掀開心中記憶的屏障,往事歷歷,如在眼前。
六十年代中期,我的爸爸在北京的一個研究所里當黨委書記,媽媽在所里做人事工作。一天,家里來了客人。一位三十多歲、穿著西服打著領帶的叔叔領著一個穿淺黃色衣裙的小姑娘來到我們家。爸爸、媽媽熱情地迎了上去,同他親切握手,真像多年不見的老朋友。那位小姑娘則恭敬地依次向爸爸媽媽和我深深地鞠躬。她的禮貌而稚氣的神態,使大家很歡喜。
爸爸、媽媽和叔叔有工作要談,我便負責招待小客人。我給她倒水,拿了糖果,端放在她面前。她靦腆有禮地向我道謝:“謝謝姐姐”。我趕忙打斷了她的話:“先不要叫姐姐,我們倆還不知誰大呢?”
“我十歲。”她很快告訴我。
“呵,我們倆一樣。你幾月出生的?”
“八月。”
“噢,比我小六個月。”看來,這個姐姐果真是我當了。
我把糖果和水杯又稍微向她面前推了推。
“以前我可沒見過你。”我盡量做得像個姐姐的樣子。
“我跟爸爸媽媽剛從日本回來。”
“你叫什么名字?”
“丹櫻,牡丹的丹,櫻花的櫻。”
“丹櫻,多好聽的名字。”
“不,我爸爸說,給我起這個名字不是為了好聽,而是為了紀念。”
“紀念?”
“是的,我爸爸說,我在日本出生,櫻花是日本的象征。我是中國人,牡丹是中國人民喜愛的花,要我永遠記住偉大的祖國,不忘日本人民。”說到這里,丹櫻換上一種我們那種年齡的人少有的嚴肅神情說:“我爸爸在日本是很有名望的光學家,但他說,我們是中國人,要把自己的知識貢獻給祖國,使祖國早日富強起來。今年十月一日,我們從東京機場起飛回國,在飛機上,爸爸高興得像個小孩,對著我和媽媽大聲朗誦唐詩‘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接著說,今天適逢國慶佳節,我們就要回到祖國母親的懷抱了!”
多少年過去了,丹櫻這一席話至今還留在我的心間。
后來,丹櫻的爸爸在我爸爸所在的研究所里當了副所長,工作很有成績。丹櫻和我則成了同班同學。她功課好,懂禮貌;性格活潑,能歌善舞。老師和同學們都很喜歡她,大家選她當班里的文娛委員。她經常唱的一支歌就是:“孔雀,孔雀真美麗,穿著一身花花衣……”這首歌,她唱得連我也會了。一天夜里,我還夢見丹櫻變成了一只美麗的孔雀……
一次,電影制片廠到我們學校拍攝反映學生生活的紀錄片,學校挑選丹櫻作為拍攝對象之一。丹櫻知道了這件事后,來到校長室,誠懇地說:“校長,我不能上電影。我學習成績并不太好。我想,要建設一個富強的國家,像我這樣的學習成績是不行的。”電影拍成時,丹櫻雖然沒上銀幕,但她的話被引進了解說詞,這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6年,正當我們在祖國懷抱里、在黨的關懷下健康成長的時候,一場大浩劫開始了。endprint
我爸爸在一個早上突然變成了“叛徒”和“走資派”。不久,丹櫻的爸爸也被關進了“牛棚”,據說他有特務嫌疑。
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化,我迷惘、痛苦、惶然不知所措。而這種打擊對丹櫻來說不是會顯得更大嗎?在她那幼稚和純潔的心靈里,祖國是這樣美,怎么受得了這種命運的打擊。有一天,她抽泣著對我說:“萍萍姐姐,我爸爸怎么會是特務呢?不!他是好人!他愛祖國,他為祖國建設出力,還要我好好學習,將來為祖國服務。他是好人!我爸爸是好人!”她不再抽泣了,而是大聲地呼喊起來。陣陣凜冽的北風刮來,使我們兩個女孩子的呼聲變得十分弱小、低微。
爸媽到干校,我要跟著去。我和丹櫻分手了。淚眼相向,默默無言。最后,還是丹櫻咬了咬牙,說:“姐姐請珍重。常來信。”
桃花開了又謝,謝了又開。轉眼已經是1975年,我和丹櫻都已是充滿青春氣息的姑娘了。一天,我接到丹櫻的一封信,她告訴我,自從鄧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以后,落實了知識分子政策,她爸爸的問題已經弄清楚:所謂“特嫌”完全是假的。但她又告訴我,爸爸、媽媽決定申請到日本長期居住。她也必須跟著走。最近就要啟程。
信戛然而止。我似乎看到她沒有寫到信上的話。這是些什么話呢?我又不能說清楚,我像丟失了最寶貴的什么東西,無限惆悵和懊惱。
我怎么也想不到,丹櫻又出現在我面前。
晚會結束了,我懷著抑制不住的激動來到了后臺。
“丹櫻!”我放開嗓子喊了她一聲。她調轉過頭,用她那美麗的眼睛注視著我——先是愣住,接著她跳起,奔過來,撲向我,緊緊擁抱著我。
“呵,姐姐,萍萍姐姐……”眼淚代替了語言,她那滾燙的淚珠滴在我的肩頭。而我的淚珠也已把她的一片襯衫打濕。
一彎皓月向大地灑下了一片銀輝。美麗的校園一片靜謐。我和丹櫻沿著長長的林蔭道慢慢地走著,細細地交談。她向我傾述著離開祖國時的失望,回到日本以后的生活,以及粉碎“四人幫”給她們一家以及廣大海外華僑帶來的歡欣和希望。
“……你為什么出國后不給我寫信呢?”我問她。
“萍萍姐姐,原諒我吧。你知道,那時我是多么想給你寫信呵,但又怕給你們帶來麻煩。”
我望著她深情的眼睛,完全理解她的心。
“現在好了,我們又在一起了。”丹櫻感慨地說。
“可是,將來你畢業后又回日本,我們只能在信中見面了。”
“回日本?我為什么要回日本呢?”她像是看陌生人一樣望著我,聲調也提高了。
“怎么,你不準備回去了?”
她嚴肅地點點頭。
“難道你不覺得……”我欲言又止。
“你是說,我們國家生活水平太低是嗎?萍萍姐姐,俗話說得好:孩子不嫌娘丑。中國人是聰明、勤勞的,祖國一定會富強起來的。”她用低緩的聲調親切地說。
我贊賞她這番話,但我心中仍有一些隱隱的憂慮,我說:“生活給我們這些天真的人的教訓夠深刻了。當年,你爸爸……”
丹櫻理解了我沒說完的話。她把頭微微昂起,用手理了理被夜風吹亂的幾根頭發,說:“萍萍姐姐,我是這樣想的:我國人民已經從那場大悲劇中學到了怎樣去防止再發生那樣的悲劇。因此,我不會再有我爸爸那種遭遇了。你說是嗎?萍萍姐姐。我記得我爸爸在送我回國時給我說了很多話,其中有這句古辭:‘殷憂啟圣,多難興邦。祖國一定會由我們建設得更富強起來的!”
丹櫻,你說得多好啊!
【責任編輯】 于曉威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