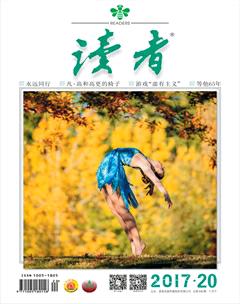那份深不見底的失望
楊照
女兒的鋼琴由江恬儀老師啟蒙。女兒六歲進小學音樂班,在江老師之外,還有廖皎含老師教她鋼琴。兩位老師都對她很好,不只疼她,而且努力想出各種方式讓她在鋼琴演奏上取得進步。

女兒上中學之后,換了鋼琴老師,但她跟江老師、廖老師都保持聯絡。有一回,她跟廖老師借琴房練琴,練了一陣子休息時,在廖老師擺放樂譜的架子上,發現一件有趣的東西。
那是她自己之前寫的一份悔過書,稚嫩的筆跡白紙黑字地承諾著:“要保持手指站好,要耐心慢練,要專心上課,不能心不在焉……”最后面是:“如果沒有做到,老師可以拒絕教我。”女兒用手機把那張還貼在架上的悔過書拍下來,將照片放到“臉書”上,一下子就吸引了許多朋友來點贊和留言。留言中有好幾則來自廖老師的學生,他們帶點興奮又帶點哀怨地說:“啊,我也寫過!”之后,出現了廖老師的留言:“這下大家都知道我是個惡老師了!”
女兒的媽媽有點擔心:老師是不是生氣了?女兒倒是很有自信:“一定不會,廖老師很有幽默感的。”幾天后,媽媽和廖老師在電話里聊天,果然老師以玩笑的態度說:“有一個在美國教琴的朋友看到那張悔過書,還叫我把內容翻譯成英文,她要拿去讓她那些不認真的美國學生也照著寫!”
我不記得自己寫過悔過書。照理說,成長過程中犯過那么多錯,一定寫過,但就是一次都記不得了。或許都是以敷衍態度寫的,沒有真正的悔過之意,時日久遠,就記不得了。但我有一段跟女兒寫悔過書類似的經歷,卻在腦中留下無法磨滅的痕跡。
小學五六年級時,我跟一位個性暴烈的老師學小提琴,課堂上經常被打,痛苦不堪。有一次上課,我心中充滿了怨懟,老師愈打我,我愈是不愿意好好將他要的聲音拉出來。幾次之后,老師突然冷靜地說:“收琴,別拉了。”我收了琴,鼓足勇氣挺胸正眼對著老師。
老師說出我完全沒有料想到的話:“琴留著,你走,回家去。罰你一星期不準練琴。”老師接著又說,“下星期來,你明白告訴我,還要不要學琴!你若說不要,我就把琴還你,以后你就再也不用來了。”
老師后面這一段話,我聽了,但沒有真正聽進去,因為心里光想著要趕快在老師還沒有改變主意前離開那里,坐實一個星期不用練琴的“懲罰”。走出老師家門,那種如釋重負的快樂,更讓我無法真正去思考老師到底說了什么。
一直到星期天,距離下次上琴課只剩下兩天時間。再也逃避不了了,也沒辦法假裝忘記老師交代的:“你明白告訴我,還要不要學琴……”我想了想,鄭重其事地暗下決心:寧可被老師揮兩個巴掌,也要勇敢地說出“不想學了”!
對,說出來,忍兩個巴掌,就從每周一次的痛苦中解脫了。
我步伐沉重地走到老師家門口。老師開了門,手里提著我的琴盒,眼睛看著我,沒說話。顯然他沒有忘掉上回的事,他在認真地等我的回答。停了一秒鐘,我開口說:“對不起,請老師繼續教我拉琴。”話說出口,自己都感到很意外,這不是我準備好要講的,我要說的明明是“對不起,我不想再學了”,為什么話在出口前自己轉了彎呢?
多年之后,我才理解在老師家門口究竟發生了什么。在那個時候,在內心深處我明白,如果說“我不想再學了”,老師會有多失望。我甚至明白了,為什么我那么受不了被老師用舊琴弓抽打肩膀——不是因為痛,而是因為老師打人時表現出的失望。他的失望比琴弓打在身上,更讓我感到痛。
我做錯準備了。我準備著忍受老師盛怒下沖動的兩個巴掌,但在那個時候,我知道不會有那兩個巴掌,只會有老師很可能完全無言的、深不見底的失望。
我沒辦法面對那樣的失望,就是沒有辦法。
(林冬冬摘自《晶報》,沈 璐圖)
——為鋼琴獨奏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