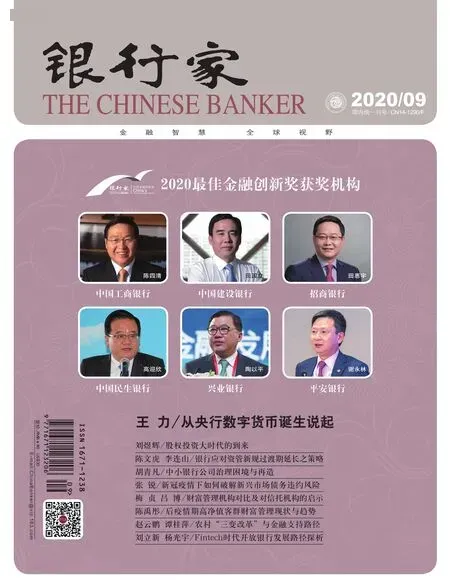父子集(37)
王青石
文學、第二只手,以及與之共存
個人公眾號井噴的時期已過去很久,九成當初立志做自媒體的草根人物現在微信平臺上已石沉大海、不見去向。堅守至今的,要么是成功套上了某種商業模式的,要么就是我這樣,自娛自樂、純為了發文章的。
寫作對于我其實是一件很special的事情,打小靠著寫范文在學校里樹立形象,不知不覺它就于成長過程里融進了骨頭深處。上回激情創作的一首《語文課代表》也是有點兒在紀念那幾年的人生巔峰。
“呵呵,你是學金融的?還以為你學文學的。”不是第一次這么被人說了,也不知是夸獎還是冷嘲熱諷。
但說實話,我接觸過的刻板學文學的人七成段位都很低,至多屬于文學愛好者,卻過于想拿科學系統的方式解釋文學,這是有問題的。成功文學中必然存在毋庸置疑的道。道為何物?無中生有、畫龍點睛的精髓,遠非兩三個研究方法可以解剖清晰的。
好文學的原型和市場對象都是人,所以文學創作歸根結底是一個心理學領域的實踐問題,而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瞬息萬變的思想生成者,以人為題的謎注定了往往最難窺探的謎底。
孔德在研究后工業革命歐洲時指出,社會學是他眼中最高階的學科,因為其研究對象無時無刻不處于一種改過自新的演變模式。換句話講,人類通過觀察自己所處的社會來得到一些有關社會的理論,而這些理論的普及會將社會打磨成新的面貌與代謝模式,從而使部分舊的社會理論失效,研究者則不得不以新社會為基礎與研究對象,以得出新的、更適合其時代的社會理論,周而復始。
所以說人是謎,不因人真的是謎,而是因所有人的觀察者也是人,人與人無法消除的共性就像一道永恒的干擾波,隔擋在我們與自身的鏡像之間。
不跑題,我想砸在小木桌上的點就是:當人觀察人、記錄人的時候,其中是有一層源自生物共鳴的隔膜,它沒有太厚,厚到宛如墻壁障;也沒有太薄,薄到是非一目了然。它的構造是近乎完美的:剛好令那些同類似是而非的相近與相差朦朧不清、若隱若現。
這不是障礙物,而是一種原始感情,就像飲料營銷者們酷愛提及的、一聽就很純粹美好的原漿;就像《心理罪》中孤兒方木在犯罪心理畫像領域一直所向披靡、滴水不漏,卻在初戀女友成為受害者后喪失了明察秋毫的天賦,我們是不會想要責備方木的,因他只是深陷生為人的體驗。
“你破的是案,我看的是人心。”
人心哪能被看透呢,又不是高德地圖,畫好了讓你隨便看。
人心是一個渾然不同的物理場,也正因如此,事關人心的游戲最具挑戰性。當中高尚一點的可能要算上文學、藝術、教育等,低階一些的包括處理男女感情、博弈于職場官場等。
回到我初始丟出的“文學”命題上,這一點亦是寫作與文學的差別:寫作可以模式化、系統生產,以達到行業標準的要求;文學卻萬萬不能,優秀文學不是上了什么榜單、在多少公眾號上實現了“10萬+”、銷量全國第幾可衡量的,優秀文學是讓人讀完直呼“感動”“騷”,或者“我了個大×”的,這才是文學的力道到了。
就像許多價格合理的私房小館口味上完全勝過某些濫竽充數的米其林餐廳。你可以混出來個米其林的星,但再多星也騙不了活生生的味蕾。
嘴硬的當然可以說,榜單與銷量必然有其公正性。但我覺得,國外,也許吧,中國的話,百分之九十九要排名的、帶有功勞性質的重大差事都充滿著政治性,那種容不得被揭發、但所有業內人都曉得它存在的政治性。
這種政治性可謂是繼斯密的第一只手后,中國市場上第二只看不見的手。
這只手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文化中,會有人責備其負面的效應,但短期內無法改變就是無法改變。我確實認為,即便有領導人的大規模變革也無能為力。
所以重點是,注定被第二只手攔于門外、卻有真才實學的人該如何生存?其實就是保護好自己,切莫怨天尤人,然后與之共存,因為內心真實的受眾還是大多數,縱然他們不會表現得那么真實。
還是前文那句,米其林星星騙不了活生生的味蕾。
就像2016年美國大選前輿論一邊倒地支持希拉里,結果上臺的卻是敢說大多數人真實想法那個人。其實大家都厭倦了許多時候無非是偽善的政治正確,這是政治性面對原始感情敗下陣來的經典案例。
所以對于性情中人,與不太性情的社會共存的前提就是必須要相信原始感情的普遍存在,相信它在那些冷漠或虛假的面具之下,哪怕證明這種存在的征兆越來越少,哪怕世界似乎已到了無法忍受的荒蕪程度。
但它存在,就像白天我們看不見的星星,就像夜晚暫時離開的太陽。這就是我堅持寫作的動力。
2017.8.1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