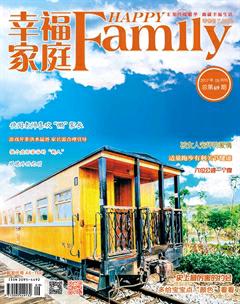請善待兒童的興趣
仲虎超
我記得自己上學前班那會兒,有很長一段時間,完全被教室墻上的一幅畫給深深地吸引住了,以至于上課時常常忽略了老師的存在,頭腦和眼睛里就只有那幅畫,總是忍不住想要去臨摹再三。
那是一幅徐悲鴻的《八駿圖》,但當時得我并不知道,只是一味地覺得那副畫畫得栩栩如生。8匹駿馬在一起撒歡兒似的恣意奔跑,鬃毛隨風起舞,英姿颯爽,好不壯觀。我心里那叫一個喜歡。總之,無論上課下課,一有閑工夫,我就拿起鉛筆,照著墻上的畫兒,一筆一畫地臨摹,重復無數遍。我總感覺不是嘴巴畫歪了,就是屁股畫得太圓了,或是哪條腿畫得不夠協調,擦了畫畫了再擦,紙擦破了,就換一張新的接著畫。一學期下來,稿紙和鉛筆消耗了不少。最后,終于對其中的一幅比較滿意,于是我把它拿回家,打算張貼在床頭,那樣我每天起床和睡覺時都可以看到它。母親一見,嚇了一跳:“這是哪來的?你畫的嗎?”我點頭。要知道,那時候農村的學前班里還沒有美術這門課程,這一點母親也知道。“嗯,比真的還好看。我還以為是老師畫的呢。太像了!”哈哈,得到母親的肯定,我感到非常得意。“媽媽,我打算把它貼到墻上,可以嗎?”我問母親。“當然,不過我想給它裱起來也許會更好。”就這樣,我們弄個框子,放到客廳最顯眼的位置,別人一進屋就可以看到,母親邊說邊用手比劃著。母親的回答顯然大大超出我的預期,我高興極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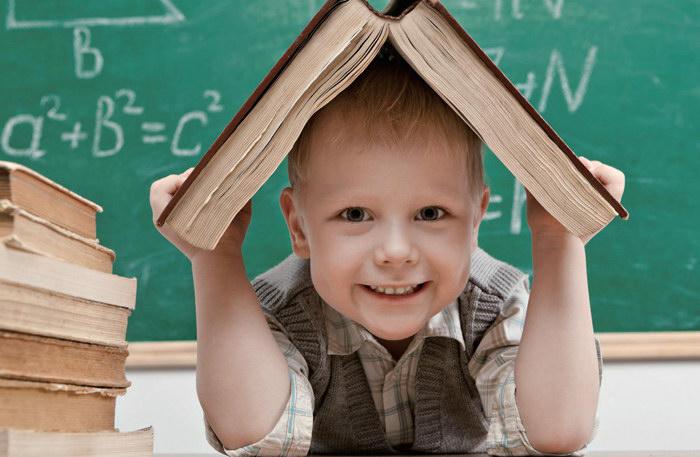
第2天我放學回來,一進門就看到我的那副“杰作”被鄭重地懸掛在客廳最顯眼的位置。現在想想,我后來對繪畫一直都特別著迷,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興趣應該就是從那時培養起來的。感謝母親,在20世紀80年代農村教育很落后的大環境下,用她樸素的寬容與愛接納了我,給了我自由發展興趣的空間,也教會了我什么是尊重。
受母親的影響,多年以后,我對自己的孩子也表現出了足夠的寬容與接納。當兒子向我講述一些古靈精怪的想法,或是做出一些讓人忍俊不禁的事情時,我從不會以成人的視角去評判是非和報以嘲笑。我總是努力從中尋找出一些積極的方面,告訴他做得不錯。有一次,兒子從學校垂頭喪氣地回來,一問之下才知道,今天他的美術作品在學校里被老師判了0分。我拿過來一看,畫的是一只長了翅膀的氣球和一只鳥兒在空中嬉戲。氣球和鳥兒一樣,有眼睛、鼻子、嘴巴,也有雙腳。有趣的是,作品中的天空是綠色的。我猜想老師可能是認為孩子畫得過于失真,所以給了這樣的分數,但他忽視了自己的做法可能會給一個兒童的熱情和自信心帶來莫大的傷害,無形之中他正是在運用教師的權威試圖扼殺掉兒童的想象力。于是我告訴兒子,他的畫富有想象力,我很喜歡,希望他能談談自己的創作過程。他見我一臉誠懇,便調整好情緒,認真地講開了。等他敘述完畢,我說:“原來是這樣。你的想法已經超出了我的想象空間,難怪老師會給你這樣的分數。我想一定是老師沒有仔細地看清楚。”在我的努力下,兒子失落的情緒漸漸釋然了。
在美國,曾發生過這樣一個故事。1968年,內華達州有位叫伊迪絲的3歲小女孩告訴媽媽,她認識禮品盒上“OPEN”的第一個字母“O”。這位媽媽聽后非常吃驚,問她是怎么認識的。伊迪絲說:“是薇拉小姐教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位母親表揚完女兒之后,竟一紙訴狀把薇拉小姐所在的幼兒園告上了法庭,理由是幼兒園剝奪了伊迪絲的想象力,因為她的女兒在認識“O”之前,能把“O”說成蘋果、太陽、足球、鳥蛋之類的圓形東西,然而自從幼兒園教她識讀了26個字母之后,伊迪絲便失去了這種能力。訴狀遞上去之后,幼兒園的老師們都認為這位母親大概是瘋了,一些家長也感到此舉有點莫名其妙。3個月后,此案在內華達州州立法院開庭,最后的結果出人意料,幼兒園敗訴,因為陪審團的23名成員都被這位母親在辯護時講的一個故事感動了。這位母親說:“我旅行時,在一個公園里見過兩只天鵝,一只被剪去了左邊的翅膀,一只完好無損。剪去翅膀的被放養在較大的一片水塘里,完好的一只被放養在一片較小的水塘里。當時我非常不解,那里的管理人員說,這樣能防止它們逃跑。他們的解釋是,剪去一邊翅膀的天鵝無法保持身體的平衡,飛起后就會掉下來;在小水塘里的天鵝,雖然沒有被剪去翅膀,但起飛時因沒有必需的滑翔路程,也會老實地呆在水塘里。當時我震驚于他們的聰明,可是也感到非常悲哀。今天,我為我女兒的事來打這場官司,是因為我感到伊迪絲變成了幼兒園的一只天鵝,他們剪掉了伊迪絲的一只翅膀,一只想象的翅膀,他們早早地把她投進了那片小水塘,那片只有26個字母的小水塘。”這段辯護詞后來竟成了內華達州修改《公民教育保護法》的依據,其中規定兒童在學校必須擁有兩項權利,一項是玩的權利,也就是自由發展興趣的權利,一項是問為什么的權利,也就是擁有想象力的權利。
今天,我們反觀傳統文化,其中大部分是鼓勵兒童按照成人的規范來規劃自我,希望他們的思想和行為要循規蹈矩,而不注重發現、激發和保護兒童天性中潛在的興趣和想象力。在這一過程中,應試教育首當其沖。很多時候,兒童的興趣里就包含著無限的想象力,二者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愛因斯坦說:“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確實,作為普通家長,在學校教育的藩籬之外,用自己的愛去接納兒童,善待他們的興趣,保護他們的想象力,應該是最理性的選擇。
(摘自《宿遷日報》2017年6月28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