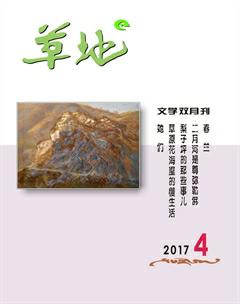流經生命的巴顏喀拉黃河
文君
巴顏喀拉的黃河不光是流經馬壽宇老師生命中的一條河流,也是流經我生命的一條河流。我在巴顏喀拉的黃河邊生活過,和馬壽宇老師有著相似的生活背景和生活經歷,因此,走近馬壽宇老師,也就成了偶然中的必然。
那是在都江堰文學網上的一次邂逅。我因為只寫現代詩和散文,加之眼疾無法廣泛閱讀,近十來年幾乎沒有閱讀過小說了,所以,對小說我是沒有任何發言權的。
三年前,因為加入了都江堰文學圈,偶爾也就會關注一下作協的網站。一日,我在首頁上瀏覽,《巴顏喀拉黃河》這幾個字突然跳進眼簾,我心里一緊,仿佛某根神經被什么觸動,趕緊點開網頁。隨后,走進了巴顏喀拉黃河邊那個荒涼的牧區草原,走進了生活在巴顏喀拉黃河邊那一群充滿了憂傷的靈魂中。
這是一篇自傳體式的小說,熟悉的環境,民風民俗,生活方式,勾起了我對這篇小說濃厚的興趣,網站上連載的片段無法讓我大快朵頤,我找到編輯老師直接要來文稿一口氣讀完,掩卷時才發現已是淚流滿面。
這是一篇分配至藏區的青年教師與原住民在荒涼而艱苦的環境中所演繹的恩怨情仇的故事。全文以“我”作為一個特殊年代知識分子的代表,和當地一位疑似麻風病患者的阿英姑娘之間的悲歡離合,揭示了一個民族,一群人,在特定的政治環境、地域環境中,所經歷的人世坎坷和人生磨難。
沒有在藏區生活過的人,很難想象高原的生活有多艱苦;沒有在藏區生活過的人,也不會明白藏族女人在生活中的地位有多卑微;沒有在藏區生活過的人,更難以想象被打上麻風病烙印的人,會經歷怎樣悲慘的人生。在高原,誰要是被指認為麻風病患者,那就等于被判了終身流放的極刑,家人、族人,甚至整個寨子的人,都會受到外部的嚴重歧視,甚至受到牽連。昔日我有一個漢人村的女同學,被診斷為麻風病送往麻風村,好長一段時間,我們都不敢搭理她們村的同學。后來聽說她在麻風村里,一個漢家女子,語言不通,生活不便,甚至連自己的糧食都弄不回來,最后因為饑餓、寒冷,在一個冬天抑郁而終。
這篇小說里,作為知識分子代表的“我”,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知識分子臭老九的符號不亞于麻風病,他所經歷的劫難,一如那個藏家麻風女阿英的遭遇,可謂萬般悲苦。
這篇小說表現的是一個特殊時代,特殊環境,特殊身份的人不同的命運。它將男人與女人,外來者與原住民,知識文明擁有者與原始習俗繼承者這兩種人之間所經歷的磨練,不為常人所知的終極靈魂的較量,現實與精神世界的生死抗爭,以及最終走向人生彼岸的故事,完全展現了出來。
馬壽宇老師用詩一樣的語言,散文般的意境,構建了《巴顏喀拉黃河》這篇小說宏大的場景。這讓我想起前段時間網上熱議的一個話題:跨文體寫作。也就是說,小說中有散文的隨意結構,有詩歌的詩性語言,有評論的理性思辨,更有報告文學的真實性。我不懂小說的創作,但我從這篇小說里看見了跨文體寫作的奇異效果。這種寫作手法的運用,使得整篇小說自始至終保持著一種理性,真實地呈現出人性的多面性和復雜性,從而塑造了“我”和阿英這些為了生存,在生命底層苦苦掙扎的靈魂,以及他們為適應生活和生存,面對那個扭曲的時代,扭曲的人群,所表現出來的隱忍、堅強、善良、包容等高貴的品質。
在這里,我要感謝馬壽宇老師給我們帶來的《巴顏喀拉黃河》這樣優秀的文學作品,它不光是歷史的再現,更是對生命的謳歌和贊禮,他給我們呈現了一個古老民族的高貴品質以及神秘的宗教和歷史文化的同時,也讓巴顏喀拉黃河像母親的乳汁一樣,流經我們的生命,滋養、孕育著我們,給我們以知識的提升和靈魂的洗禮。
感謝文學,感謝相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