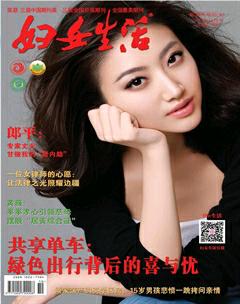文萃月報(bào)
毒品犯罪5年54.3萬人被判刑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發(fā)布的《人民法院禁毒工作白皮書(2012-2017)》顯示,2012年到2016年,全國法院一審新收毒品犯罪案件共計(jì)54.1萬件,判決生效犯罪分子54.3萬人。毒品犯罪案件是增長最快的案件類型之一。
(摘自2017年6月21日北青網(wǎng))
中國超算實(shí)現(xiàn)三連冠
記者從國家超級計(jì)算機(jī)無錫中心獲悉,基于國產(chǎn)眾核處理器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級計(jì)算機(jī)連續(xù)第三次獲得世界超級計(jì)算機(jī)排名榜TOP500第一名。同時(shí),“神威小型機(jī)”的原型機(jī)研制工作也已完成。
(摘自2017年6月20日《北京日報(bào)》)
湖泊磷污染八年下降逾三分之一
日前,天津大學(xué)環(huán)境學(xué)院的一項(xiàng)研究表明,2006年到2014年,我國城市地區(qū)與磷污染有關(guān)的水體富營養(yǎng)化風(fēng)險(xiǎn)大幅降低,其中湖泊主要污染物磷的含量下降三分之一以上。
(摘自2017年6月20日《光明日報(bào)》)
我國將成為世界經(jīng)濟(jì)增長第一引擎
國家統(tǒng)計(jì)局日前發(fā)布的數(shù)據(jù)顯示,2016年,中國對世界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率達(dá)到34.7%,拉動世界經(jīng)濟(jì)增長0.8個百分點(diǎn),是世界經(jīng)濟(jì)增長的第一引擎。
(摘自2017年6月22日《光明日報(bào)》)
國家土壤環(huán)境監(jiān)測網(wǎng)已初步形成
環(huán)保部土壤環(huán)境管理司司長邱啟文介紹,環(huán)保部已編制土壤環(huán)境監(jiān)測總體方案和國控點(diǎn)位布設(shè)方案,已確定2萬個左右基礎(chǔ)點(diǎn)位布設(shè),覆蓋我國99%的縣、98%的土壤類型、88%的糧食主產(chǎn)區(qū),初步建成國家土壤環(huán)境監(jiān)測網(wǎng)。
(摘自2017年6月22日《北京青年報(bào)》)
“絕望主婦”戴安娜王妃
在戴安娜王妃逝世20周年之際,其生前口述的自傳《戴安娜:她的真實(shí)故事》得以再版,作者安德魯·莫頓也首次對媒體披露了口述內(nèi)容的錄音稿。戴妃在錄音中痛陳自身的疾患、丈夫的私情以及婆婆的“冷漠”,多次用到“絕望”一詞,更語出驚人地表示“才結(jié)婚幾星期就想割腕自殺”。
據(jù)戴妃口述,她與查爾斯王儲的關(guān)系早在大婚前就多次出現(xiàn)“不和諧音符”,查爾斯對她的“挑剔”讓她很不舒服。英國《太陽報(bào)》舉例稱,1981年3月,剛剛宣布訂婚的二人首次“公開約會”,戴安娜為此精心挑選了一件黑色晚禮服。然而,這身裝扮卻遭到未婚夫的嫌棄。查爾斯當(dāng)時(shí)說:“你不會穿這么一身出去吧?這是服喪的人才穿的顏色!”王室婚禮令戴安娜承受了巨大壓力,為保持形象,她在短短5個月內(nèi)瘋狂減肥,將2.2尺的腰圍收縮至不到1.8尺,在此期間她還患上了嚴(yán)重的飲食失調(diào)癥。戴安娜在錄音中說,自己和這一頑疾的抗?fàn)幙梢恢弊匪莸胶筒闋査褂喕榈哪且恢埽?dāng)時(shí),后者摟著她的腰說了一句很“欠”的話:“你這里可胖了。”
1986年,戴安娜跟隨查爾斯出訪加拿大,參加溫哥華世博會。他們在世博會上逛了4個小時(shí),沒有吃東西。戴安娜感到非常餓,但又不敢和身邊的人說,因?yàn)樗麄冎粫阉脑挳?dāng)成抱怨。“我把手放在丈夫的肩膀上,說親愛的,我想我就要消失了。說完,我就在他身邊倒下了。”戴安娜說,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暈倒。
戴安娜被帶到一個房間休息。查爾斯很惱火,說戴安娜應(yīng)該安靜地在另一處暈倒,在門后邊暈倒,這一切實(shí)在太尷尬了。戴安娜說,她只是太餓了,但所有人都認(rèn)為她應(yīng)該好好休息,只有查爾斯堅(jiān)持認(rèn)為她應(yīng)該繼續(xù)參加晚上的活動,否則就會流言四起。
孩子出生后,戴安娜越來越受到公眾的喜愛。公眾的喜愛和王室內(nèi)部對她的忽視在戴安娜的生活中形成嚴(yán)重的反差。“對公眾來說,他們需要一個童話公主,只要公主摸一下他們,就能點(diǎn)石成金,就能讓他們忘卻一切的擔(dān)憂。”但公眾不知道戴安娜內(nèi)心承受的折磨,因?yàn)橥跏业娜丝偸钦J(rèn)為她不夠好,所以她也認(rèn)為自己不夠好,承受不了民眾的愛戴。
與此同時(shí),查爾斯開始嫉妒戴安娜得到的愛戴。一次,戴安娜和3歲的威廉王子一起游泳,因?yàn)橥踝臃噶隋e,戴安娜斥責(zé)了他,沒想到引起了威廉王子的回?fù)簦骸澳闶俏矣龅竭^的最自私的女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自己!”戴安娜驚呆了,威廉才3歲,她問威廉這話是聽誰說的,威廉說:“噢,我常聽爸爸這么說。”
如果說這些事只是“敗壞心情”,那么查爾斯與卡米拉的私情足以令戴妃“陷入絕望”。據(jù)稱,二人的不正當(dāng)關(guān)系早在查爾斯大婚前就已露出端倪:當(dāng)時(shí)卡米拉患病,查爾斯送上一捧鮮花,并留下曖昧字條“弗雷迪送給格拉迪斯”——這是之前兩人互起的愛稱。更嚴(yán)重的一次,戴安娜在浴室外聽到查爾斯和卡米拉的電話通話。查爾斯說:“無論發(fā)生什么,我都永遠(yuǎn)愛你。”戴安娜承認(rèn),丈夫的“不忠”令自己心神不寧、病情加重。
據(jù)莫頓回憶,他著手對戴安娜王妃進(jìn)行秘密采訪時(shí),這對王室夫婦間的矛盾已經(jīng)到了不可調(diào)和的程度。同丈夫溝通未果后,戴安娜曾找女王訴苦,但也沒能得到任何寬慰。戴安娜曾考慮帶孩子“出逃”澳大利亞,她還擔(dān)心自己可能會被當(dāng)成“精神病患者”拘禁起來。孤立無援的戴妃在整個王室中沒有任何可以信賴的人,即便是對密友科瑟斯特醫(yī)生也不敢完全開誠布公,其絕望程度可見一斑。
(摘自2017年6月13日《環(huán)球時(shí)報(bào)》)
賀龍:用兵就要愛兵
斯諾在《西行漫記》中這樣描寫賀龍:他的口才很好,說起話來能“叫死人活過來打仗”。但賀龍?jiān)谑勘薪⒊绺咄渥陨淼能娛虏拍芘c個人魅力才是根本。賀龍數(shù)十年一貫堅(jiān)持的“有鹽同咸,無鹽同淡”的理念,及“要用兵就要愛兵”的帶兵信念,是他深得將士之心的重要原因。
1928年春,南昌起義后的賀龍脫下皮鞋穿草鞋,回到湘西老家洪家關(guān)再舉義旗,拉起了3000多人的隊(duì)伍。在敵強(qiáng)我弱的形勢下,部隊(duì)受到挫折,9月底,轉(zhuǎn)移至湖北鶴峰堰埡附近的高山野林之中。經(jīng)過整頓,隊(duì)伍只剩下了91人、72條槍,共編成9個班。洪家關(guān)一帶的后方基地被敵軍侵占,人員補(bǔ)充、物資供應(yīng)都面臨著極大的困難。沒有糧食,戰(zhàn)士們常在野地里找野菜充饑,幾天吃不到一粒鹽,喝不上一口稀飯。有一次,炊事員想方設(shè)法弄到指頭大的一點(diǎn)鹽巴,給賀龍專門炒了一碗有鹽的辣椒。賀龍嘗了一口,便將那碗辣椒倒進(jìn)大鍋里。炊事員上前阻攔,賀龍笑著說:“有鹽同咸,無鹽同淡嘛!”endprint
1936年7月,時(shí)任總指揮的賀龍率紅二方面軍長征進(jìn)入漫無邊際的草地。起初戰(zhàn)士每人每天有3兩青稞面充饑,可沒過幾天就完全斷了糧。指戰(zhàn)員們只好挖野菜、刨草根吃,到后來連野菜和草根也挖不著了。有的戰(zhàn)士因過度饑餓,走著走著就倒下再也沒能站起來。賀龍神情嚴(yán)峻,走到他的棗紅馬跟前,愛憐地?fù)崦淖酌瑥?qiáng)忍內(nèi)心的痛苦,做出了殺馬的決定。賀龍愛馬如命,可是為了保住戰(zhàn)士們的生命,只有犧牲馬的性命。警衛(wèi)員們知道情況后,都傷心地哭了起來。賀龍內(nèi)心比他們更難過,但他說:“人對馬親,馬也對人親;我們愛馬,馬也愛我們。可是,戰(zhàn)士、戰(zhàn)馬不可皆得啊!”
1949年年底,賀龍指揮10萬大軍直插秦嶺山區(qū),與二野、四野大軍,對國民黨胡宗南潰軍形成南北夾擊攻勢。秦嶺山脈到處懸崖峭壁,只有一條川陜公路。賀龍看到汽車經(jīng)過時(shí)卷起大量塵土,路邊行軍的戰(zhàn)士忙不迭用手捂住口鼻,連忙叫停車,命令各部隊(duì)在安排行軍序列時(shí)要人車分開。賀龍說:“我們坐車,戰(zhàn)士走路,他們本來就很辛苦,再讓戰(zhàn)士們吃土怎么行啊!要用兵,就要愛兵。安排行軍序列,要盡量把汽車團(tuán)放在前面,讓車隊(duì)先走,部隊(duì)后走,把人和車錯開。”
1952年,時(shí)任西南軍區(qū)司令員的賀龍聽到反映,重慶北碚某部兩名軍官為自己蓋了一棟“小洋樓”,而附近高炮連戰(zhàn)士卻住在漏風(fēng)漏雨的蘆席棚里。他當(dāng)即約副司令員李達(dá)等一起到北碚進(jìn)行暗訪,情況果然屬實(shí)。走出蘆席棚后,賀龍給高炮連全體戰(zhàn)士恭恭敬敬地鞠了一個躬:“我賀龍對不住大家。我有官僚主義,到現(xiàn)在還讓你們住在漏風(fēng)漏雨的棚子里,我向你們道歉!”當(dāng)即下令兩名軍官一個星期內(nèi)把房子騰出來,讓高炮連搬進(jìn)去住。
1955年,賀龍到青島第四海軍學(xué)校視察。中午,學(xué)校請賀龍到食堂用餐。偌大一個食堂全騰了出來,師生們都聚在院子里,蹲在地上圍成一個個圓圈吃飯。賀龍的臉色頓時(shí)沉了下來,他一聲不吭地向蹲著吃飯的學(xué)員們走過去:“給我一個碗,我就在這里和你們一起吃。”一旁的蘇聯(lián)高級顧問見了,大惑不解地說:“元帥怎么能和士兵蹲在一起吃飯呢?”賀龍聽了,哈哈一笑:“顧問同志,這可是我們中國軍隊(duì)的傳統(tǒng)啊!”那位顧問看到賀龍真的蹲著和戰(zhàn)士一塊吃飯,聳了聳肩,只好陪著賀龍?jiān)谠鹤永锍粤艘活D飯。
(摘自2017年第5期《文史博覽》
耐煩有恒
我多次請書法家寫“耐煩”兩字。我雖然是一介布衣,仍然覺著“耐煩”事關(guān)做人做事的全部。
先解“耐煩”的基本義。耐,經(jīng)得起,受得住;煩,從火從頁,身體發(fā)熱了頭痛了,引申為煩悶、瑣碎。耐煩,就是要頂?shù)米∷闊┑娜撕褪隆R馑己唵危⒉淮砟茏龅阶龊谩?/p>
年輕時(shí)的曾國藩也曾風(fēng)流放蕩懶散,他做官后,將“居官以耐煩為第一要義”奉為座右銘,幾乎苛刻地遵從。耐,就是要和急躁浮泛作抗?fàn)帲撔模瑢R唬瑑?nèi)心鎮(zhèn)定。曾國藩深知,自己處事如果不急不躁,就能時(shí)刻保持頭腦清醒,如此,才能做出正確的決斷。后來,他將“耐煩”擴(kuò)大到做人做事的方方面面。他的觀點(diǎn)是,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怨天尤人不是辦法,只有摒除煩惱,直面現(xiàn)實(shí),冷靜思考,才能找出解決之道。
曾國藩的同鄉(xiāng)沈從文將“耐煩”的意義延伸為鍥而不舍、不怕費(fèi)勁。我是在汪曾祺的回憶文章《星斗其文,赤子其人》里讀到這些文字的。汪回憶:沈先生很愛用別人不太用的一個詞,“耐煩”。沈先生認(rèn)為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煩”。他對別人的稱贊,常說“要算耐煩”。看見兒子小虎搞機(jī)床設(shè)計(jì),勉勵“要算耐煩”。看見孫女小紅做作業(yè),也鼓勵“要算耐煩”。沈從文自己解釋:北方話叫發(fā)狠,我們家鄉(xiāng)話叫“耐煩”,要扎扎實(shí)實(shí)把基本功練好,不要想一蹴而就。
綜觀沈從文的一生,他真是“耐煩”的杰出踐行者。不說他文學(xué)成就的輝煌,單單是他的服飾研究成就,也達(dá)到了前人少有的高度。但是,有多少人能耐得住這個煩呢?
英國哲學(xué)家羅素在《快樂的世界》里,列出了一百多年前他那個國家的三類邪惡:一類是物質(zhì)的,如死亡、痛苦以及田地難以生產(chǎn)出糧食;二類是性格的,如愚昧無知、缺乏意志以及暴烈的脾氣;三類是權(quán)力的,殘暴專制,用武力或者用精神去干涉別人自由發(fā)展。羅哲學(xué)家認(rèn)為,三種邪惡相互牽制相互影響。解決的基本途徑是:用科學(xué)去對付物質(zhì)的,用教育去干預(yù)性格的,用改革去完善權(quán)力的。
其實(shí),我們完全可以將這些看成想躲也躲不開的煩惱。拆解煩惱的方法就是在“耐煩”中注入科學(xué)、教育、改革等生動活潑的因子,從而解決耐煩。
倡導(dǎo)生活禪的星云大師,用彼德懶得彎腰撿馬蹄鐵,爾后為了撿耶穌掉下的十八顆櫻桃彎腰十八次的故事,告誡人們,面對工作、家事、人情,更要“耐煩”。“耐煩”做人,才能把人做好。于是,我們就可以將“耐煩”的外延和內(nèi)涵進(jìn)一步拓展,比如,修養(yǎng),度量。
我可以毫不夸張地?cái)嘌裕伺c人的差異,就在“耐煩”和“不耐煩”之間。
“耐煩”且有恒,便能有一種平和的巨大力量,戰(zhàn)勝所有的煩人和煩事。
(摘自2017年6月19日《今晚報(bào)》)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