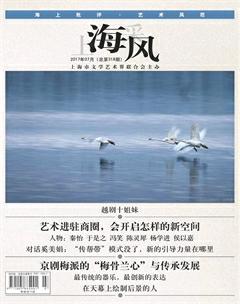“兩蕭”客居上海
丁言昭+馬信芳
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被稱為“兩蕭”的著名作家蕭軍和蕭紅無疑占有一席之地。而上海,是“兩蕭”文學(xué)生涯的重要轉(zhuǎn)折點(diǎn),兩人正是在這里聲名鵲起。今天,追念文壇前輩的足跡,重讀他倆曾在上海,為自己的“黃金時(shí)代”寫下的燦爛篇章,還真其味無窮。
丁言昭,當(dāng)代作家、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者。她已為丁玲、林徽因、陸小曼、安娥等九位“民國才女”立傳,其中在撰寫被譽(yù)為“三十年代的文學(xué)洛神”的蕭紅傳記時(shí),不僅向40余位曾經(jīng)接觸過蕭紅的文學(xué)前輩們征集資料,而且對(duì)蕭紅與蕭軍在上海的足跡作了大量的考證。丁言昭的“蕭紅傳”在大陸和臺(tái)灣前后出版過《愛路跋涉》《蕭蕭落紅情依依》等三個(gè)版本。評(píng)論家認(rèn)為,她以挖掘“活”的歷史資料寫蕭紅,無論當(dāng)時(shí)還是將來都極有人文和歷史價(jià)值。值得一提的是,蕭軍、蕭紅當(dāng)年客居上海,曾經(jīng)住過的拉都路(今襄陽南路)351號(hào),就在她的居所“慎成里”的后弄堂。那天,在丁言昭的引領(lǐng)下,我們特意來到當(dāng)年兩蕭的居所。丁言昭介紹說,徐匯區(qū)有關(guān)部門曾在這里門口掛過銘牌。可我仔細(xì)查看,現(xiàn)已杳無蹤影,大門口正被多輛破舊自行車和一些廢木料所“占據(jù)”。
今非昔比,感嘆中,丁言昭說述起她對(duì)兩蕭所作的研究。據(jù)現(xiàn)在掌握的資料,目前所知道的兩蕭在上海住過的地方有7處,而其中3處就在今日的襄陽路。
拉都路上幾春宵
馬:我知道你是位作家,怎么對(duì)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也有研究,尤其對(duì)兩蕭?
丁:這是我受父親的影響所致。我父親丁景唐長(zhǎng)期從事出版工作,同時(shí),他還是位現(xiàn)代文學(xué)史的研究者。他不僅在魯迅、瞿秋白研究方面撰有不少專著,而且對(duì)“左聯(lián)五烈士”和左翼文藝運(yùn)動(dòng)史方面頗有研究。生活在這樣家庭里,耳濡目染,對(duì)此已比較熟悉。父親與蕭軍相為朋友。關(guān)于我家后弄那個(gè)“351號(hào)舊址”,父親不僅早就與我們說過,而且經(jīng)常帶來客去拍照,成為追念文壇前輩的一個(gè)景點(diǎn)。1979年,我欲為蕭紅立傳,在為蕭紅整理年譜的同時(shí),我想到了蕭軍先生,于是給他去了信,請(qǐng)教他當(dāng)年與蕭紅在上海居住過的舊址和他們的寫作情況。當(dāng)年3月5日,蕭軍很快給我回了信,并提供了大量的資料。他還寫下了《在上海拉都路我們?cè)?jīng)住過的故址和三張照片》(后收入了蕭軍文集)。這些對(duì)兩蕭研究無疑十分重要,同時(shí)為我撰寫蕭紅傳提供了“活”的歷史資料。今天想來,依然彌足珍貴。
蒲柏路公寓、拉都路283號(hào)
馬:蕭軍和蕭紅是什么時(shí)候來上海的?
丁:兩蕭——兩個(gè)來自東北的“不甘做奴隸者”,嘗盡人間苦痛,卻對(duì)文學(xué)有著無限的熱愛和向往。1934年秋,蕭軍試著給心中敬仰的魯迅先生去了第一封信,希望得到文學(xué)上的指導(dǎo)。令他們沒有想到的是,魯迅在接信后就寫了回信。從此,兩位青年的人生就和大文豪魯迅的名字連在了一起。
同年11月2日,蕭軍、蕭紅和友人梅林乘坐日本輪船“共同丸”抵達(dá)上海。兩蕭住進(jìn)了位于法租界蒲柏路(今太倉路)上的一家公寓。
不過,在這里時(shí)間很短,因?yàn)樗麄兂惺懿涣税嘿F的房租。當(dāng)時(shí),兩人沒有收入,所以必須盡快尋找新的住處。也許是種緣分,當(dāng)蕭軍來到了拉都路(即今襄陽路,這條筑于1918年至1921年的拉都路,取于法國郵船公司職員之名。1943年10月,以湖北省的一縣名改名襄陽路而易用至今),他便在283號(hào),一家名為“元生泰”的小雜貨鋪前停住了腳步。他看到門上貼著的一張“招租”告示,說二樓的大亭子間要出租,便進(jìn)去察看了一番。這是一個(gè)南北向的長(zhǎng)亭子間,但有一個(gè)單獨(dú)的門可進(jìn)出。當(dāng)蕭軍得知房租每月僅9元時(shí),頓覺便宜,就租了下來。第二天兩蕭就搬了過去。
在新居,蕭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他的成名小說《八月的鄉(xiāng)村》。這里沒有陽光,沒有爐火,刺骨的寒風(fēng)從窗縫鉆進(jìn)。蕭紅披著大衣,幫蕭軍一字一字謄寫,她流著清鼻涕,時(shí)時(shí)搓搓凍僵的手指,或者跺跺腳,以此取暖。
很快,魯迅先生向他們發(fā)出了邀請(qǐng)。11月30日,兩蕭終于如愿與魯迅見面。這天對(duì)于兩蕭無疑是個(gè)喜慶之日。根據(jù)約定,兩蕭準(zhǔn)時(shí)來到了內(nèi)山書店。出人意料的是,魯迅已在那里等候他們了,這使蕭軍蕭紅有點(diǎn)不知所措。而魯迅卻平靜地問道:“是劉先生、悄吟女士嗎?”兩人迷亂地點(diǎn)著頭。接著,魯迅便引導(dǎo)兩蕭走出書店到一家不遠(yuǎn)的咖啡店。
初次見面可以說是極其令人愉快的。蕭軍把《八月的鄉(xiāng)村》手稿交給魯迅,希望先生給予指導(dǎo),并幫助尋找書店出版。魯迅喜歡蕭軍蕭紅的純樸爽直,而蕭軍蕭紅呢,他們完全被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征服,不由自主地傾倒在魯迅面前。不一會(huì),許廣平領(lǐng)著海嬰也來到了咖啡店。蕭紅與許廣平真是一見如故,特別是淘氣的滿嘴上海話的海嬰,也很快和蕭紅混熟了。許廣平曾以滿懷詩意的筆調(diào)描述這初次的會(huì)面:“陰霾的天空吹送著冷寂的歌調(diào),在一個(gè)咖啡室里我們初次會(huì)著兩個(gè)北方來的不甘做奴隸者。他們爽朗的話聲把陰霾吹散了,生之執(zhí)著,戰(zhàn)斗,喜悅,時(shí)常寫在臉面和音響中,是那么自然,隨便,毫不費(fèi)力,像用手輕輕拉開窗幔,接受可愛的陽光進(jìn)來。”
臨別,兩蕭接過了魯迅借給的20元錢。這是兩蕭在事前的信中提出的不得已的請(qǐng)求。因?yàn)閮墒挳?dāng)時(shí)生活真的很拮據(jù),已經(jīng)沒有錢買食油,天天的食譜就是白水煮面片,飄著幾根菠菜,僅剩的一袋面粉也快吃完。囊中羞澀,才向魯迅求助。
對(duì)先生的關(guān)愛,兩人回家后就寫信感謝,同時(shí)表達(dá)了自己的心情。對(duì)此,12月6日魯迅馬上回信寬慰他們:“來信上說到用我這里拿去的錢時(shí),覺得刺痛,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個(gè)俄國的盧布,日本的金圓,但因出版界上的資格關(guān)系,稿費(fèi)總比青年作家來得容易,里面并沒有青年作家的稿費(fèi)那樣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緊。而且這些小事,萬不可放在心上,否則,人就容易神經(jīng)衰弱,陷入憂郁了。”
面對(duì)兩個(gè)流亡的文學(xué)青年,魯迅像慈父般的疼惜、憐愛,更有關(guān)懷。
因?yàn)橹浪麄冊(cè)谏虾o親無友,于是想給他們介紹幾個(gè)可靠的朋友。在12月17日的信中,魯迅寫道:“本月十九日(星期三)下午六時(shí),我們請(qǐng)你們倆到粱園豫菜館吃飯,另外還有幾個(gè)朋友,都可以隨便談天的。粱園地址是廣西路三三二號(hào)。廣西路是二馬路與三馬路之間的一條橫街,若從二馬路彎進(jìn)去,比較的近。”endprint
魯迅怕他們不熟悉路,不厭其煩地說明。面對(duì)先生如此細(xì)心的筆致,蕭軍他們收到信時(shí),先是蕭紅流下了眼淚,接著,蕭軍的雙眼也濕潤(rùn)了起來:“我們這兩顆漂泊的、已經(jīng)近于僵硬了的靈魂,此刻竟被意外而來的偉大的溫情,浸潤(rùn)得近乎難以自制地柔軟下來了,幾乎竟成了嬰兒一般的靈魂!”
這次飯局,魯迅向兩蕭介紹認(rèn)識(shí)了葉紫、茅盾和聶紺弩、周穎夫婦。兩蕭由此進(jìn)入了上海文壇。這些人后來都成為兩蕭的好朋友,對(duì)他們的創(chuàng)作和生活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
馬:在建國前的四十年代老地圖上,拉都路283號(hào)還是叫“元生泰”的雜貨鋪。現(xiàn)在它的位置在哪里?
丁:當(dāng)年的拉都路283號(hào),在現(xiàn)在的永嘉路、襄陽南路口往北一點(diǎn)。不過,原來的沿街房子已被拆除,建起了新的樓房,但底層依然是一排店鋪。我在拆除沿街舊房之前特已拍攝了照片,但是后面的亭子間早已無蹤影了。
拉都路411弄22號(hào)
馬:1935年1月2日,蕭軍寫信給魯迅,說是又搬家了。他們搬哪兒了?
丁:依然在拉都路,不過移到了南段。這是拉都路411弄,名為福顯坊的22號(hào)。走進(jìn)弄堂左拐,最后一排房子的第一幢。當(dāng)時(shí)那里屬于城市邊緣地帶,比較偏僻,沒有什么醒目的建筑,只有兩片菜地,圍著竹籬笆,還有種菜人住的一些破爛的平房。
這里每月房租11元。對(duì)此新居和環(huán)境,蕭軍感到很滿意。魯迅在回信中也稱道:“有大草地看,要算新年幸福……”蕭軍還把從東北帶來的一幅自己肖像油畫掛在墻上。突然,他倆發(fā)覺新居只有一單床,他們想分床,而口袋里的錢所剩無幾,于是只能想法借了。在葉紫的介紹下,兩蕭來到呂班路(今重慶路)木刻家黃新波的住處。黃新波是葉紫《豐收》封面的設(shè)計(jì)作者(后來也為蕭軍的《八月的鄉(xiāng)村》設(shè)計(jì)封面),和葉紫相熟。于是當(dāng)場(chǎng)借給兩蕭一張鐵床,并叫了兩輛黃包車,把他們送走。
新居給兩蕭帶來了創(chuàng)作激情。蕭軍一口氣創(chuàng)作了短篇小說《職業(yè)》《櫻花》《貨船》《初秋的風(fēng)》《軍中》等,其中《職業(yè)》經(jīng)由魯迅介紹,刊登在《文學(xué)》第4卷第3號(hào)上,這是他在上海公開發(fā)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拿到38元稿酬,這足足可以交3個(gè)月的房租了。
蕭紅也開始在上海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活動(dòng),撰寫了《小六》《過夜》等散文,其中《小六》經(jīng)由魯迅介紹,刊登在陳望道主編的《太白》雜志上。
搬到新居后,兩人迎來了除夕之夜。這是他們第一次在上海歡度春節(jié)。
拉都路351號(hào)
馬:接著,該是他們第三次搬家了吧。
丁:是。沒過幾天,一日,門外響起了青島朋友的熟悉聲,他們是來上海“闖天下”的。幾位熱情朋友對(duì)兩蕭的新居發(fā)了一通議論后,表示應(yīng)該租闊氣一點(diǎn)的住房,并要與兩位住在一起。就這樣,他們?cè)陔x福顯坊五六分鐘的路程找到了新居。這就是你現(xiàn)在看到的拉都路(今襄陽南路) 351號(hào)。
這是幢西式樓房。兩蕭住在三樓,幾個(gè)朋友分別住在底層和二樓。這里房間的外觀和內(nèi)部條件自然比福顯坊優(yōu)越多了。不過,每月的房租也隨之增高,三個(gè)樓面共要56元。
馬:據(jù)說,兩蕭已開始習(xí)慣上海人的生活,早上在這里吃起了大餅、油條。
丁:對(duì)。早晨,蕭紅常到對(duì)馬路的一個(gè)早攤點(diǎn),買大餅、油條作為早餐。一天,蕭紅在買油條時(shí),竟然發(fā)現(xiàn)包油條的紙竟是魯迅翻譯班苔萊夫的中篇童話《表》的手稿(該譯文發(fā)表在1935年3月16日出版的《譯文》月刊第2卷第1期),感到十分意外。隨后兩蕭就把手稿寄給魯迅,表示“憤懣”,并請(qǐng)魯迅要把手稿催討回來。而魯迅卻不以為然,還幽默地稱,自己的手稿居然還可包油條,可見還有點(diǎn)用處。
馬:那魯迅先生的手稿怎么會(huì)流落到攤點(diǎn)上的呢?
丁:這拉都路324弄,名為敦和里,是條四通八達(dá)的大弄堂。當(dāng)時(shí)《文學(xué)》《譯文》《太白》編輯部就設(shè)在這里。他們和魯迅關(guān)系密切,其中兩個(gè)刊物還刊登了兩蕭在上海第一次發(fā)表的文學(xué)作品。《譯文》曾由魯迅主編,后由黃源接手。魯迅的翻譯手稿正是從該編輯部流散出去的。黃源后來得知,懊悔不已。
馬:魯迅先生對(duì)蕭軍蕭紅的關(guān)心,可謂無微不至,不僅是引路的導(dǎo)師,而且還給予父輩一樣的愛。據(jù)說,先生曾親臨拉都路351號(hào)上門探望。
丁:是。這是1935年5月2日上午,樓梯上突然響起了腳步聲,兩蕭打開房門一看,原來是魯迅先生帶著許廣平和海嬰一家三口,這讓兩蕭驚喜不已,急忙請(qǐng)讓他們進(jìn)屋。魯迅點(diǎn)起了香煙,并帶來了愉悅和說不盡的話題,滿屋洋溢著歡樂的氣氛。
一小時(shí)后,魯迅先生邀請(qǐng)兩蕭外出吃飯,地點(diǎn)是霞飛路上的―家西餐館。飯后,兩蕭送魯迅全家上了電車。當(dāng)天魯迅在日記里寫道:“晴。上午同廣平攜海嬰往拉都路訪蕭軍及悄吟(即蕭紅),在盛福午飯。”據(jù)眾多專家考證,查看上世紀(jì)四十年代相關(guān)資料,在拉都路與霞飛路口向東拐四五十米,有一家“德盛福食物號(hào)”,門牌為1013號(hào)(近路口為1023號(hào),解放初為天津小吃部,后改名為“燕京樓”)。雖然此店名比魯迅說的多了一個(gè)“德”字,但很有可能就是這一家。遺憾的是,如今這一帶建筑已大大變樣,再也無法尋找舊址了。
當(dāng)天兩蕭回家后,又分別忙碌起來。蕭紅趕寫一組回憶散文,那就是后來知名的《商市街》。“商市街”是哈爾濱的街名,兩蕭曾住在那里,“貧窮和饑餓”的可怕陰影一直追隨著他倆。
《生死場(chǎng)》力透紙背
馬:從兩蕭生前的相關(guān)記載看,兩人在拉都路351號(hào),只住到當(dāng)年6月。
丁:沒想到,魯迅先生這次來訪引起了與他們住在一起的朋友的不滿。當(dāng)晚,朋友就責(zé)怪蕭軍怎么不把魯迅介紹給他們。后來又因這些朋友所托的幾件事,蕭軍未能辦成。于是,雙方之間關(guān)系就此冷落下來。這促使兩蕭要搬離拉都路。
離開拉都路后,兩蕭先是住在薩坡賽路(今淡水路)190號(hào)。那里是唐豪律師事務(wù)所。唐是兩蕭的朋友,與史良是同學(xué),曾為“七君子”辯護(hù)。
1936年3月,兩蕭干脆搬到了北四川路底的“永樂里”(可能是永安戲院近鄰的“永樂坊”,今四川北路1774弄及海倫路73弄)。這距離魯迅先生家近了,兩人幾乎每天晚飯后都要去大陸新村魯迅家。這時(shí),兩蕭已成上海有名的作家夫婦,《八月的鄉(xiāng)村》《生死場(chǎng)》等作品讓兩人登上文壇而熠熠閃光。endprint
1935年6月,蕭軍的《八月的鄉(xiāng)村》在魯迅的關(guān)心下,以奴隸叢書出版,魯迅稱這個(gè)發(fā)生在哈爾濱附近的一個(gè)偏僻村莊、而且是崛起的最初階段、是野生的奮起的故事,“顯示著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xiàn)在和未來,死路和活路”(魯迅《八月的鄉(xiāng)村》序)。書一出版立即引起很大反響。
而蕭紅的《生死場(chǎng)》幾經(jīng)磨難后,也于同年12月出版。
《生死場(chǎng)》以淪陷前后的東北農(nóng)村為背景,真實(shí)地反映舊社會(huì)農(nóng)民的悲慘遭遇,以血淋淋的現(xiàn)實(shí)無情地揭露日偽統(tǒng)治下社會(huì)的黑暗。同時(shí)也表現(xiàn)了東北農(nóng)民的覺醒與抗?fàn)帲乃啦划?dāng)亡國奴、堅(jiān)決與侵略者血戰(zhàn)到底的民族氣節(jié)。
蕭紅對(duì)人性、人的生存這一古老的問題進(jìn)行了透徹而深邃的詮釋。這種對(duì)人生的生存死亡的思索,超出了同時(shí)代的絕大部分作家。魯迅先生深夜為之寫序,贊曰:“北方人民的對(duì)于生的堅(jiān)強(qiáng),對(duì)于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jīng)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xì)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魯迅還把《生死場(chǎng)》交給來訪的胡風(fēng),要他就這部書寫點(diǎn)文字以便讀者理解。胡風(fēng)應(yīng)承下來,很快拿出了“讀后記”:“……《生死場(chǎng)》的作者是沒有讀過《被開墾了的處女地》的,但她所寫的農(nóng)民們對(duì)于家畜(羊、馬、牛)的愛著,真實(shí)而又質(zhì)樸,在我們已有的農(nóng)民文學(xué)里面似乎還沒有見過這樣動(dòng)人的詩篇”,“使人興奮的是,這本不但寫出了愚夫愚婦的悲歡苦惱而且寫出了藍(lán)空下的血跡模糊的大地和留在那模糊的血土上的鐵一樣重的戰(zhàn)斗意志的書,卻出自一個(gè)青年女性的手筆。在這里我們看到了女性纖細(xì)的感覺也看到了非女性雄邁的胸境”。
《生死場(chǎng)》由此成為一個(gè)時(shí)代民族精神的經(jīng)典文本。誠如許廣平所說,《生死場(chǎng)》“作為東北人民向征服者抗議的里程碑的作品”,其面世“無疑地給上海文壇一個(gè)不小的新奇和驚動(dòng)”。“是蕭紅女士和上海人初次見面的禮物”。這部作品奠定了蕭紅作為抗日作家的地位,蕭紅的名字不脛而走,成為上世紀(jì)三十年代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
幾個(gè)月后,兩蕭搬到呂班路南端(過辣菲德路),今重慶南路256弄7號(hào)。這是由接連幾個(gè)門牌號(hào)組成的整幢兩層西班牙式建筑,有臺(tái)階、弧形拱門窗、半圓石柱裝飾,挺有氣派。這里周圍多為花園住宅。當(dāng)時(shí)房客多為俄國人。東北作家也曾聚住在此。從256弄拐進(jìn)去,前面有2號(hào)至7號(hào),7號(hào)一旁是公利醫(yī)院,256弄南面緊鄰是教會(huì)的“味增爵會(huì)墳地”、法國華僑集資創(chuàng)建的伯多祿教堂和震旦大學(xué)運(yùn)動(dòng)場(chǎng)(現(xiàn)為上海二醫(yī)大)。在256弄朝西出口可通到有名的周公館(臨思南路)。弄堂口朝東出口的斜對(duì)面是鄒韜奮故居(現(xiàn)為韜奮紀(jì)念館)。
如今這里為了建造高架,已經(jīng)拆除不少建筑,原來的2號(hào)至4號(hào)建筑已不復(fù)存在,只剩下5號(hào)至7號(hào),5號(hào)已臨街。這里往北一點(diǎn)就是復(fù)興中路口,對(duì)面是復(fù)興公園(1900年為法軍兵營,后辟建顧家花園,俗稱法國花園,蕭軍回憶中還常提及)。
馬:蕭紅在這里沒住多久就去了日本東京,這為什么?
丁:在魯迅先生日記里,1936年4月13日,還出現(xiàn)蕭軍、悄吟(蕭紅)的名字,并一起去上海大戲院(后改為倉庫,今遺址在四川北路1408號(hào))觀看蘇俄影片《夏伯陽》。此后日記中兩蕭名字消失了。直到同年7月7日,魯迅日 記中才出現(xiàn)蕭軍一人的名字,他是前來還50元錢的。
原來兩蕭的感情出現(xiàn)了裂縫。他們兩人,一個(gè)好動(dòng),一個(gè)好靜;一個(gè)強(qiáng)壯,一個(gè)柔弱;一個(gè)愿從武,一個(gè)想從文,這種性格的差異,導(dǎo)致了后來他們最終在西安的分手。而在上海,應(yīng)該看到,他們?cè)诟星樯弦延辛芽p。為此,兩人商量“廝守不如小別”,決定分開一年。蕭紅去東京寫作,蕭軍回青島,相約一年以后再相見。
1936年7月15日,魯迅在日記中這樣記載:“晚廣平治饌為悄吟餞行。”這是說,魯迅在家設(shè)便宴,許廣平還親自下廚做菜,為蕭紅餞行。兩天后,蕭紅走了。
有意思的是,兩人雖在感情上有縫隙,但拉開了距離反讓他們情意綿綿,借著鴻燕,互訴衷腸。
1936年7月26日,蕭紅到東京的第六天,她覺得特別寂寞,想哭,給蕭軍寫信說:“這里的天氣也算很熱,并且講一句話的人也沒有,看的書也沒有,報(bào)也沒有,心情非常壞,想到街上去走走,路又不認(rèn)識(shí),話也不會(huì)講。昨天到神保町的書鋪去了一次,但那書鋪好像與我一點(diǎn)關(guān)系也沒有,這里太生疏了,滿街響著木屐的聲音,我一點(diǎn)也聽不慣這聲音。這樣一天一天的,我不曉得怎樣過下去,真是好像充軍西伯利亞一樣。”
大約是不習(xí)慣東京的天氣,蕭紅到了東京后就傷風(fēng)感冒,信里屢屢和蕭軍說到,但關(guān)于寫作,她絲毫沒敢懈怠。8月30日晚的信里,她寫道:“二十多天感到困難的呼吸,只有星座是平靜的,所以今天大大的歡喜,打算要寫滿十頁稿紙。”
1936年9月4日,蕭紅到東京近一個(gè)半月,已完成一個(gè)三萬字的中篇小說《家族以外的人》。蕭軍大概在信里罵蕭紅不會(huì)照顧自己,老是得病。雖然是借著罵來表達(dá)愛,蕭紅卻不領(lǐng)情,提出欲和蕭軍比比寫作速度。果然,她十天里竟寫了五十七頁稿紙。蕭紅的一系列鄉(xiāng)村生活記憶小說在這里完成的……
1937年春,當(dāng)兩蕭再次在上海呂班路256弄7號(hào)相聚時(shí),魯迅先生已去世,自此兩人再也聆聽不到先生的教誨了。
關(guān)于7號(hào)公寓兩蕭的生活諸事,留下的資料并不多。蕭軍曾說過一件事:蕭紅在這公寓里曾用碳筆畫了一副蕭軍“寫作時(shí)的背影”,那時(shí)她在“白鵝畫會(huì)”里學(xué)畫,使用碳條、畫紙很方便。此畫起因是她一時(shí)寫不出文章,而看著蕭軍光著上身在大寫特寫,心里很“嫉妒”,也很生氣,一“怒”之下就畫了這幅速寫。事后,蕭紅將此原因告訴了蕭軍,此畫一直被蕭軍所保存,其中所蘊(yùn)涵的豐富情感和那段難忘的歲月,都讓蕭軍感慨不已。
1937年9月上旬,兩蕭結(jié)束了客居上海近三年的日子,離開上海前往武漢。
塵封的記憶被轟開
馬:四十多年后,你去信蕭軍,請(qǐng)教當(dāng)年他與蕭紅在上海的舊事。蕭軍怎么說?
丁:1979年,當(dāng)時(shí)蕭軍先生已經(jīng)72歲。他接到我的信,特別是要他告訴上海的足跡,蕭軍稱,我的信,一下把他那塵封的記憶轟開了。3月5日和3月15日,他兩次給我回了信。蕭軍不僅寫下了他們?cè)谏虾@悸返鹊氐脑?jīng)經(jīng)歷,在3月15日的信里,還賦詩一首題為《憶故巢》。3月23日,蕭軍又特意來信,對(duì)其所寫的詩,說要改動(dòng)兩個(gè)字。這是蕭軍對(duì)他與蕭紅生命中那一段感情生活最真摯的記憶。其不忘初心,還是那么認(rèn)真:
夢(mèng)里依稀憶故巢/拉都路上幾春宵/雙雙人影偕來去/藹藹停云瞰暮朝/緣結(jié)緣分終一幻/說盟說誓了成嘲/閑將白發(fā)窺明鏡/又是東風(fēng)曳柳條。
馬:我記得,蕭軍去世前還來過上海。
丁:是,又過了七年,1986年10月,蕭軍先生應(yīng)上海魯迅紀(jì)念館之邀重回上海故地,并來到“慎成里”——我們家里。遺憾的是,我當(dāng)時(shí)正在北京出差,未能當(dāng)面向他請(qǐng)教。據(jù)我父親說,蕭軍不僅與我父母(當(dāng)時(shí)母親還健在)合影留念,還在父親陪同下,穿過后弄堂來到當(dāng)年“舊居”——那幢粉黃色拉毛外墻的公寓探訪。撥開繚繞的歷史煙塵,勾起他對(duì)諸多往事的回憶。毋庸置疑,一種特殊的情感油然而生。“拉都路上幾春宵”,老作家感慨萬千。這也是蕭軍對(duì)他與蕭紅客居上海、對(duì)老弄堂時(shí)光的最后一次致意。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