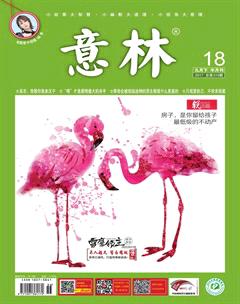久病床前的掃地僧
華明明
T大姐提醒我觀察一個有趣的現實,單位發體檢報告時,拆看毫無心理負擔的,多半是30歲以下的姑娘小伙子;而放在那里久久沒有勇氣拆看的,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其表情好像是對高考發揮沒底的學生,這會兒卻要面對要命的分數條一般。
T大姐在我單位負責書籍的勘校。她敏銳覺察到的這種忐忑不安,就是每個中年人心境的必由之路——上一代已經差不多進入耄耋之年,急需精神的、體力的、金錢的全方位扶持;而下一代書還沒有讀完,工作還沒有找到,對象與房子都沒有解決。我們這些已經走向疲憊衰老的中流砥柱,不得不站在命運的激流中,幫上下兩代人抵擋這些驚濤駭浪。這個時候,最可怕的,就是這根中流砥柱也扛不住壓力。
T大姐自己的故事,恰能說明這一切。
有天我去向T大姐請教校對清樣上的問題:在道光年間,有一位躲在尼姑庵里吸鴉片而促使道光帝下決心禁煙的莊親王,是叫什么名字?校樣上寫的名字是奕寅,看著就不對,然而我查閱了清代親王的世襲制度,越看越不能確認這一位莊親王,究竟是第幾代世襲的親王。因為清代的世襲制度不僅要看長幼,還要看功勛;若中途有親王被罷黜,之后由家族中的哪位男丁來襲爵,就更沒有譜了。
誰曉得我的難題,在T大姐看來完全不是問題。她閉眼思索了一會兒,問我:“是不是道光十八年在靈官廟中被查出來吸鴉片的那位莊親王?”我答:“是。”
她毫不猶豫地把莊親王的名字寫給我:奕镈。還解釋說,镈字既是鐘磬類的樂器,又是一種鋤頭般的農具。在清代,農業與禮樂一樣受到皇家的重視。
再次仔細查閱那段歷史,果然是。我大吃一驚,以為自己遇見了掃地僧式的清史專家!
T大姐淡淡地說,30年前,她念中學時,歷史很差的,尤其是背各種大人物的生辰與卒年,背各種大事年表,背得腦袋里一團糨糊。然而45歲之后,卻迷上了看各種歷史書籍。
契機說起來很心酸。7年前,T大姐76歲的老父親因腎衰開始每周三次的血透,那個階段老人家已經被腎衰折磨得體力衰弱,每次去醫院血透都需有人扶持、看護。而T大姐的老母親已經79歲,顯然不堪當此大任。于是這任務就落在長女身上,T大姐白天上班,晚上陪護父親血透到10點,再打車送他回家。血透病床前,T大姐起初拼命地承歡膝下,搜腸刮肚要找些新鮮有趣的話題來安慰父親,但父親半閉著眼,已經不太有精神回應。父親不忍看到女兒陪護的時間這樣荒廢,就說,你從圖書館借些書來看,年深日久,也長些見識。爸爸已經拖累了你,當然不希望你將來回憶這段時間,只剩下滿滿的犧牲感。
T大姐就開始在血透病床前看書。她看的第一本書是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看完明朝,又看清朝,這兩個朝代,從來源于正史的歷史小說,到專家的學術講義型的暢銷書,到有歷史專家把關的影視劇本,再到各種個性化的人物傳記。歷史書籍不像探案、推理書籍,一拿起來就放不下,方便她隨時觀察父親的狀況,該喊護士喊護士,該喊醫生喊醫生,從來沒有耽誤看護的正事。到后來,連T大姐自己也驚訝,那些枯燥的歷史知識,都在她腦子里連成了一張有彈性、有光澤、有捕獲能力的蛛網。只要一有問題像飛蟲一樣蒞臨,她馬上就能捕捉、響應、消化。
她鍛煉出了歷史學掃地僧的功夫,在無意中。
她從未跟任何人說起過自己的壓力。唯有一點出賣了她:每年的體檢報告,她都不敢看。必須由一位要好的同事,幫她拆封細看過之后,告訴她結果。
(大浪淘沙摘自《羊城晚報》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