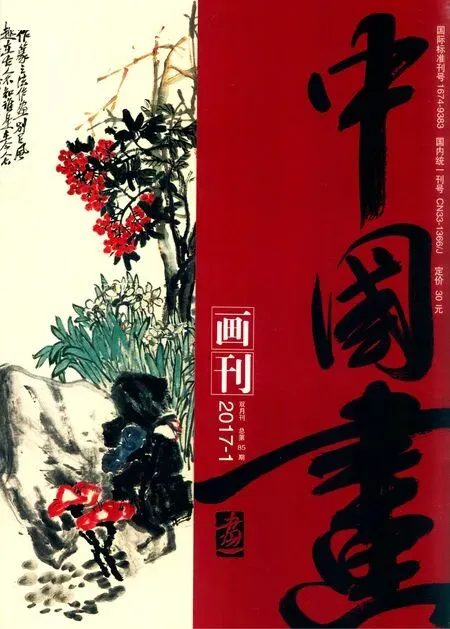有氣韻方可生動—智能時代傳統(tǒng)書畫藝術(shù)的不可替代性
文/鄭利權(quán)
有氣韻方可生動—智能時代傳統(tǒng)書畫藝術(shù)的不可替代性
文/鄭利權(quán)

鄭利權(quán)
書法家、策展人、美術(shù)評論家。現(xiàn)為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會員、浙江省書法家協(xié)會理事、浙江美術(shù)館學(xué)術(shù)部副主任。
伴隨著科技的高速發(fā)展,機器人技術(shù)的日新月異,機器視覺和人工智能的發(fā)展正在將藝術(shù)拉下神壇,幾乎人類智能的一切領(lǐng)域都正在被人工智能所解構(gòu)和顛覆,傳統(tǒng)書畫藝術(shù)也不例外,美術(shù)院校要辦人工智能專業(yè),機器人書畫家將對傳統(tǒng)書畫行業(yè)形成徹底的變革,所有書畫家將面臨失業(yè)的危險。在學(xué)術(shù)界,人工智能應(yīng)用于書畫創(chuàng)作的理論研究也在深入開展。早在2007年,浙江大學(xué)徐頌華先生便以《中國書畫藝術(shù)電子化創(chuàng)作的初步算法性探索》為題開展博士論文的研究,對中國書畫藝術(shù)電子化創(chuàng)作中涉及到的若干智能設(shè)計與美學(xué)創(chuàng)作的重要問題以計算機科學(xué)研究的方式展開了一系列算法設(shè)計工作與軟件工程的實踐。論文涉及三個方面:一是計算機智能書法生成的研究;二是國畫分解及國畫風格動畫智能生成技術(shù)的研究;三是交互式中國書畫創(chuàng)作的研究。

阿里云利用AI機器人為員工寫對聯(lián)

阿里云利用AI機器人為員工寫出的對聯(lián)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英文縮寫為AI。它是研究、開發(fā)用于模擬、延伸和擴展人的智能的理論、方法、技術(shù)及應(yīng)用系統(tǒng)的一門新的技術(shù)科學(xué)。人工智能企圖了解智能的實質(zhì),并生產(chǎn)出一種新的能以人類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應(yīng)的智能機器。人工智能是對人的意識、思維的信息過程的模擬。人工智能不是人的智能,但能像人那樣思考,也可能超過人的智能。人工智能因其強大的數(shù)據(jù)處理與分析能力,對藝術(shù)形態(tài)形成強烈沖擊。人工智能是數(shù)字技術(shù)的產(chǎn)物,更容易對電影、音樂、裝置藝術(shù)等具有聲光電特色的藝術(shù)形態(tài)產(chǎn)生影響與觀念變革。在傳統(tǒng)書畫藝術(shù)領(lǐng)域,藝術(shù)技法可以被嚴密數(shù)學(xué)化,并且可以被提取、變換和轉(zhuǎn)移,但是藝術(shù)風格、性情、學(xué)養(yǎng)與功力是人工智能不可復(fù)制、不可摹仿,更是不可替代的。

會繪畫的機器人

會寫書法的機器人

會打乒乓球的機器人
其一,學(xué)養(yǎng)是電腦難以逾越的鴻溝。中國傳統(tǒng)書畫藝術(shù)追求法度,追求書卷氣、文人氣,使傳統(tǒng)書畫不僅成為人們用來記敘和表述思想的實際手段,更用書畫藝術(shù)來體現(xiàn)文人的才情和學(xué)養(yǎng),所謂“字如其人”。清代劉熙載《藝概》說:“書,如也,如其學(xué),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 學(xué)養(yǎng)是衡量一位書法家是否合格的基本標準,書卷氣就是作品中自然流露出來的郁郁勃勃的文雅氣象,是評價書法優(yōu)劣高下的重要標準之一。清代書法家楊守敬說:“一要人品高,品高則下筆妍雅,不落塵俗;一要學(xué)問富,胸羅萬有,書卷之氣,自然溢于行間。” 學(xué)養(yǎng)不僅是知識淵博,更是一種氣質(zhì),人工智能在知識方面似乎有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具有海量的知識存儲空間,但要具備學(xué)養(yǎng)有著難以逾越的鴻溝。
其二,情感是電腦無法掌握的密碼。傳統(tǒng)書畫藝術(shù)是一個渲泄藝術(shù)家情感的藝術(shù)形態(tài),通過筆墨與線條的造型功能,營構(gòu)一種表現(xiàn)情感的形式。書畫藝術(shù)表現(xiàn)的語言是訴之于意象,也就是把情感形式化。書法表現(xiàn)語言的情感形式化,是通過線條、墨色、節(jié)奏、章法等方式來呈現(xiàn)的,比如王羲之《蘭亭序》的情感表現(xiàn)是“清靜雅幽”,我們看到了親近自然、逸情山水的魏晉風度。這種情感表現(xiàn)通過細膩的用筆、秀美的結(jié)構(gòu)、酣暢流美的筆勢來呈現(xiàn);而顏真卿《祭侄稿》的情感表現(xiàn)是“悲憤慷慨”,整幅章法雜亂,用筆時緩時急,字形時大時小,行距忽寬忽窄,用墨或燥或潤,筆鋒有藏有露,隨情揮灑,任筆涂抹,蒼涼悲壯,躍然紙上。藝術(shù)情感的本質(zhì)是一種生命性,這是機械性電腦所無法達到的。人工智能再發(fā)展,也無法捕捉到細膩入微的藝術(shù)情感。人工智能不可能產(chǎn)生情感,其創(chuàng)作素材只能是色彩或文字符號之類的存儲,其作品只能是停留于技術(shù)的產(chǎn)物。
其三,個性是電腦難以企及的能力。個性化是中國傳統(tǒng)書畫藝術(shù)的精神,個性是書畫家的標識,是真實且不可摹仿的。在古代書畫創(chuàng)作論中,關(guān)于“如何評價偉大之作”無疑有過不少定論的,其中之一便是對“個性”的推崇。無論是二王、顏柳歐趙,還是四王、八大、石濤,舉凡古代書畫大家,都注重“個性”,使個人藝術(shù)風格呈現(xiàn)出唯一性。這種個性既是書畫家個人情感的表征,也是其學(xué)養(yǎng)、精神、性情等藝外之旨的印證。人工智能可以完成對于藝術(shù)作品與藝術(shù)風格的模仿與復(fù)制,而且只能局限于技法圖像層面的仿制。

機器人自動添加制作披薩的番茄醬
其四,感悟是電腦無法逾越的屏障。感悟形態(tài)是中國書畫藝術(shù)的潛形態(tài),它潛藏于由線條構(gòu)筑的直覺造型中。這一直覺造型所孕含的意義往往是一種超時空的人生感悟和哲理思致,是莊子所言的“道”或海德格爾所言的“在”的神秘隱約的顯示。書畫藝術(shù)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蘊含的豐厚的詩性智慧是融哲學(xué)思想與文藝思想于一體,展示出一種超越邏輯和知識的靈性。中國書畫精神的感悟形態(tài)集中于對“道”的理解與體悟之上。徐復(fù)觀曾指出“道”的精神就是中國傳統(tǒng)藝術(shù)的最高精神,這種精神是以老莊道學(xué)為基本精神,蘊含著華夏民族深沉而又博大的宇宙觀、人生觀以及社會歷史觀。感悟是電腦無法逾越的屏障,“道”在書畫藝術(shù)中看不到,摸不著,卻又是客觀存在的。人工智能要掌握書畫藝術(shù)的“道”,既不現(xiàn)實,也無可能。
勿庸置疑,人工智能應(yīng)用于書畫創(chuàng)作,豐富了表現(xiàn)手段,開拓了想象空間,在書畫觀念、創(chuàng)作格局等方面,對人類的傳統(tǒng)創(chuàng)作提出了挑戰(zhàn)。但本質(zhì)上屬于機器的人工智能,尚無法創(chuàng)作出真正具有人性境界的作品。從書畫藝術(shù)的特質(zhì)來看,有其人工智能所無法企及的特性,因而是不可替代的。傳統(tǒng)書畫藝術(shù)因此消亡的觀點,更是杞人憂天。
傳統(tǒng)書畫藝術(shù)講究“氣韻生動”,無氣韻何以生動?筆之氣韻,線之氣韻,墨之氣韻,其本質(zhì)是人之氣韻,人工智能不可能產(chǎn)生氣韻,即使能掌握用筆的技法與造型,其創(chuàng)作作品必然是機械的、無生機的。總之,傳統(tǒng)書畫藝術(shù)是一個永恒的生命體,是經(jīng)過數(shù)千年發(fā)展累積而形成的一個具有旺盛生命力和超級穩(wěn)定結(jié)構(gòu)的藝術(shù)體,有其自身的發(fā)展軌跡,不會因為外在因素的變遷而改變其核心基因或者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