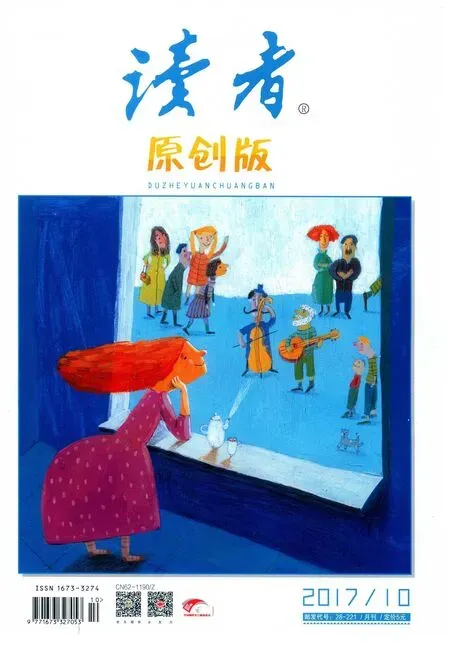花臉伴了他們好多年
文|南在南方
花臉伴了他們好多年
文|南在南方

我問父親:“花臉回來了沒有?”“沒,”父親說,“自從那天下午從麥地朝西邊梁上走了,再沒有回來。我還讓你媽去喚了的,它沒回。”
花臉是一只公貓,一只像狗一樣的貓,它喜歡跟在父親的身后,悄無聲息地跟著。如果父親坐下來,它就會突然現身,臥在父親膝下。有時也調皮,轉圈子抓自個兒的尾巴,許是轉暈了頭,突然跌倒。父親哈哈地笑,說花臉就像我小時候。
后來花臉大了,一些春天的夜里,它離家很遠,求偶或者捕食去。父親給它留著門,它習慣黎明回來。
可花臉這一次卻離家一個多月沒有蹤影。
我習慣每天給父親打電話問安,總要問到花臉。父親問我為啥老是問花臉,我一下愣在那里,沒有話說。之后,還是照問花臉回來沒。
我和弟弟妹妹長大之后,都離開了父母。幾間老屋,四個老人。后來祖母去世了,剩下父母和祖父。再后來,祖父走了。
父親說天天都是重陽節。他的語氣安詳,那一刻,我心里揪得有點兒緊。
有一回看電視上說植物,說它的第一片葉子總是離根最遠。我立刻給父親打電話說:“我是你的第一片葉子。”父親被我這句話弄得一頭霧水。我說了原因,父親笑著說:“離根再遠的葉子最后也會落在根上嘛。”
依然語氣安詳。可是等我老了,他在哪里呢?這話終是沒有問他,可是我們是說過死亡的。
老話說“多年父子成兄弟”,有些道理。像父親和祖父,我和父親,都有那么點兒意思。祖父輕微中風之后,醫生說當心摔跤,可他閑不住。父親勸,他不聽。父親說:“你這是視死如歸啊。”
他們父子呵呵笑了。
院子里有一棵椿樹,是我少年時種下的,如今高大壯實。在我們那兒,椿樹是做棺木的材料。我問父親,給他做棺木夠不夠。他仰著頭目測—他是個木匠—然后說:“夠了。我的有了,給你留著吧。”
我們父子哈哈大笑。
那天打電話,母親說父親肚子痛,翻來覆去一夜。吃了止痛片,還是痛。我讓母親收拾一下,扶父親去鎮醫院檢查一下。醫生說是闌尾炎,要立刻切除。手術做得很順利,因為打了麻醉針,父親過了很久才醒來,還不能吃東西。醫生說做這樣的手術,病人要放個屁才能放心,說明腸子沒有粘住。
我和母親通電話,母親只是要我們放心。想著母親勞累了一天,我就沒有說放屁的事情。
可那天一直惦記著那一聲響動。
電話在深夜響起,是母親請醫生打過來的,只說了一句:“你屋老漢頭子放屁了!”我的心一下展開了,充滿喜悅。類似的事情,后來還發生了幾次,父親做手術,母親做手術,我們等著那一聲響。
父親一天天地康復。
有一天,他說花臉回來了。是后半夜回來的,聽見它叫,開了燈,它蹲在床前,一聲聲叫著,父親就一聲聲喚著。
那時,花臉離家三個多月了。
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我為什么一直問候花臉,那是我把它當成我,伴在他們的身邊,蹲在他們的膝下,給他們小小的歡喜。
他們有子有女,都不在身邊。那只叫花臉的貓,伴了他們許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