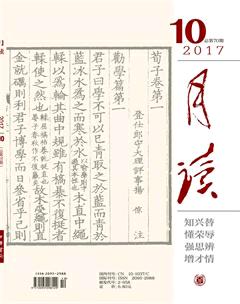秋爽來學(xué)
佚名
又到開學(xué)季,忽然想起前兩天看到的一則掌故,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jì)勝》中說:“京師小兒懶于嗜學(xué),嚴(yán)寒則歇冬,盛暑則歇夏,故學(xué)堂于立秋日大書‘秋爽來學(xué)。”這不和如今的孩子一樣么:一樣的寒暑假,一樣的秋季開學(xué),一樣的懶。雖然現(xiàn)在的開學(xué)日,已晚于立秋,但也仍是秋高氣爽的日子。所以這幾個字,真是看得人神清氣爽。只是不知孩子怎么想,放羊了一個暑假,按部就班的小夾板又戴上了。
放假還有更長的。陸游《觀村童戲溪上》里說到“三冬暫就儒生學(xué)”,自注“村人惟冬三月遣兒童入小學(xué)”。也就是說,除了冬閑,其他季節(jié)都不用上學(xué)。細(xì)想想,卻無法羨慕。應(yīng)該是因?yàn)榻?jīng)濟(jì)原因,不能全日制讀書吧。沒有參加科舉和做學(xué)問的壓力,自然不用學(xué)那么多,所以也只能一代代“千耦還從父老耕”。
至于《紅樓夢》里寶玉的上學(xué),在眾人口中,就像個笑話。賈政的反應(yīng)最為直白,當(dāng)眾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學(xué)兩個字,連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理。仔細(xì)站臟了我這地,靠臟了我的門!”全是語言暴力,一點(diǎn)也不關(guān)心和愛護(hù)下一代。更讓兒童心理學(xué)家顫抖的,是下面眾清客相公的那句話:“老世翁何必又如此。”一個“又”字,可見非止一次,由來已久。但在那個時代,這才是合格的父親形象。
賈政當(dāng)年的教育理念,也很成問題,看他要轉(zhuǎn)告(指示)校方的幾句話:“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jīng)》,也都是掩耳偷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xué)里太爺?shù)陌玻驼f我說了:什么《詩經(jīng)》古文,一概不用虛應(yīng)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氣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顯然他不太在乎素質(zhì)教育,應(yīng)試教育才是硬道理。但在當(dāng)時,這也是世事洞明之言。相比之下,我們?nèi)缃竦男戮幮W(xué)語文課本里,把古詩詞增加到了一百三十多首,真是了不起的進(jìn)步呢。
當(dāng)然賈政后來也改變了對寶玉的態(tài)度。到七十八回,已經(jīng)不再以高考(舉業(yè))相逼,因?yàn)槟赀~,“名利大灰,然起初天性也是個詩酒放誕之人,因在子侄輩中,少不得規(guī)以正路。近見寶玉雖不讀書,竟頗能解此,細(xì)評起來,也還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就思及祖宗們,各各亦皆如此,雖有深精舉業(yè)的,也不曾發(fā)跡過一個,看來此亦賈門之?dāng)?shù)。況母親溺愛”云云。
《紅樓夢》是一部關(guān)于成長的書,寶玉、黛玉、賈環(huán)、賈蘭都在成長,連賈政都在成長。
林妹妹對他上學(xué)的態(tài)度,可用一個“哂”字概括:“好!這一去,可定是要蟾宮折桂去了。我不能送你了。”又惦記著“你怎么不去辭辭你寶姐姐呢”,小兒女嬌俏之態(tài),不說也罷。
其實(shí)真正關(guān)愛他,內(nèi)心對他寄予厚望、眼巴巴指望他這一去就能“蟾宮折桂”的,還有兩個人,賈母和王夫人。可這一段的書里,什么也沒寫。只提一句,見了王夫人,辭了賈母。隔輩人的愛,都是單向的,而且永遠(yuǎn)無法抵達(dá)他內(nèi)心的最深處。沒辦法,人性如此。
寶玉的這趟上學(xué),在書中留下的標(biāo)志性事件就是鬧學(xué)堂,然后秦鐘夭逝,再然后這條線幾乎就斷了。直到六十六回,才由興兒總結(jié)道:“長了這么大,獨(dú)他沒有上過正經(jīng)學(xué)堂。”似乎也沒什么可遺憾的。起碼從前八十回我們可以知道,他長成了自己本來的樣子。寫一部《紅樓夢》,和做一名科舉達(dá)人,孰優(yōu)孰劣,誰知道呢。
有時想想,我們學(xué)了什么,學(xué)了多少,和自己最終會成為什么人,還是有關(guān)系的。所以,秋爽時節(jié),來學(xué)就好。
(選自《深圳商報》2017年9月7日。薦稿人:潘光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