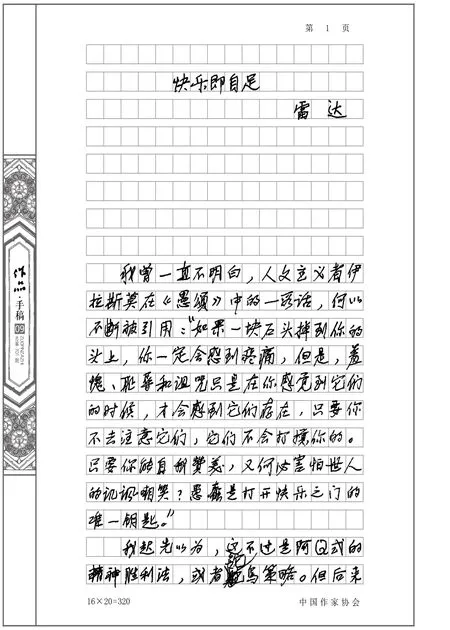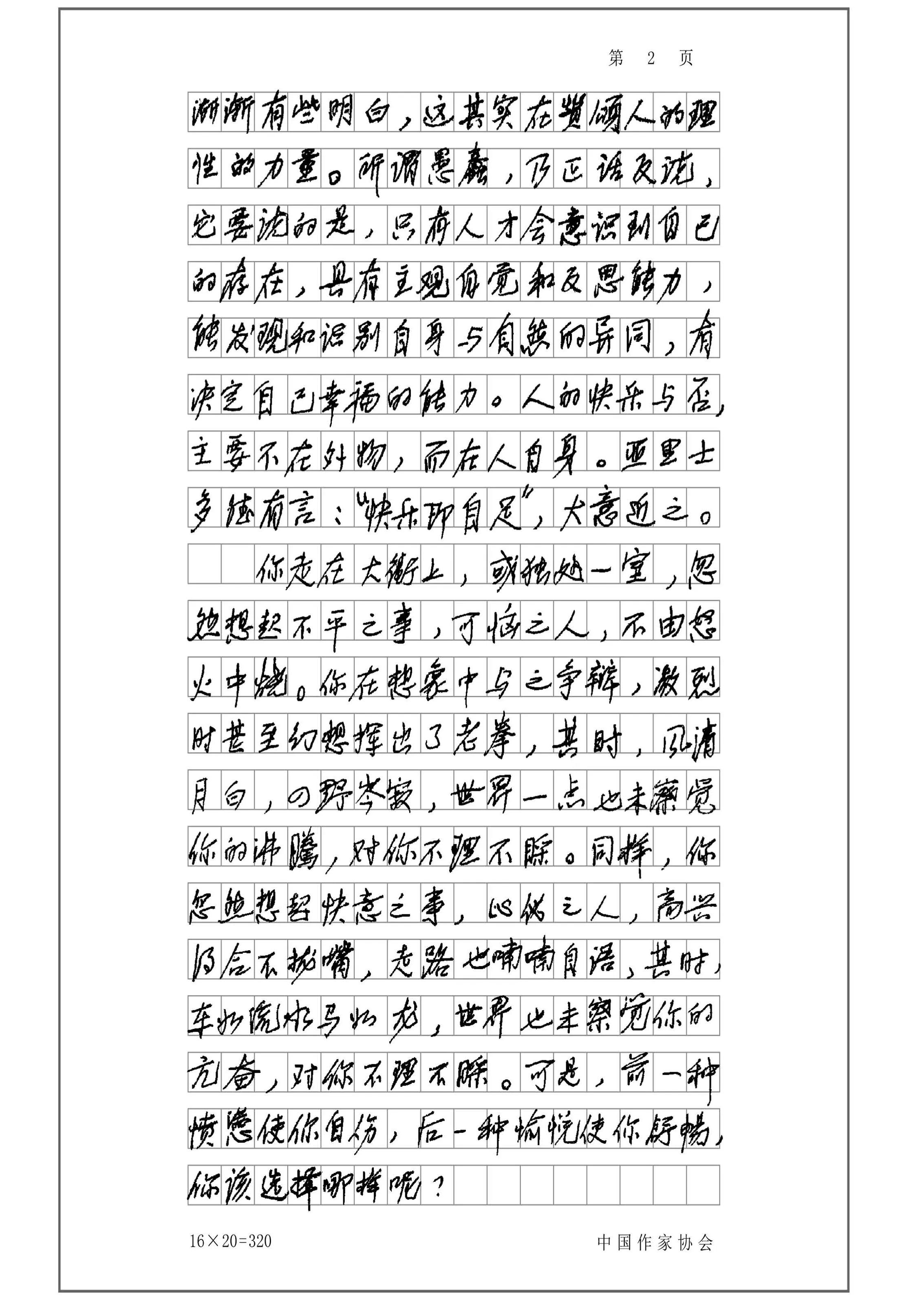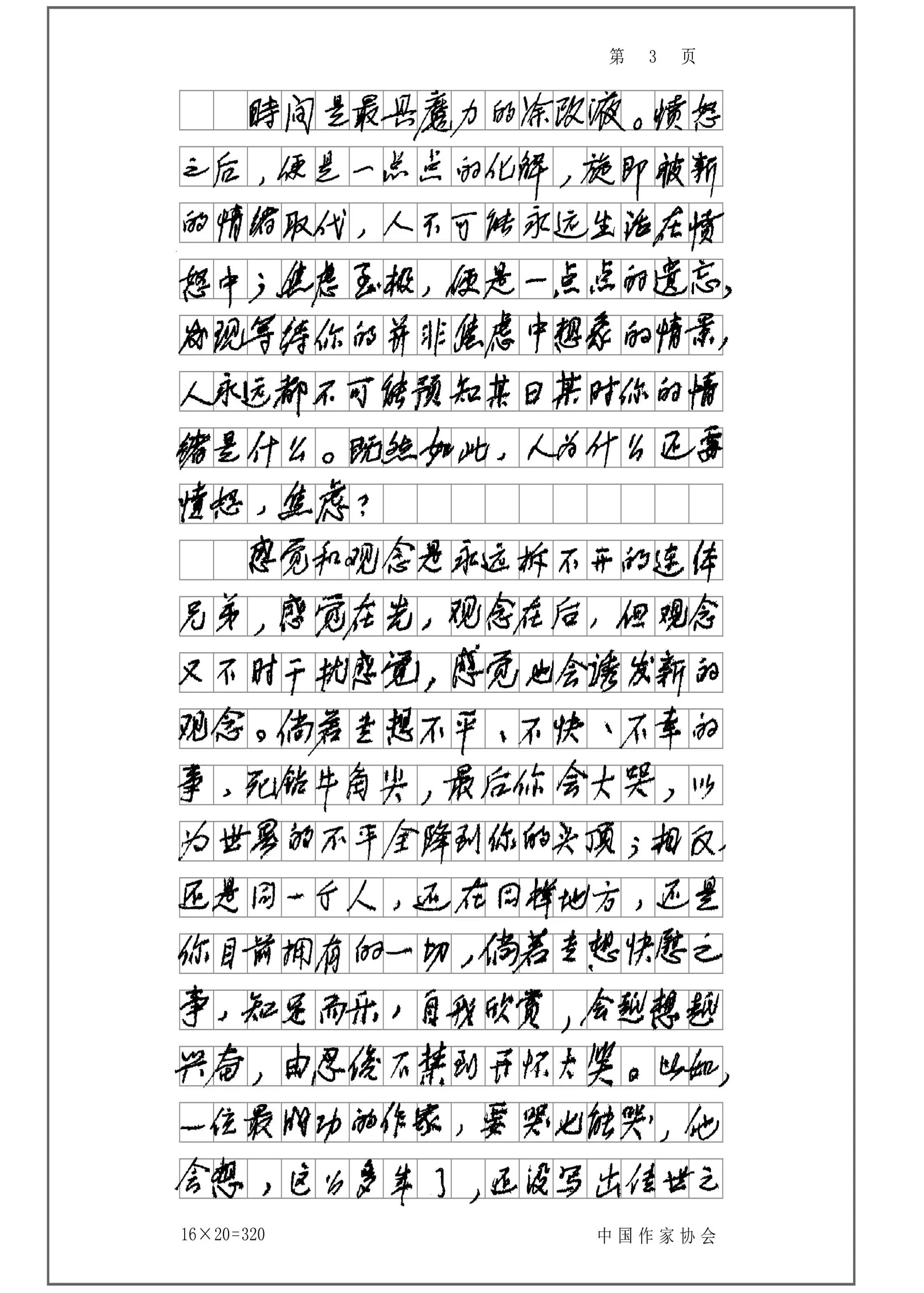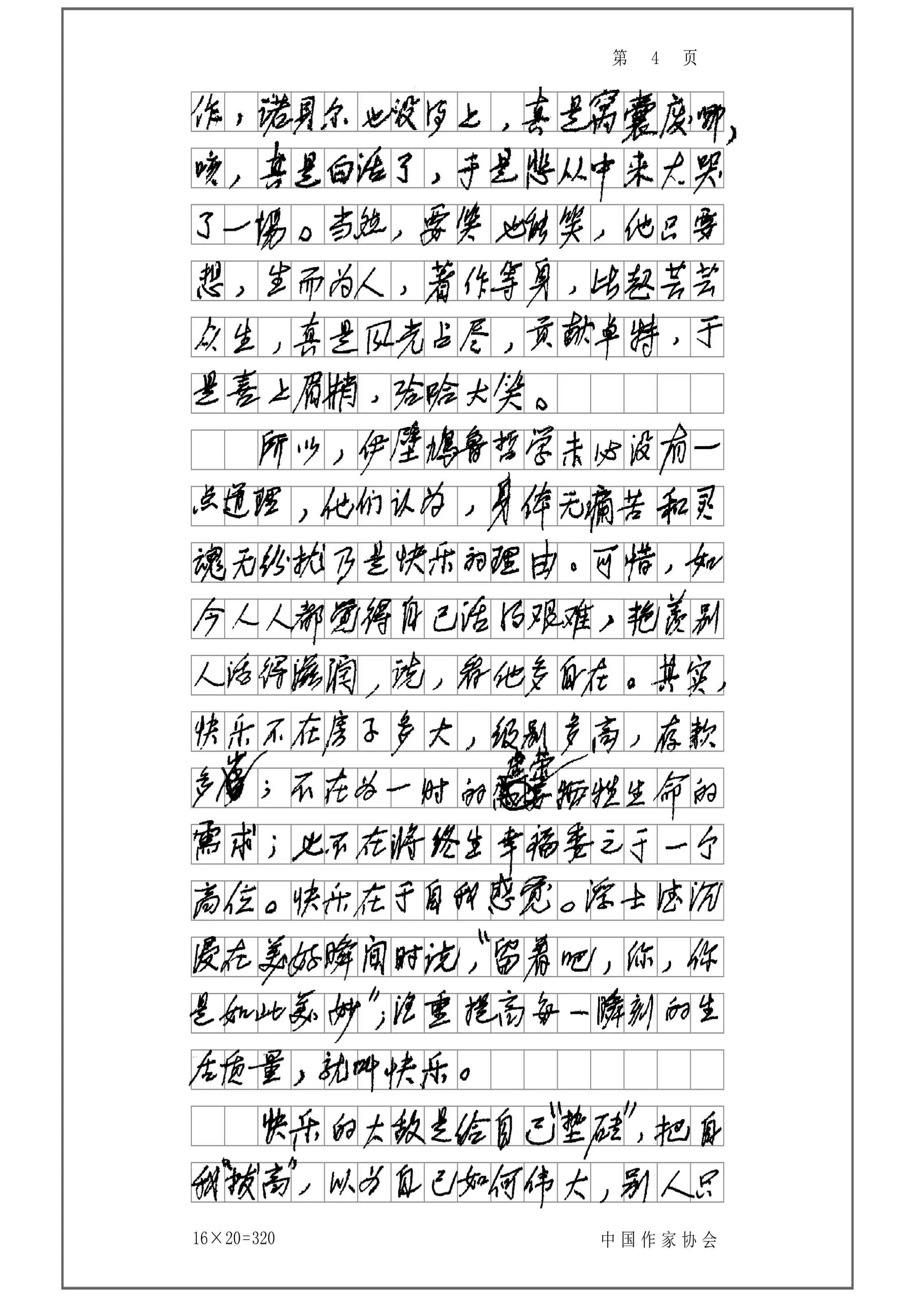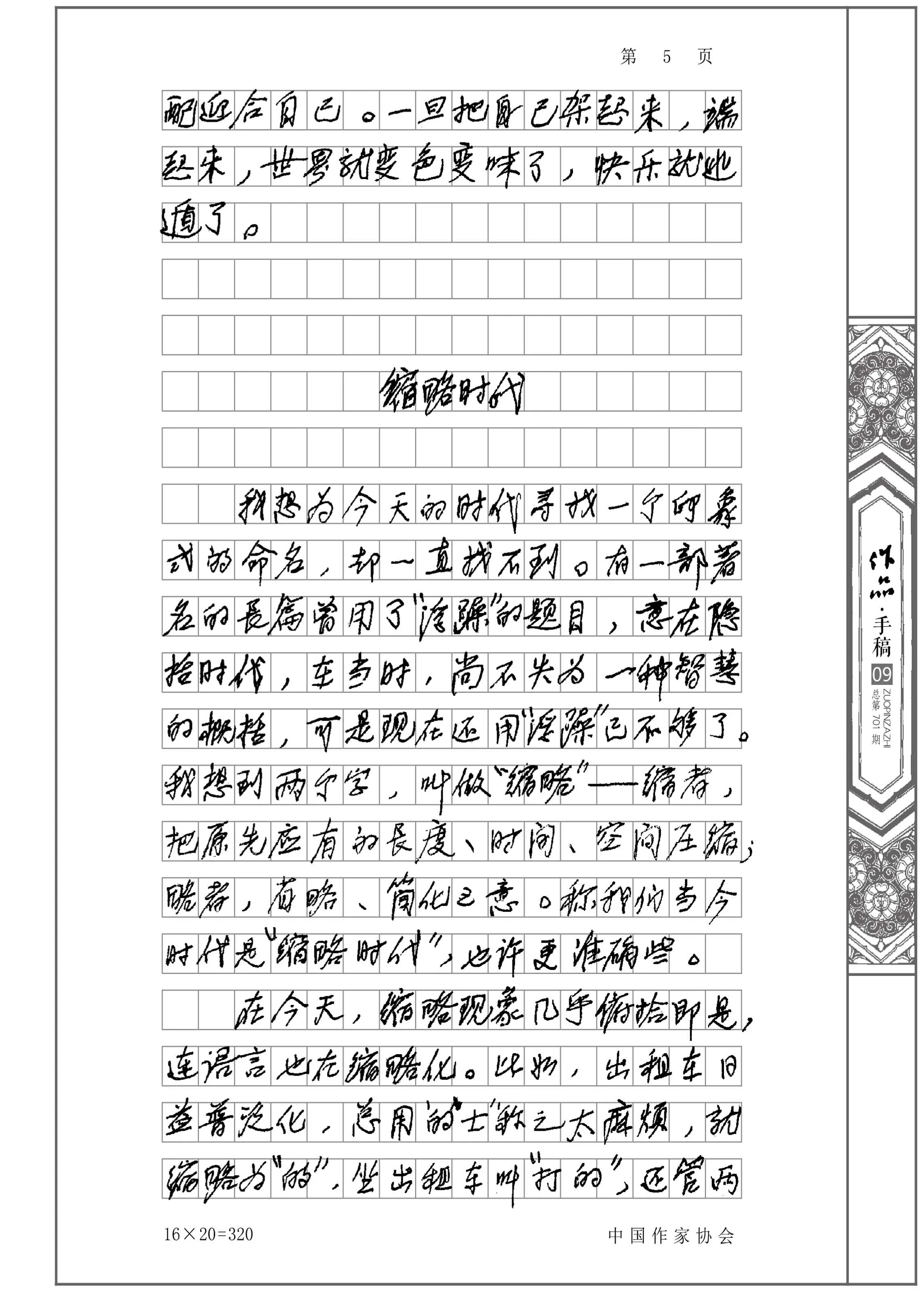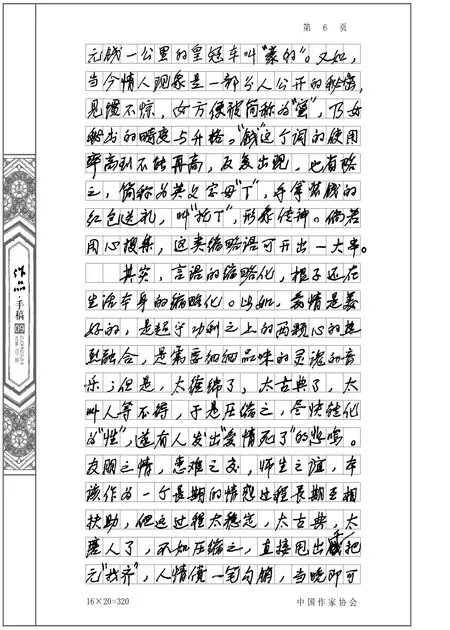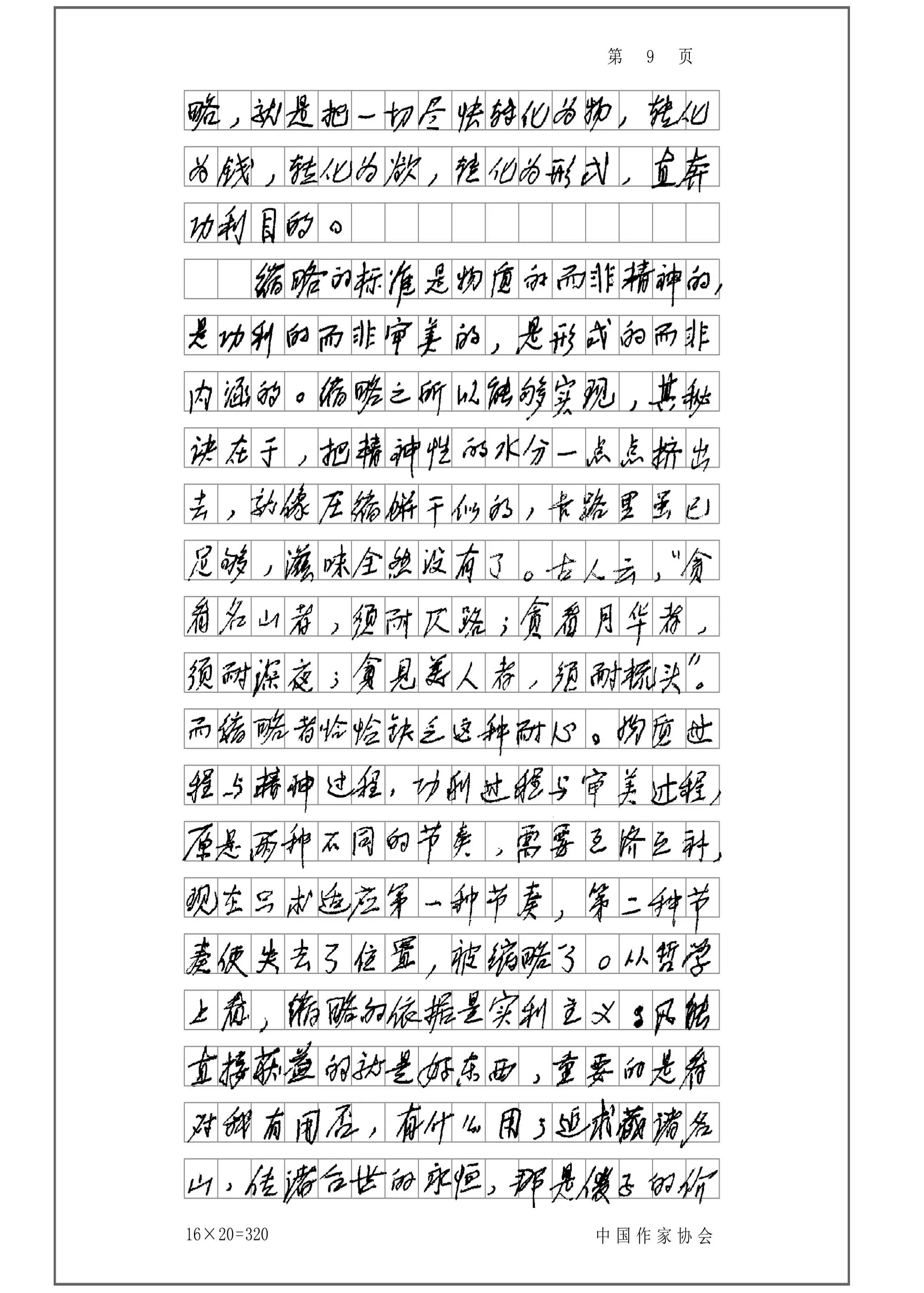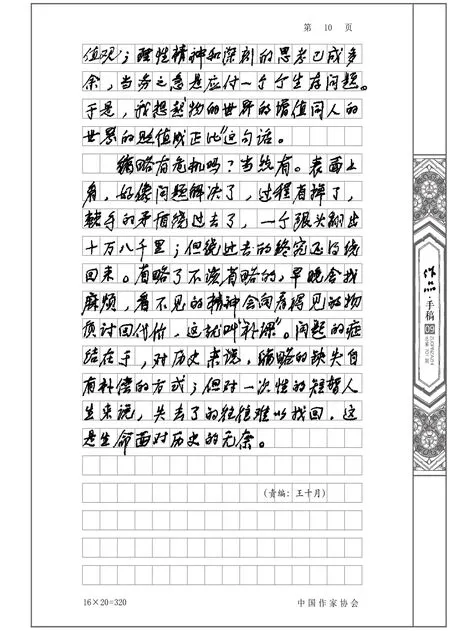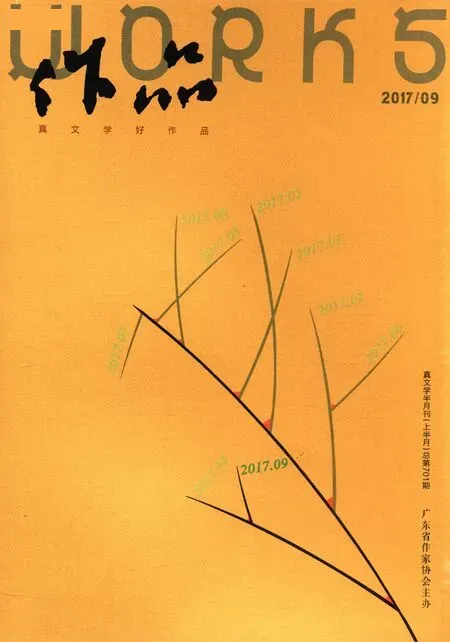90后文學新粵軍的兩駕馬車:路、索耳比較論
——90后小說觀察之三
文 /徐 威
文 /徐 威
徐 威
男,江西龍南人,1991年生,廣東省作協會員,中山大學中文系2015級博士研究生,現居惠州。在《作品》 《詩刊》 《中國詩歌》 《詩選刊》 《星星·詩歌理論》 《當代作家評論》 《當代文壇》 《創作與評論》等發表小說、詩歌、評論若干,著有詩集《夜行者》。
路魆:在臆想中言說
幻覺與臆想,原本就是毫無邏輯可言的。所以,在我看來,路魆筆下的幻覺中,發生了怎么樣的故事已經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路魆在作品中所構建的荒謬而有著強大隱喻的“獨立世界”——《拯救我的叔叔衛無》中神秘而詭異的監獄、《圓神》中的工廠、《林中的利馬》里隱藏在森林深處的別墅、《圍爐取冷》中孤島般的醫院、《竊聲》中的王家園小區……它們都自成一體、遠離人世。然而,我恰恰認為,這種遠離實質上正是一種隱晦的人世觀照——這些世界指向的正是我們所處的現代社會。比如,在孤島般的醫院中,“我”與其他醫生分區而居,難以相見,因為“區域是不能亂跨的,因為有人曾經試過亂跨區域,被革職,最后被人發現死于野外。恐怖的禁忌是我們心里長久以來的法度。”這實質上正是我們現代人孤獨、牢籠、隔離等精神狀況的一種隱喻。又如《圓神》中的工廠,“我創造的圓神工業,是一個現代化的地獄,那些無休止、無緣由的勞作,就是孟婆湯,只要動手勞作了,就是自我遺忘、自我贖罪。忘憂之地,藝術的天堂。”[3]所以,路魆筆下的世界,不是具象而是抽象的,不是物質的而是精神的。路魆在幻覺與臆想中書寫荒謬,在荒謬中袒露人性。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路魆的小說雖不呈現現實生活,卻同樣有著尖銳的批判力量。
現在我的小說的特殊性已經得到公認了。然而,如果有人直接問我:“你寫的究竟是什么具體的故事?你是怎么寫出來的?”面對這樣的問題,由于內心深恐產生誤會,我只能回答說:“不知道。”從通俗的意義上來說,我的確不知道。并且,我是一個有意地讓自己處于“不知道”的狀況中來寫作的人。由于信仰原始之力的偉大,我必須將其放在虔誠的、認為的蒙昧氛圍中去發揮,以使自身掙脫陳腐常規的羈絆,讓強大的理性化為無處不在的、暗示性的激勵和慫恿。[4]
二、索耳:隱晦與多重指向
索耳,本名何星輝,1992年出生于廣東湛江。索耳在高中時期就已開始創作,2013年以索耳為筆名開始發表作品,至今已在《作品》《山花》《長江文藝》《芙蓉》《青年作家》《當代小說》等刊發表中短篇小說近二十篇,其中《所有鯨魚都在海面以下》《南方偵探》還被《小說選刊》《中篇小說選刊》轉載。今年夏天,索耳從武漢大學畢業,獲得了比較文學碩士學位。
坦白說,閱讀并試圖解讀索耳的小說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比如,我在閱讀他最初發表的作品之時,心中就閃現出了許多的困惑與不解——《卡拉馬佐夫線》中,這個標題到底是何意、與小說文本有何聯系,至今我仍看不清楚、想不明白。這種隱晦特征,在他之后的小說創作中也一直延續著。我們很難如同以臆想、幻覺、死亡等為關鍵詞歸納路魆的寫作主題一樣,用三兩個關鍵詞匯去總結索耳的小說創作。顯然,這是他有意為之。在創作談《我所追求的是異質之美和審美共存》中,索耳說道:“我希望自己的小說有一種無可定形的狀態,同時和主流文學審美保持距離”、“ 我覺得多一點不確定性不是壞事”[8]。這樣一種文學觀,使得索耳的小說文本具有了多種解讀的可能性。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無法確認,哪一種解讀才是索耳創作的真正意圖。甚至于,我還暗自懷疑,有些作品索耳自己本人也并無法三言兩語說清楚他到底想要表達什么。
縱觀索耳的小說作品,可以發現一條較為清晰的分界線——《卡拉馬佐夫線》《鑄刀師的遺產》《調音師的依米醬奈》等是其練筆之作,初見索耳在小說敘事上的嘗試,然而文本的力量始終有限;《蜂港之午》《殺觀眾》中其筆法逐漸走向圓潤,可看作其過渡期;至《前排的幽靈》《所有鯨魚都在海面以下》《南方偵探》《在紅蟹涌的下半晝》,小說文本的內容與結構愈加協調,相互支撐,使得文字隱含的力量愈加強大。與此同時,《顯像》《白琴樹苑》則顯示出索耳在敘事上的“異質”與“新變”。
《前排的幽靈》帶有一種神秘的氣息,其指向的是記憶、勇氣與救贖這樣深刻的文學主題。在老詹多次的夢境與殷姑對其獨特的拯救治療中,老詹記憶深處的恐懼被一點一點地挖掘出來。在那個瘋狂而殘酷的特殊年代,站在前排眼睜睜看著父親被打死的一幕,對老詹的一生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之后,老詹再也無法站在前排,看電影始終選擇坐在最后幾排,看球賽也認為坐在前排有生命危險。在小說中,老詹的朋友瓦沈建是這一記憶的挖掘者,他或是暗示(如假裝無意地告知老詹“我”的父親是被人打死的,這令老詹沉默數秒,最終仍不敢面對,只能轉移話題),或者直言(直接告知老詹:“你是幽靈”,而他的任務就是拯救正在消亡的幽靈),或是震喝(“你不喜歡坐在前面,是因為對前排的位置有一種恐懼感,你害怕坐在前排,因為你以前坐在上面,你曾經是最前排的觀眾。你看到了一些讓你恐懼的東西……你親眼看到了你父親活活被毆打的場面”)。現在與過往、真實與夢境的相互交錯,使得小說在結構與內容上相互支撐,生成了一股巨大的張力。
如果說在《前排的幽靈》中,我們還能看到索耳在敘事結構與敘事意圖上有意為之的痕跡的話,那么,在《在紅蟹涌的下半晝》里,這種隱晦與多重指向則潛藏于流暢自然的日常書寫中。這篇小說的情節極為簡單——一對年輕夫婦,在電視上看到紅蟹涌的風光廣告,并于第二日前往紅蟹涌度假。這是極為流暢的日常生活書寫。然而,小說卻飽含隱喻色彩,直指現代人的生育焦慮。兩人在生小孩問題上的爭執、“我”所夢見的蟹腳雨、把寵物貓寄養在朋友處、打撈不到海鮮卻每日堅持出海的漁民、倒塌的東岸海灣大橋、妻子的對煙癮的壓制與放縱、一言不發的古怪導游被我們推下海、島上漫天遍地的紅蟹令我們落荒而逃、到家之后再去接回貓(“我們唯一的孩子”)……這些日常化的現實與不合邏輯的超現實雜糅在一起,最終聚集在一點:生育焦慮。一方面,是父母在催生,妻子也開始動搖,想要生小孩卻又含糊其辭;另一方面,是將寵物貓當成唯一孩子的我們對于不生育生活的一種滿足。這對年輕夫婦的矛盾與困惑、孤獨與恐懼,在簡單的日常敘事中若隱若現,令人印象深刻。
在《顯像》與《白琴樹苑》中,索耳的敘事探索值得一提。在《顯像》中,索耳將《照相館》《多少》《他山之石》《酷刑》《世上最好吃》《乙酸異丙酯》《審片人》《陌生的游戲》《上將和馬》《一次刺剪》十個毫無關聯的獨立故事,組合成一篇小說。在《顯像》這一大標題之下,試圖呈現出人的存在之荒謬與艱難。《白琴樹苑》亦是多個故事相組合的敘事方式,只不過,故事與故事之間還略有關聯。小說每一節的敘事對象與敘事口吻都在變幻,索耳試圖在偶然之中勾勒出那無形的必然命運來。這種寫法,在《蜂港之午》中索耳曾使用過。
三、并駕齊驅的“兩輛馬車”
然而,這兩個90后作家的敘事風格與美學特征又是如此相異。路魆的小說是反理性、反經驗、反邏輯的,而索耳的小說則是理性、經驗與邏輯的;路魆的小說作品彌漫著一股陰冷之氣,時常令人頭皮發麻,索耳的小說則如冒頭的冰山一角,在看似普通中隱藏著巨大的力量;路魆的小說時常構建一片獨立于現實的荒謬世界,而索爾的小說則緊緊扎根于我們的現實世界;路魆的小說源自于個體的感性體驗,而索耳的創作則遵循著一套理性而學術的文學觀念,這些觀念來自于中外數十個國家的作家作品。
最后,我需要說明的是——從現階段的90后小說創作來看,路魆與索耳可謂是廣東本土90后作家中并駕齊驅的“兩駕馬車”。如今,這兩駕馬車都已經上路,朝氣蓬勃,銳意無限。當然,這并不是一條容易通行的道路,他們可能會遇到荊棘、坑洼甚至懸崖。然而,我始終希望,他們能夠走得更遠。
愿他們繼續奔馳下去。
注釋:
[1] 路魆:《拯救我的叔叔衛無》 《青年作家》,2016年第9期。
[2]路魆:《幻痛的射擊者》 《文藝報》,2017年5月3日。
[3]路魆:《圓神》 《廣州文藝》,2017年第7期。
[4]殘雪:《一種特殊的小說》,見《殘雪文學觀》,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頁。
[5]路魆:《幻痛的射擊者》 《文藝報》,2017年5月3日。
[6]路魆:《幻痛的射擊者》 《文藝報》,2017年5月3日。
[7]路魆:《死與蜜》 《天涯》,2016年第1期。
[8]索耳:《我所追求的是異質之美和審美共存》 《文藝報》,2017年7月3日。
(責編:周朝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