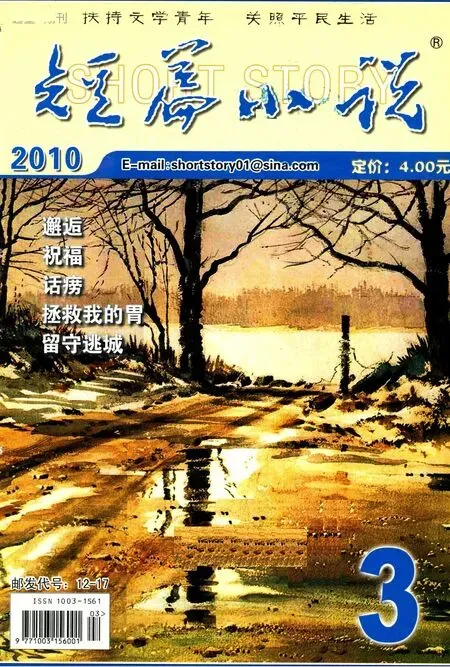他死得太遲了
◎小 米
他死得太遲了
◎小 米
老呂,四川人,解放初落戶本村,跟一個寡婦攢家〔中年或老年才在一起過日子的半路夫妻〕。
跟老呂攢家的這個寡婦,跟我家是“伙內”而不是“親房”,關系比較遠。論起來,她是我的同輩,但因為她的女兒嫁給了本村我的一個“親房”,她的女婿都跟我爺爺是同輩,我就不叫她什么了,沒辦法叫。她的女兒,小名俊女子——到現在,她都老了,是當奶奶的人了,人們還叫她俊女子。但是,我這樣的小輩不能叫,我得叫四婆,也就是四奶奶。四奶奶偶爾去一趟娘家,時間一般都很短,幾分鐘就走了。四爺從來不到岳母家里去。他們的長子,小名叫做大牛,從小就跟外婆一起生活。四爺對這個名義上的兒子不親,大牛也不把四爺叫爸爸,叫了四爺也不答應。四奶奶倒是對大牛很好,爹不親娘親,兒子畢竟是娘身上掉下來的肉嘛。
為什么說大牛是四爺“名義上的兒子”呢?因為四爺跟俊女子結婚的時候,大牛已經有了,這都是我聽大人們說閑話聽來的。大牛跟我同歲,還是小學同學,他小學沒有畢業就不念書了,念不會。許多農村孩子跟他一樣,也沒有人計較。“念那么多書干啥?只要認得錢就行了。”這是當時許多家長的觀點,當然這不是老呂的觀點。老呂是見過世面的人,他知道讀書的好處,不像村里許多人,活了一輩子,連縣城都沒有去過。但大牛不念書,他不愿意念,老呂拿他也沒有什么好辦法,只有由他去。
老呂的女人跟我奶奶年齡差不多,老呂比她好像還要略大一些。老呂的女人還有一個兒子,而且只有這么一個兒子,還是長子。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卻去了很遠的一個村里,給人當了上門女婿,從來不回本村。即使過年什么的,也只派他的兒子過來一天兩天,平時也難得見到他,我幾乎不認識她的這個兒子。他是對老呂有成見。
這一子一女,都不是跟老呂生的,他們都不跟老呂姓,他們也從來不把老呂叫爸爸。據說,老呂到這個家庭的時候,他們都已經十來歲了。
老呂沒有自己的骨肉。
老呂跟她的女人,還有大牛,他們三口人,單另過。
因為“呂”和“驢”諧音,人送老呂一個外號:“老驢”。
這是有原因的。
老呂剛到這個家的時候,跟“兒子”睡,他的女人跟俊女子睡。家里只有兩個炕,兒女也大了,“叫兄妹一起睡,不好。”這是老呂說的,女人認為他說得有道理,照辦了。老呂正當壯年,自然沒有不親近女人的道理。他跟“兒子”睡到半夜,就起來,假裝解手,摸到另一間屋里的另一個炕上去,做他想要做的事。做完了,又悄悄地回到他跟“兒子”睡的炕上。有時候,老呂做完了,并不急著走。天上沒有月亮的晚上,屋里也就很黑,黑得什么也看不見。老呂的手忍不住就到了他的女人發現不了的地方,到了他不應該到達的地方。
炕上還有一個人呢,是俊女子。俊女子已經懂些事情了,盡管不是很懂,她早已讓老呂和母親驚醒了,只是,在黑暗中,她不說,不動,有些好奇,她閉著眼睛仔細地聽著,她不想聽也得聽。
老呂的手,估計女人已經睡著了,就假裝不經意地,那么隨便一伸,一擱,就到了俊女子的胸脯上。那兒,剛剛有了凸起的感覺,他覺得挺不錯,他讓手停了很久。俊女子給嚇住了,她動也不敢動,連大氣都不敢出,心里跳得咚咚直響。老呂的手沒有遇到拒絕,更沒有他預料中的反抗,反而得到了鼓勵似的,就輕輕地動作著。
又過了許多夜。
情況還是一樣。沒有拒絕也沒有反抗,老呂的手就更前進了一步,他讓它往下走,一直到達俊女子的私處。俊女子自然不是想讓他摸,她只是害怕驚動了母親。她怕母親發覺了,反而說不清。但她覺得這也不是個辦法。
又過了一段時間。
有一天,吃完了晚飯,俊女子悄悄地對母親說:“媽,今天晚上,我想去跟玉英說個事情,這幾天天又太黑,就不回來睡了,我跟玉英睡。”玉英是俊女子的女伴,兩人從小就特別要好,玉英又是一個人睡,俊女子曾跟她睡了無數個晚上,一點也不格外。她的母親想也沒想就答應了俊女子。
一連幾天,俊女子都是這樣。
老呂沒有說什么,他并不著急。心急吃不了熱豆腐,老呂想,再說了,俊女子畢竟還是個孩子,沒有成人呢。
女人急了。
這天,吃完了晚飯,俊女子又要走,做母親的說話了,她說:“家里留不住你了?你是恨你爸爸,還是咋的?你倒是說說!”
俊女子能說什么呢。她什么也不好說,沒法說。
她站著,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那就別去了!”做母親的最后說。
俊女子就沒有去。
老呂隔三差五地,還摸到她們睡的炕上去,他跟女人做事情的聲響更大了,他就是要驚醒俊女子,他故意要讓俊女子聽到,他要讓她知道他們在做著什么,但他不動俊女子了,一指頭也不動了。老呂想,先穩住她再說。他還要讓俊女子覺得難受,他就是這么做的。
這真是一個惡心人的人。
老呂不對她動手動腳了,俊女子反而放下心來,也就再也不提去跟玉英睡的話頭了。
這樣過了兩年多。
俊女子小時候就長得俊,很好看,也讓人耐看,愛看。她的臉白白凈凈,沒有一粒雀斑,下巴尖尖的,是人們常說的那種瓜子臉;她的眉毛又細又彎,是人們常說的那種柳葉眉;她的眼睛很大,又大又黑又亮,顯得特別有靈氣;她的頭發烏黑發亮,兩根頑皮的長辮子甩到脊背上,又吱溜一下,跑到胸前來了;她的手指頭白里透紅,纖細、均勻、修長,跟蔥一樣。俊女子很少穿新衣服。衣服雖然是舊的,而且有補丁,但是干凈,整潔,沒有污漬也從來不粘塵土。鄉下的孩子,一年能穿上一件新衣服的,就很不錯了。
自從老呂到了她家,俊女子年年都能穿上一整套新衣服。有花布的上衣,藍布的褲子,有平絨面子的新布鞋——這已經很高級了。買布的錢是老呂弄來的,衣服是她母親縫的,鞋也是她母親做的。俊女子的母親年年都要給家里人每人做一雙新布鞋。新衣服,就不一定人人都有份。老呂自己也沒有。他的手頭還沒有那么寬展。
俊女子給人的,從來都是賞心悅目的感覺。
俊女子是一個讓人愉快的人。沒有多余的話,不亂說,不大喊大叫,不撒潑。
俊女子慢慢地,長成一個小女人了。
俊女子懷孕了。
肚子都大了,瞞是瞞不住了。
村里人都在背后嘰嘰喳喳地議論,都在替俊女子惋惜——“一個這么好的姑娘,唉!”
母親問她,不說。母親打她,還是不說。在母親面前,俊女子成了啞巴。
母親背著俊女子,去問玉英。玉英也說不知道。
老呂不問俊女子,不打俊女子。他仿佛不知道,不關心,他的眼睛好像是瞎的,什么也看不見。他對俊女子很客氣——他一直對俊女子很客氣。老呂似乎事不關己——俊女子又不是他親生的,用不著他關心。他給人們的印象就是這樣。
四爺年輕的時候有點渾小子的味道,嗓音大,聽了可笑不可笑的事情,他都哈哈大笑。這是個沒有什么心計、什么粗話丑話都敢說的人,他是個典型的二不楞——楞頭青。所以二十好幾了,還說不上個媳婦,沒有人愿意把女兒嫁給他。
有人來給四爺說俊女子。是俊女子的母親托付那人來的。四爺不愿意。“我可不想要一個帶著包袱的女人!”四爺說。
“你也別臭美了。不帶個包袱,人家能看上你?”
那人臨走對四爺說:“想一想吧。”
又過了兩個月,那人又來問四爺,說是等不住了,不行就算了,人家也好另外想辦法。
四爺低頭尋思了一會兒,然后才跺了跺腳,抬起頭來,惡聲惡氣地對那人說:“就是一泡屎,我也把它吃了!”
四爺有個條件,他不要俊女子肚子里的孩子。“我可以養活到兩歲,斷奶了,還給他們,——我不要有娘無老子的娃。”
四爺終究還是答應了。
“這倒不是個問題,讓老呂他們把娃娃養大就是了。”那人說。
臨走的時候,那人還在跟四爺嘮叨:“哪有這么好的事,白撿一個媳婦。”
四爺發火了:“你再說,我就不干了!”
那人趕緊賠著笑臉說:“你能!你能!你是我的爺,我惹不起你,我馬上就走!”
那人說得一點也不錯。
這個媳婦,是跟白撿的一樣。
僅僅過了幾天。
幾天之后,四爺就跟俊女子結了婚。結婚的時候,也沒有辦酒席,老呂一家人到四爺家里吃了一頓米飯,是晚飯。吃飯的時候,誰都沒有說什么,飯也吃得別扭,匆匆忙忙地糊弄飽了肚子,留下俊女子,就都走了。
在生產隊里,老呂只怕一個人。這個人是隊長。
生產隊長的權很大,好處也很多。生產隊長,由大隊書記指派,生產隊的干部,由生產隊長指派,社員大會上一宣布就行了。生產隊的干部,除了隊長,還有婦女主任、貧協主任、會計、記工員等,還有民兵排長——民兵排長歸大隊民兵連長管,也算是生產隊的干部。隊長可以叫記工員記工分,誰一天十二分 (壯勞力、全勞力)、誰六分(半勞力),這個基本上是固定的;老弱病殘、婦女、少年(十四五歲的),干一天活,由他說了算。年終,分糧食的時候,口糧是一份,用工分計算出來的糧食;還有一份,這也是最主要的一份,隊長還可以叫會計多給誰算上幾百分工分,可以叫保管員給誰一點糧食。這些當然是私下里說。誰也不敢不聽他隊長的話。誰要是敢不聽,隊長就開一個社員會,免了他,隊長還能夠另外指派一個人干。隊長沒有免過誰的職務,但他有這個權力。
當保管員的老呂,還能不怕隊長嗎?
老呂在隊長跟前,真的唯命是從。這是一個奸猾的人。
老呂一直是生產隊的保管員。
保管員得六親不認,因為他直接管著生產隊的糧食和錢物,眼不生的人,手不緊的人,看不好這個大家。老呂跟村里人關系都不怎么好,他又不怎么跟人拉關系、套近乎。這個村子里的人,都姓一個姓——李,生產隊里,還有一個比較小的村子,只有七八戶人,住在河對面,他們都姓王,相距也就七八十米的樣子。這兩個姓的人,過來過去都算是親戚,他們排擠外姓人。讓姓王的或姓李的當保管員,隊長都不放心。老呂做保管員,的確最合適不過了。他真是撿了個大便宜。
倉庫的門是用一寸厚的松木板做的,倉庫的門栓是鐵匠爐里打出來的,倉庫的鎖是村里最大的,比拳頭還要大。誰也別想偷偷地進入倉庫。
門鎖再怎么好,再怎么結實,再怎么牢固,它也鎖不住老呂。鑰匙在他的屁股上吊著,老呂想什么時候進去,就什么時候進去。
老呂有個心愿,也可以說,是他的人生目標,他對誰也沒有說。他不敢說。
到底是什么見不得人的目標呢?
——他想把村里所有的女人,一個一個,都弄到手!
這當然不是因為她跟女人有仇,完全不是——恰恰相反,他愛她們。老呂認為,人的一輩子,如果不盡可能地多弄幾個女人,就算是白活了。
按理說,老呂喜歡女人,并沒有錯,是他做錯了。
愛,并不一定占有身體。
這是一個喜歡走極端的人。如果按他這樣的目標來評價他的一生,他就是一個很差的、不及格的人。
到手的女人,當然也不少。絕對不止一個兩個。
俊女子沒有結婚的時候,有那么幾次,到倉庫里去找老呂,叫開了門,在里面的,除了老呂,就有別的女人。
把老呂叫老驢的,不是別人,也是俊女子。俊女子懷了孕,就暗地里叫他是老驢了。有一回俊女子在玉英面前說漏了嘴,弄得玉英也張大了嘴巴。“你怎么能這樣說大人呢?”玉英說。
俊女子索性說:“一點也不錯,他就是條老驢!老叫驢!”
老驢的外號,就這么傳開了。
俊女子再沒有把老呂叫過爸爸。見面的時候,她把老呂什么也不叫。
這個被自己的“女兒”稱做老驢的人,活了將近八十歲,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終于死了。按照我們鄉下人的幽默,他是“到黃土坪上曬熱頭(太陽)去了。”
村里人死了,都埋在黃土坪一側的老祖墳里,那兒很向陽,光照特別充足。
在農村,他也算是高壽。
他死得太遲了。
這個世界上,無論什么人,遲早都是要死的!
責任編輯/何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