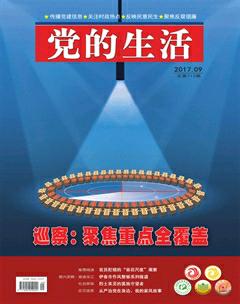官員犯錯的“容忍尺度”觀察
錢昊平 張鑫曄
近幾年,越來越多的地方開始容忍官員犯“一定的錯誤”。
例如,江蘇省提出,各級干部今后在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時,只要是主動擔責、積極作為,如果出現一定失誤和錯誤,將能被容錯免責。這讓江蘇的公務員吃了一顆“定心丸”。
根據2017年6月江蘇省委制定的《關于建立容錯糾錯機制 激勵干部改革創新擔當作為的實施意見(試行)》,共有八種情形可以被免責,包括在處置突發事件中臨機決斷、落實管黨治黨主體責任時出現失誤等。
江蘇的做法是中央精神在地方的又一次落地生根。黨的十八大之后,中央多次強調“容錯”,2016年國務院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出“健全激勵機制和容錯糾錯機制,給干事者鼓勁,為擔當者撐腰”。今年7月19日召開的中央深改組第三十七次會議再次指出,建立健全改革容錯糾錯機制。
據《南方周末》記者不完全統計,2015年以來,已有河北、浙江、四川、云南、上海、山東等十多個省份探索建立干部容錯機制,一些干部因此而“躲”過了本來要受到的處分。
在探索容錯糾錯的實踐中,浙江走在前列。2014年,溫州在省內率先制定容錯機制后,浙江省委于2015年出臺了《關于激勵干部干事創業治理為官不為若干意見》。此后,杭州、金華、臺州、紹興等市也制定了相應的制度。
寧波市下轄的象山縣自2015年推出容錯免責機制后,已有十多名鄉鎮(街道)和縣直部門的主要負責人被免予問責。現任象山縣丹西街道辦事處黨工委書記的史欣榮就是一個“幸運兒”——本來對他的問責程序已經啟動,最后他不僅沒有被問責,還順利地被提拔了。
史欣榮的“麻煩”與浙江省在2013年啟動的“三改一拆”工作有關。“三改一拆”,是指在全省開展舊住宅區、舊廠區、城中村改造和拆除違法建筑,計劃用三年時間完成,2015年是最后一年。為保證進度,象山縣一開始就宣告,將對“三改一拆”工作進度遲緩、排名靠后的鄉鎮街道負責人啟動問責調查。
2015年1月到9月,由于丹西街道的進度排名位于全縣末兩位,縣紀委啟動了對時任街道辦主任史欣榮的調查。被談過話的史欣榮當時覺得委屈,因為丹西街道不僅有“三改一拆”任務,還要承擔19個縣重點工程,任務較重,為避免“多線作戰”,史欣榮對推進方案做出了調整——上半年集中精力做拆違對象的思想動員工作,下半年再“集中戰斗”,從而導致上半年的進度顯得緩慢。
忐忑幾天后,縣紀委的一個免責電話讓史欣榮頓時感到釋然。象山縣紀委負責人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史欣榮所供職的丹西街道拆違量較大,工作難度也較大,必須考慮到社會穩定,還要兼顧縣里其他重點工程的推進,進度落后不是由于領導主觀上工作推諉或工作安排失當造成的。根據象山縣的免責規定,最終對史欣榮做出了不問責的決定。
2015年10月,丹西街道完成了全部拆違任務,史欣榮本人也被評為寧波市2015年“三改一拆”工作先進個人,并在2016年升任街道黨工委書記。
史欣榮最終能被免責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主觀故意”,算上這條,象山縣的免責條款共有五條,此外還包括“為了改革而大膽探索、先行先試過程中出現失誤或者錯誤行動”等情形。
在象山縣出臺容錯機制之前,該縣已經出臺了機關工作人員問責辦法,“免責與問責并舉”是大多數已出臺容錯機制地區的通行做法。與象山縣同屬寧波市的奉化、江北、海曙等區,在出臺容錯機制之前已經對干部“能上能下”進行了一定的探索,并制定了相應的問責制度。
寧波市奉化區委組織部相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該區從2012年開始推行“干部能上能下”,到2016年已有20名不適宜擔任現職的干部被調整,其中包括5名市管干部。“為了體現有獎有罰,我們又出臺了容錯機制。”該人士說,這與推行“干部能上能下”是相呼應的。
在省一級,容錯機制大多也與問責處理機制并存。江西、廣東、內蒙古等地都是分別出臺了兩個文件;北京則是在“市委實施《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辦法”中直接列出了“容錯機制”條款;山西在2016年實行“三項機制”并舉,先后建立了鼓勵激勵機制、容錯糾錯機制、能上能下機制,容錯糾錯干部156人,同時也以“能下”方式調整干部489人。
各地的“容錯”工作一般都由紀委和組織部負責執行,但各地下發這一文件的機構并不一致,江蘇、浙江、山西、陜西都是以省委辦公廳的名義印發,內蒙古、四川是由黨委、政府辦公廳聯合印發,江西則由省紀委和省委組織部聯合印發。
“不在于文件是由哪個部門發出的。”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學教研室主任王占陽說,關鍵是有了上面的精神之后,下面的干部是不是就真的敢放手去干事。
王占陽說,干部的畏難情緒不克服,即便上面說容錯了,下邊也不敢動。而據《瞭望》周刊報道,山西省委組織部2015年上半年在全省11個地市進行了一次干部狀態調研,樣本近兩萬人。結果顯示,呂梁市有60.2%的干部表示“不敢作為,內心沒有安全感”;而在太原、長治等地,有這種心態的干部都超過50%。山西11個市地都有一定比例的干部希望建立容錯機制。
此后,山西省長治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郭康峰在接受《人民日報》記者采訪時就表示,不能正確處理、對待改革中的失誤,會影響干部干事創業、改革創新的熱情,或導致干部瞎干、蠻干等亂作為。
在各級干部中,基層干部對容錯的期待顯得更為迫切。寧波市江北區委組織部相關負責人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建立容錯糾錯機制,是當前干部工作中急需破解的重點難點問題。
以江北區為例,該區啟動了“為官不為”整治行動,但在實踐中,一些干部“不能為”也有一些客觀原因,首先是權責不對稱。鄉鎮作為基層政權,是黨委、政府工作落實的“最后一公里”,但他們缺少資金和執法、審批的權限及資源,導致不少重要工作“不能為”。例如在推進“兩路兩側”環境整改工作時,鐵路部門有時就不配合,甚至基層人員主動去幫他們清理都被拒絕。endprint
體制機制的不順暢,也經常導致基層干部的“不能為”。寧波市江北區委組織部相關負責人舉例說,目前的工作體制是“塊抓條保”,很多重點項目是卡在規劃、國土、環保等條線上,經常將大量精力耗在與這些部門的工作協調上,因久拖不決,往往演變成歷史遺留問題。該負責人認為,對于這類“不為”現象,如果干部已經竭盡所能,就應該有科學的容錯糾錯機制,以免誤傷干部的積極性。
基層有強烈呼聲,高層也意識到了給干部“松綁”的必要性。2016年1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研討班上講話時指出,要把嚴格管理干部和熱情關心干部結合起來,并提出了日后成為各地在制定容錯機制時都遵循的“三個區分開來”。
“三個區分開來”,即要把干部在推進改革中因缺乏經驗、先行先試出現的失誤和錯誤,同明知故犯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把上級尚無明確限制的探索性試驗中的失誤和錯誤,同上級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把為推動發展的無意過失,同為謀取私利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
從各地的容錯免責辦法來看,在“三個區分開來”的總體框架下,具體做法大同小異,大多強調了不是明知故犯、經過集體民主決策、法律法規沒有明令禁止、符合上級政策精神等具體容錯標準。
此外,沒有獲取私利也是可以被容錯免責的一個重要前提。浙江省紹興市鏡湖新區靈芝鎮黨委書記陳繼瑞就是一個因此被免責的干部。
靈芝鎮水產村有片叫上下官渡的水域,共1790畝,多年來被水產養殖戶們分散承包,雖然給當地帶來了經濟效益,但也造成了環境污染。2015年,根據浙江省“五水共治”的要求,市里需要對水面進行整治,恰巧當年養殖戶們對水域的承包合同也將到期,于是,靈芝鎮決定先將這部分水面以市場價格流轉給鎮政府,再尋找承包者進行生態養殖。
問題是,這么大面積的水域要流轉,必須經過公開招投標,但陳繼瑞擔心:如果公開招投標,水域要是再次被分散的個體承包者中標,可能增加整治的難度。最終鎮里決定,不公開招標,而是先由水產村集體承包。陳繼瑞沒料到的是,一封指控他“私下將水域承包給村支部”的舉報信很快寄到了鏡湖新區所在的越城區紀委。
區紀委經過調查后,確認陳繼瑞是出于公心,沒有為個人、他人和單位謀取利益,最終沒對他做出實質性處罰。據《浙江日報》報道,對于這次免責,陳繼瑞本人并未提出申請。
而一般的容錯免責流程都是由被問責干部提出申請,問責的實施機關,主要是紀委調查核實,并在規定時限內拿出結論性意見。內蒙古要求在30日之內給出意見,湖南則規定在兩個月內給出意見。對于一時難以有定論的情形,浙江各地都推出了“暫掛制”——可以暫緩做出決定,暫掛期間不予追究責任和進行負面評價,暫掛時間不得超過六個月。浙江省臺州市還建立了澄清保護機制,對于可以免責的干部及時消除負面影響,并嚴肅查處誣告陷害等行為。
不過,各地的容錯也是有“底線”的,并非所有領域出現錯誤和過失都可以免責。湖南就規定了“重大安全責任事故除外”;浙江省杭州市也做出了同樣的規定,并嚴禁打著改革創新的旗號搞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
從近幾年的實施效果看,各地的容錯機制確實保護了一些干部,不過,一些學者和地方官方也開始辯證地考慮問題:如果沒有更加健全的制度保證,擔心容錯會背離初衷,甚至成為對個別人的“縱容”。
寧波市一位區委組織部負責人向《南方周末》記者提供的書面材料中就提出,實施容錯要防止兩種錯誤傾向,一是過度容錯糾錯。他認為,容錯糾錯針對的是那些敢闖敢試的干部,而不是那些總想找借口庸政懶政的干部,所以,一定要對問責免責同等重視,不能放過任何一個為官不為的干部。
“此外,還要防止容錯糾錯不實。”這位組織部負責人指出,一些地方雖然出臺了實施辦法,但在具體的執行過程中,往往由少數部門或少數人說了算,甚至以一言堂代替認定程序,導致干部群眾對認定的過程心生疑慮,干部更加不敢干事擔責。
目前各地決定容錯免責的認定機構都是問責的實施機構,也就是紀委。對此,這位組織部負責人建議,應該由黨委來統籌,建立相應的認定機構,可以探索在一個行政區域內設立容錯糾錯委員會,作為非常設機構,由包括紀檢、組織干部在內的官員、法律人士、專業人士,以及利益關聯方代表和群眾代表共同組成。對一些有重大爭議的事項,充分聽取委員會意見,進行初步裁決,再通過公示,征求各方意見,最后再做出裁決。
這一思路與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的想法不謀而合。汪玉凱也認為,容錯機制的具體操作應該引入多元評價機制,不僅有紀檢等問責機構的認定,還應該有社會評價,讓公眾能參與容錯免責的認定,這樣才能保證認定的公正性和科學性。
對于實際操作者來說,認定一個干部是否應該被免責,還有一個困惑:到底哪些錯誤和失誤可以免責?雖然各地是“大同”,但畢竟存在“小異”,基層希望更高層能有統一的“清單”。寧波市江北區委組織部相關負責人就表示,希望由中央相關部門牽頭,出臺細化的容錯免責清單,以便基層有章可循、有據可依。“這樣黨員干部才能從容比對自身行為,進而大膽地闖、大膽地試。”
專家認為,容錯不是技術問題,而是一個基調問題,但目前更多的還是只做技術手段的改變,基調問題還需要改進,努力營造一個讓干部敢闖、敢干的大環境。從保護干部的角度出發,也應該讓干部的各項公務活動規范起來,“一切都依照規矩來,也就沒有什么錯可犯了”。
(轉自《南方周末》)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