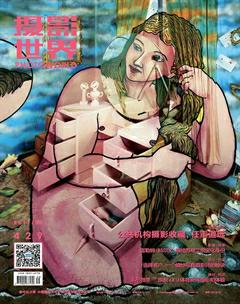一間屋子
章開元
一間屋子里,一盞燈下,同時住著老少三代人是什么滋味,現代年輕人可能無法想象。但在幾十年前,這種情況卻普遍存在,可惜當年的攝影師們,很少有人想到將這種生活狀態系統地記錄下來,盡管這樣的事情也許就發生在他們身邊,或自己身上。
自攝影被發明以來,它就被人類用于記錄一切可以被記錄的事情。攝影成本較高的年代,人們只用它“光顧”相對重大的事件或人物。隨著技術進步、攝影的成本逐漸降低,發生在百姓生活中的邊角瑣事也被攝影師帶入照相機的光影空間。在手機加入攝影行列的今天,影像記錄所涵蓋的范圍更像沒有邊際的宇宙,永無窮盡。感謝攝影發展得突飛猛進,讓今天的我們在回望過去時變得日益高效和簡單。
然而,在影像記錄手段并不普及的年代,許多在今天看來有價值的事情,并沒有被系統地記錄下來,使得今天的我們在試圖了解過去時仍需要費一番口舌,還未必能說得清楚。比如,那些照片中記錄的普通人的生活場景:一間屋子里,幾個人圍坐在一起吃個團圓飯之類,這就是幾十年前中國人日常生活的縮影。可惜在這個方面,攝影師給我們留下的一手資料并不很充分,同時,能利用手頭的有限資料加以說明的人也越來越少。
在我的記憶中,30~40年前的中國,即使在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兩至三代人住在一間1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絕不算是什么新鮮事。有的廚房是幾家公用,有的甚至只是在露天或過道中放一個煤球爐。衛生間這個詞在那時也還沒有出現,住平房的人上廁所時要出門走上一段路。至于夏天想在家里洗個澡,面對一大家子有男有女的情況,窘況可想而知。好在30~40年前,北京的夏天沒有現在這么熱,有時人們用水擦擦身就對付了。到了冬天,公共澡堂是有經濟條件的人們的好去處。當時,住房主要是靠單位分配,享有私房的情況不多,且這兩類住房的情況千差萬別。
當年盛行“三大”,即“大廣播”“大禮堂”“大家庭”。“大廣播”是統一的消息來源,“大禮堂”是娛樂場所,當時,機關單位的娛樂活動都集中在本單位的大禮堂舉辦。大禮堂里通常都有超過一千個座位,單位級別越高,禮堂越講究。這里是機關干部及其家屬看節目、看電影的地方,遍布城市各個角落的電影院則是普通城市居民的休閑場所。而“大家庭”與我們每個家庭過去生活狀態的關系最為密切。
隨著中國人住房條件的不斷改觀,“大家庭”這個詞的表現形態也在發生改變。房子住得寬敞了,一家三代人分住三個地方的情況甚為普遍。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距離也拉開了。想當年三代同堂,你進我出,那種熱熱鬧鬧的感覺,如今恐怕沒有幾個在城市長大的年輕人能說得出來。
家庭人口增多后,首先要面臨的就是住房問題。1950年代,中國的人口出生率猛增,10年工夫多出2億多人。就拿北京來說,剛解放的時候,北京地區常住人口不過百萬人,后來隨解放軍進城有一批人,根據國家建設需要也調進來不少人,沒幾年北京地區人口就超過200萬。這些新增加的人大多處于生育年齡,很快,無數個中等規模的家庭迅速出現。中等規模家庭通常指一對夫婦加兩三個孩子,這樣的家庭在當時社會中占絕大多數,但有五六個孩子的家庭也不少。如果說誰家只有一個小孩,那在當時都是稀罕事,被人們稱為“獨苗”。
那時候,很少聽說過誰家孩子一人住一間屋子,兩人住一間都算寬敞的。幾個小孩跟父母同住一間屋都屬于普遍現象。那時候,普通居民家里也沒什么擺設,除了必要的家具,剩下的地方擺的都是床。那個時代,人們的穿著也很簡單,講究點兒的冬天穿個絨衣、毛衣、襯衫之類,條件差的人在單衣外面直接穿件棉襖,或者光著腿直接穿棉褲,這種情況在40~50年前非常普遍。至于鞋子,大多數人一年到頭就兩雙——單鞋和棉鞋。1960年代以后,開始出現塑料涼鞋,那時能穿得起“空花涼鞋”的人,都是家里有點兒小錢的。至于進家門要換拖鞋這個習慣,直到1980年代,在廣大人民中間還屬于“創新項目”,并不多見。那時也沒有裝修這么一說,普通居民家里一進門就是水泥地,還有磚地和土地的家庭,所以人們也不需要考慮換鞋的問題。
過去的孩子們沒有宅在家里的條件,不僅房間小,也沒什么玩具,小人書就那么幾本,早看膩了。所以,除非天氣條件不允許,孩子們平常都是在戶外的廣闊天地里折騰。我曾看過這樣一張老照片:夜色中的天安門廣場上有許多人坐在地上,借著昏暗的燈光看書。那是當時的真實狀態,老百姓家里不僅沒地方,燈光也比大街上亮不到哪兒去,愛學習的人們就只能這樣借著廣場上的燈光學習。
然而,在當時的全國范圍內,北京人住的還算是寬敞的。論住房的擁擠程度,上海的情況我是親眼所見。尤其夏天,在大街上過夜的上海人不在少數。記得1984年7月,我出差到上海,親眼見到了這壯觀的一幕:講著上海話的大姑娘、小伙子們,白天忙忙碌碌,到了晚上就睡在馬路中間自己家“占領”的那塊僅能放下兩張竹床的小天地里。一到晚上,狹小的居室里溫度時常超過35攝氏度,一絲涼風都沒有。
中國人買商品房,或許是改革開放以來發生在人民消費生活中最大的事件之一,房子是家庭生活消費中真正的“大件”,與之相比,其他東西都是小件。相傳建國之初,作家老舍從美國歸來定居北京,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地方,故想自己掏錢購房,后經周總理批準,才買了一個小四合院。由此看來,那時在北京買房已不是錢的問題,而是需要獲得批準。
1990年代后,單位住房開始按工齡折價提供給居住人,但這還不算真正意義上的房屋買賣。北京的房屋開始作為商品供有需求者合法購買,應該始于21世紀頭一兩年。我記得那時坐在北京出租車里,收音機中不時傳來售房信息,當時出售的房屋基本都在三環以內,售價每平方米3000元左右,首付極低。即使這樣,能拿得出這筆錢的人也是極少。大部分人住著單位分配的房子,讓他們拿自己辛辛苦苦攢下來的那點兒錢去購買商品房,人們很難接受這種觀念。但到了2003年底,“買房子”這個對一般家庭來講都不敢想的奢望,開始升溫,并成為許多家庭在飯桌上討論的頭等大事。那時,位于北京陶然亭公園北門附近的樓盤“陶然北岸”售價每平方米5800元左右,而如今,這個樓盤每平方米的售價大約在10萬元上下。
房子這個事情,有人越說越高興,有人越說越后悔,還有人越說越生氣,總之百感交集,一言難盡。如今的北京,一間小屋子里住著一家三代、六七口人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如果真的還能找到這樣的一家子,開玩笑地說,也應該算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