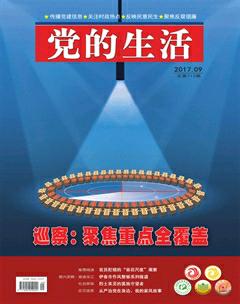烈士英靈的孤獨守望者
王宇萌
賓縣,糖坊鎮,兩公里外寂寥的山坡上,一位身形佝僂的老人在默默地拔著墓碑旁的雜草。
“楊喜林排長,你當年犧牲時多大啊?”
“王同治連長,你的親人都在山東哪個地方啊?”
看著墓碑上的銘文,老人不時地自言自語。
只有問話,只有獨語,只有鳥鳴。很難想象,這樣的場景已經重復了30多年。
這位老人叫張玉山。
1949年出生的張玉山,八個月時就沒了爹娘。因為與新中國同齡,爺爺給他起了一個響亮的小名:解放。
這不是為了“趕時髦”,而是寄托著爺爺心中一份真摯的情感。
從張玉山四五歲懂事開始,爺爺就經常給他講解放戰爭那段血與火的歷史:“四平戰役時,我當過民工擔架員。仗打得那個慘啊,滿地的鮮血都沒過了腳面……那些烈士為了咱把命都搭上了,咱啥時候都不能忘本啊!”
爺爺的話在張玉山的心中澆灌出一個信念:不要忘記為建立新中國獻出生命的那些革命烈士。
20世紀80年代,當了18年拖拉機手的張玉山趕上改革開放的好光景,和另一個居民合伙開辦了一個酒坊,年收入三四萬元,成了那個年代令人羨慕的“萬元戶”。
1985年,張玉山通過招工進入糖坊鎮養路段工作。每天上工,他和同事都要經過糖坊鎮烈士陵園。
說起這個烈士陵園的來歷,要追溯到1946年的一場剿匪戰斗。
那年1月,一伙兒頑匪竄入糖坊鎮,同當地反動武裝相勾結,與新誕生的人民政權為敵。松江軍分區老七團官兵奉命剿匪,在進攻頑匪盤踞地點的戰斗中,21名官兵壯烈犧牲。
1966年,當地政府在埋葬烈士的山坡上修建了簡易陵園,豎立了墓碑,刻寫了銘文。
張玉山每天經過陵園時,總覺得心里非常難受——陵園內一片狼藉,幾乎所有烈士墓都被一人多高的野草給掩蓋了;附近村民散放的牛羊在陵園里隨意排泄,沒人清理……
張玉山不止一次問自己、問同事:“烈士們幫我們解放糖坊,又犧牲在這里,我們糖坊人就這樣對待他們嗎?”
1985年10月,張玉山經過慎重考慮,向道班長提出辭職:“我要去守陵。”
道班長愣住了:“辭職?你才36歲,正是人生的大好時候,真能耐住寂寞去給死人守墓?”
張玉山認真地說:“普通人的祖墳都有人經管,更何況是為我們流過血的烈士?做人得將心比心,陵園就那么荒著,我受不了。”
他寫了一封“決心書”,表示要義務看守陵園,一看到底,堅決看好。
有人聽說后不禁搖頭:“這小子,不是瘋子,就是傻子!”
糖坊烈士陵園占地面積2萬平方米,荒草萋萋,破敗不堪。為了美化陵園環境,1986年春,張玉山自己花了3000元錢在烈士墓四周修起一道寬100米、長140米的綠色長廊,并在陵園里點綴了許多花草。
沒想到,他的這一舉動竟得罪了不少人。
原來,自張玉山進駐陵園,為修建“綠色長廊”,他看見牲口就攆。附近村民認為他多管閑事,沒少跟他吵吵。有人懷恨在心,晚上偷偷進入陵園把張玉山種下的樹苗掰斷。轉年開春,張玉山重新買來樹苗栽上,結果又被掐折。
為了緩和與周邊村民的關系,張玉山買來100斤白酒,又煮上一鍋肉,看到放牧人就去招呼:“來,哥們兒,今天咱不吵吵,一起整點兒!”
借著喝酒的功夫,張玉山和村民聊起看守陵園的初衷,推杯換盞之際,彼此都掏出了心窩子,關系漸漸緩和下來。
經過一年的努力,附近村民對張玉山由反感變成了欽佩。村民張德寶說:“老張,你說得對,給烈士守墓是正事,你這個朋友我交定了!”
張玉山松了口氣,開始擴建陵園,沒承想,又捅了自家的“馬蜂窩”。
1988年春,張玉山請來鐵匠給陵園裝上大門,自己又從山上拉來砂石修了一條路,一共花費兩萬多元。
妻子和他大吵了一架,四個兒子沒有一個站在他這邊。
“你到底想干啥!”妻子涕淚交加,“辭了工作去守墓,我忍了,可這兩萬多塊錢不是大風刮來的啊,能蓋好幾棟房子,你就這么敗禍了,這日子還咋過?!”
“爸,酒坊讓你關了,工作也讓你扔了,咱家這點兒家底你還要往里搭?”兒子也翻臉了。
張玉山無言以對,跑到烈士陵園一遍遍地轉圈。
晚上回來后,他跟老婆孩子態度堅決地說:“我已經給鎮里寫了‘決心書,看守陵園一定要堅持到底,也必須堅持到底,不能說話不算話!”
家人拗不過他,一個個只得忍氣吞聲。沒辦法,他是一家之長啊!
1996年,他將自己在鎮里蓋的四間大磚房賣了三間,又添了三萬多元,建起了陵園門臉兒和鋼筋水泥院墻。
1998年,實在拗不過他的妻子不得不搬到陵園來與他同住,靠每年養雞鴨賺得的萬八千元維持家用。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經過多年的努力,張玉山的義舉終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2004年,賓縣政府對糖坊鎮烈士陵園進行了重修,保留當年的鋼筋水泥院墻,鋪上了水泥步道板,為烈士立起了漢白玉墓碑。
埋葬在糖坊鎮的烈士,大部分是山東籍。他們犧牲時,年齡最大的才23歲,最小的只有16歲。
2004年秋天,一位山東老大姐找到這里——她的小弟弟參軍后來到東北,犧牲在黑龍江,但不知具體葬在哪里。說明來由后,張玉山領她去看墓地。
老大姐挨個墓碑看,找了好幾圈也沒找到弟弟的墓,忍不住掉下眼淚。臨走時,她對張玉山說:“大兄弟,這個陵園真美,他們睡在這里也挺好。雖然沒找到弟弟,但我要代表那些烈士家屬謝謝你,請你一定好好守護他們。”
老大姐千里迢迢的尋親之舉,讓張玉山深為震動:“烈士們犧牲的時候正是好年華,他們的親人肯定不知道烈士長眠在這里。”
張玉山動了為烈士尋親的念頭。endprint
2005年春,為了尋找這些烈士的資料,張玉山自費到黑龍江省軍區七次,每次都吃了閉門羹。但他沒有放棄,等到第八次去時,守衛人員一眼就認出了這個老頭兒,破例叫檔案室的人領他進去。
工作人員聽明來意后,深受感動:“這些年找烈士的人多了,但像您這樣的還是頭一個!跟您說實話吧,1960年之前的烈士檔案都在沈陽軍區。”
歷時兩年多,張玉山找到三位黑龍江籍烈士的親屬和其他烈士的部隊番號與籍貫。
由于沒有更詳細的資料,加上年代久遠,山東籍烈士的親屬一直未能找到。于是,他決定到山東為烈士尋親。
2009年9月,張玉山來到山東省濟南市。為了引起輿論的關注,幫助他提供線索,他在自制的馬甲上寫下“義務為烈士尋親”幾個大字——那是張玉山咬破手指,用手指寫上去的血書。
令張玉山感到遺憾的是,這次“尋親之旅”并無太大收獲。因為趕上老伴兒有病,張玉山只能給當地報社、電視臺的記者們留下聯系方式,黯然而歸。
山東之行雖一無所獲,但令張玉山稍感安慰的是,之前找到的黑龍江籍烈士家屬已經來陵園祭拜。
三位黑龍江籍烈士徐德、趙有、劉濤,只有徐德還有后人。徐德的兒子徐念英(化名)來祭奠時,正好趕上張玉山從山東回來。他含著熱淚對張玉山說:“感謝您多年來一直照看我們家為國捐軀的親人。”
張玉山不知道的是,他的山東尋親之旅就像丟入湖中的石子,已經泛起陣陣漣漪。
2015年清明節前夕,烈士劉本仁的后代劉光德通過媒體得知父親的墓地在黑龍江省賓縣糖坊鎮烈士陵園,立即帶著妻子和女兒前來祭掃。
一到烈士陵園門口,劉光德的表情立刻肅穆起來,當“劉本仁烈士之墓”幾個字映入眼簾時,他快步上前,“撲通”一聲跪倒在地:“爹,這么多年,我們終于找到您了……”
70年來,劉光德無數次設想過與父親“團聚”的場面,當這一相聚場面真的出現時,這個七尺男兒沉積在心底的情感終于得到了釋放。他重重磕了三個響頭,久久不肯站起。
祭拜結束后,劉光德就像對待失散多年的兄弟一樣,緊緊抱住張玉山,動情地說:“謝謝大兄弟,這么多年守護我爹和他的戰友,辛苦你了!”
“這么多年的罪,沒白遭。”這一刻,張玉山覺得值了。
30多年來,他用誠信恪守諾言,他用奉獻維護崇高,他用執著書寫信仰,他用情懷感染他人,他用生命守望著先烈的英靈,守望著我們這個民族的魂和根。
如今,年已68歲的張玉山初心不改:“有些烈士的親人還未找到,我得替他們照顧好這群回不去家的人。”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