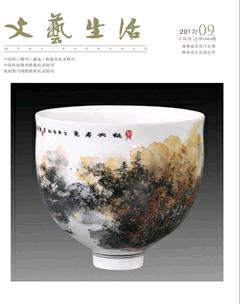“紅色經典”作品的當代改編
劉佳祺
摘 要:作為“紅色經典”的樣板戲曾經給人們的文藝及精神生活帶去了難以忽視的影響。從談及樣板戲“色變”。到徐克《智取威虎山》的口碑票房雙豐收,本文就要從樣板戲出發(fā),以徐克對《智取威虎山》系列經典前文本的改編為例,探尋“紅色經典”在當代改編的新可能。
關鍵詞:紅色經典;樣板戲;當代改編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7)27-0106-02
一、由《林海雪原》的早期電影改編說開
提及小說《林海雪原》的電影版,人們首先想到的也許是革命樣板戲《智取威虎山》。1970年,經過修改而拍攝的電影《智取威虎山》終于完成。這部屬于“無產階級文藝”的創(chuàng)造,在無產階級專政最高權力的直接控制下,響應了“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的號召,表達了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無限忠誠,一度被列為八部樣板戲之首。
早在1960年,八一電影制片廠就已經拍攝過小說同名電影《林海雪原》。這一版本截取了曲波原著中的經典橋段“智取威虎山”,將楊子榮塑造成中心人物。盡管毛澤東在1964年做出了“不要把楊子榮搞成孤膽英雄”①的指示,但是到了樣板戲中,由于創(chuàng)作團隊對“三突出”原則的遵循,加之江青對少劍波人物的壓制,楊子榮的孤膽英雄形象實際上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他甚至直接成為了主要英雄人物。
盡管如此,政治話語的籠罩仍不能否定《智取威虎山》的藝術貢獻。雖然它過分強調國家意志,忽視個體情感訴求,但是在將京劇搬上熒幕的過程中,由于江青提出“還原舞臺高于舞臺”的原則,主創(chuàng)人員還是做了很多努力。比如鏡頭上的匠心調度使正反面人物對比鮮明,戲劇也更具完整性;立體置景的運用使畫面更具觀賞性;音樂設置上鏡頭與節(jié)奏也不斷呼應,這些都使電影獲得了新的生命力,也為之后戲劇轉變成電影的拍攝提供了相當借鑒。
二、徐克的“紅色經典”再生產
2014年底,《智取威虎山》以直逼9億的票房讓我們看到了此類題材電影的一種可能。這部電影獲得良好口碑除了卡司、投資、宣傳的保駕護航外,導演對于原作的重構也功不可沒。
作為“紅色經典”,《林海雪原》富于寫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的描寫為電影提供了廣闊的表現(xiàn)空間。徐克以一種更集中的形式對過去系列作品進行重新解讀。在人物塑造上,雖然影片中還保持著鮮明的正邪對立,但豐富性顯著提升。正面人物如楊子榮,他是被政治話語規(guī)訓的革命政治范本,一人深入匪窩,智斗匪徒,充滿革命話語籠罩下的“主角光環(huán)”。徐克把他變成了一個亦正亦邪的江湖俠士,消解了本顯刻板的軍人氣質,增添了江湖豪俠的快意恩仇。他與少劍波也由前文本中革命隊伍里的上下級同志,轉變?yōu)樾市氏嘞У男值芮檎x。反派角色也不再單純被貼上“壞人”標簽,徐克在表現(xiàn)他們殘酷的同時,也展現(xiàn)了他們人性的一面。此外,小栓子和青蓮這兩個新增角色的出現(xiàn)不但豐富了故事的線索,還消解了原本樣板戲中的政治表達。楊子榮和小分隊的行動都從抽象的革命目的落到實處——除暴安良。
眼花繚亂的技術也是電影成功的關鍵。真實的戰(zhàn)斗場景、以假亂真的特效加上不斷運動的短鏡頭使電影的戰(zhàn)斗場面酣暢淋漓,經典打虎橋段也栩栩如生。技術的運用帶來感官的愉悅,讓觀眾更易投入故事。而如此的視覺沖擊力和藝術表現(xiàn)力,也是之前版本不曾做到的。
但是,《林海雪原》畢竟是一部50年代反映解放軍剿匪的革命傳奇,盡管技術支持下的戰(zhàn)斗場面可以還原,觀眾如何彌合時代割裂感也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徐克的做法是將集體記憶轉化為個體記憶。以事件親歷者后代追尋祖輩記憶的個人化敘述方式,為故事本身的武俠氣質和浪漫想象提供合理性,也為當下主流年輕觀影群體進入歷史搭建橋梁。
三、“紅色經典”改編在當代的一種可能
當今時代,“紅色經典”的改編反而被人懷疑不符合時代潮流。許多作品為片面迎合大眾口味做了很多庸俗改動。比如電視劇《林海雪原》。楊子榮在里面不僅與座山雕卷入獵奇的“三角戀”,還有了“私生子”,這種所謂“嘗試,很容易激起心中已根植小說、電影等各種形式前文本的觀眾的逆反心理。“紅色經典”并不是不適合改編,問題在于,如何把握它本身具有的政治革命話語與當下商業(yè)話語相結合的尺度。畢竟“‘紅色經典”的再度流行不僅是一個弘揚主旋律的問題,而是同我們的全民歷史記憶與社會文化心理密切相關。”②
實際上, “紅色經典”中的大多數既有跌宕起伏的劇情,又有現(xiàn)實與傳奇結合的色彩,未嘗不算當下影視圈主流的“大IP”。加之“紅色經典”儼然已經融入老一代的記憶及情感,基于歷史延續(xù)性和權威性的考慮,主流意識形態(tài)對“紅色經典”的改編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社會的重大轉型時期所形成的焦慮和空虛給‘紅色經典的大規(guī)模復出提供了歷史機遇。”③,“紅色經典”改編在當代有了新的可能。
徐克顯然抓住了“紅色經典”被掩蓋住的商業(yè)價值。他在保持原作精髓的基礎上,用武俠片的方式重新包裝故事,而不是向譬如“手撕鬼子”的奇葩劇情靠攏。這樣他不但規(guī)避了觀眾的審美疲勞,還使重拍的“紅色經典”有了賣點。此外,他還添加了大量類型片元素,幽默又生活化的設計使影片在緊張氛圍得到了緩解。總之,徐克“用現(xiàn)代手段去拍,用商業(yè)電影的形式去包裝,用好萊塢的大片方式去制作”電影,他沒有讓英雄人物在人性豐富化的過程中被歪曲,沒有讓反面人物在“人性化”的過程中變得光輝,沒有讓故事情節(jié)在“豐富化”的過程中蓄意迎合時尚趣味。電影既遵循了原有主流價值觀念,又尊重了觀眾對諸多前文本已經形成的認知定位和心理期待。以上種種,都是“紅色經典”作品在當代改編的過程中可以借鑒的。
但是,徐克的電影文本中還有一個改變就是人民群眾的位置。在之前的版本中,解放軍小分隊總是聯(lián)系群眾。但是在這部電影里,人民群眾雖然逐漸表現(xiàn)出了對解放軍的親近,但是自始至終處于一個“拒絕革命”的狀態(tài)。這樣,英雄與群眾的關系被簡單定位為“拯救者與被拯救者”,而作為“被拯救者”代表的小栓子即使在一腔感恩與仇恨中融入解放軍,到最后也沒有表現(xiàn)出對于革命的主體認同。可能這才是關鍵,屏蔽掉政治話語的干擾,才能永葆故事通俗與傳奇的生命力。
我們應該意識到,“紅色經典”傳遞著人類邪不勝正的正義愿景與樂觀、堅韌的普世精神。“書寫革命歷史和英雄傳奇的紅色經典被改編的最終意義是與當代文化意識對話、碰撞,開掘其精神道德資源,實現(xiàn)其歷史超越性。”④
所以,“紅色經典”的當代改編不能機械停留在過去,更不能惡意迎合當下消費語境,創(chuàng)作者和生產者應該借助“紅色經典”的外衣,挖掘其深刻的內涵,只有這樣,“紅色經典”才能不被時代淘汰。
注釋:
①文化部批判組.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揭露江青掠奪革命樣板戲成果的罪行[N].人民日報, 1977-2-13.參見姚丹.“無產階級文藝”理論、實踐及其成效初析以樣板戲<智取威虎>為中心[J].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03):104.
②熊文泉.“紅色經典”藝術生產的內在機理分析——以作品<林海雪原>的生成、改編為例[J].當代電影,2004(06):69.
③侯洪.“紅色經典”:界說、改編及傳播[J].當代電影,2004(06):81.
④李艷.紅色經典下的快意江湖——論<智取威虎山>的電影改編[J].新聞界,2015(10):62.
參考文獻:
[1]姚丹.“革命中國”的通俗表征與主體建構——<林海雪原>及其衍生文本考察[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2]熊文泉.“紅色經典”藝術生產的內在機理分析——以作品<林海雪原>的生成、改編為例[J].當代電影,2004(06).
[3]侯洪.“紅色經典”:界說、改編及傳播[J].當代電影,2004(06).
[4]李艷.紅色經典下的快意江湖——論<智取威虎山>的電影改編[J].新聞界,2015(10).
[5]任姍姍.豪情壯志沖霄漢——導演徐克與電影〈智取威虎山〉[N].人民日報,2014-12-25.
[6]路楊.<智取威虎山>:“革命中國”的想象、追認與終結[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5(0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