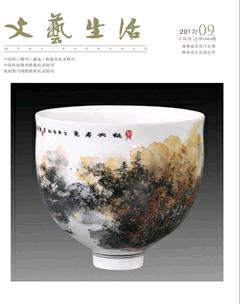蘇州博物館新館設計中存在的問題及其改造反思
馬婷+靳文杰

摘 要:文章主要從蘇州博物館新館的設計項目入手,分析項目中存在的問題并對其進行改造,改造的目的在于從新的視角使得設計作品更具合理性,基于項目改造引發自我的思考。
關鍵詞:蘇州博物館新館;蘇州園林;現代主義建筑;庭院空間;建筑形態
中圖分類號:TU24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7)27-0192-01
一、蘇州博物館新館設計概況
蘇州博物館新館的場地位置十分特殊,該 地塊被貝聿銘稱為“圣地”,在這一地塊上設計博物館是“人生最重要的挑戰”,“在這里設計博物館很難很難,既要有傳統的東西,又要 有所創新,傳統的東西就是要運用傳統的元素,讓人感到很協調、很舒服;創新的東西就是要運用新的理念、新的方法,讓人感到很好看,有吸引力,因為時代是在發展的”。
“中而新,蘇而新”的設計思路,博物館新館的設 計結合了傳統的蘇州建筑風格,把博物館置于 院落之間,使建筑物與其周圍環境協調統一。
二、蘇州博物館使用中存在的問題
1.過分追求平面布局與周圍環境的統一,忽視建筑本身。建筑結構采用傳統南方園林的設計手法,使得整體建筑環境舒適宜人。但作為博物館,陳設展覽也是其重要的功能,由于建筑頂端矗立著正方體的構筑,室內采光受到影響。同時由于正方體垂直的界面,使得建筑整體立面高差懸殊較大,建筑結構舒緩的節奏感有些許破壞。
2.植物配置缺乏,整體空間環境缺乏靈動。傳統園林設計講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植物在園林設計中的應用也十分重要。植物不僅溝通人與自然,也溝通室內與室外,聯系生命的脈絡。
二、蘇州博物館改造意見(對于建筑屋頂的改造)
元素的提煉為設計提供動力,用現代技術手段將玻璃與石灰墻面結合,虛實的強烈對比使得整體建筑風貌更具趣味。保持原有平面布局和空間組合,在其立面構成中加以調整,引入新的材質,在滿足功能條件的同時兼顧審美需求。
將原有正方體墻面屋頂拆除,替換成用玻璃材質,立面構圖更加舒緩,具有延展性;同時,玻璃作為虛的建筑界面,有效的將自然光引進室內,更好的為展品陳設提供光線,而非人為的光源,是生態可持續的體現。
三、基于上述改造的總結與思考
在蘇州博物館新館中,特殊的城市環境因素是決定性的制約元素,也決定了新館的空間形態。新館布局上延續了江南院落式的布局方式,在現代幾何造型中體現了錯落有致的空間關系。在環境和空間的關系中,新館通過群體建筑形象上的延續和對周邊環境的延續,使得新館的空間融入了周邊的環境。在整體布局上也和東側的忠王府格局也并無沖突,都源自于貝聿銘對蘇州園林布局內虛外實的借鑒。新館在整體布局中借鑒了傳統園林,但在建筑設計上仍然是西方現代主義建筑語言。早期,雕塑性和幾何性是貝聿銘作品中常有的特征,但在新館設計中貝聿銘吸取本地的、民族的和歷史文化所遺留下來的痕跡,在當地的地域性文化中提取元素,并將裝飾性符號引入建筑外觀,使得幾何性特征變得更加豐富而復雜,同時雕塑性這一特質被減弱。其次,新館把景觀引入空間,通過各種借景手法,溝通了室內外。現代主義建筑提倡室內外空間穿插與流通,并給參觀者提供了舒適健康的空間環境。
在新館中,特殊的城市環境因素是決定性的制約元素,也決定了新館的空間形態。新館布局上延續了江南院落式的布局方式,在現代幾何造型中體現了錯落有致的空間關系。在環境和空間的關系中,新館通過群體建筑形象上的延續和對周邊環境的延續,使得新館的空間融入了周邊的環境。在整體布局上也和東側的忠王府格局也并無沖突,都源自于貝幸銘對蘇州園林布局內虛外實的借鑒。
新館中的庭院借鑒了蘇州傳統園林造園的元素,疊石、理水、亭、竹林。但在表現手法上是現代主義提倡的“少即多”的造景方式,樹木的孤植及精心挑選、簡約而寫意的疊石風格。讓人的感受卻是日本枯山水的枯寂、平淡的禪意。中國的建筑和庭院是融合的、感性的、柔性的,而蘇新館在外形上給人的感觀是單純、機械、理性而剛性的,這符合西方現代主義建筑的審美理念。
中國傳統建筑形式的空間組合,使新館的內部空間更加豐富。在新館改造中,通過改變光線的流量和角度創造是創造空間意境的主要方式,新館屋頂上的大玻璃配合內飾的木質墻面,把自然光融柔和的進入空間。光線的投影使空間流動起來,并隨著時間的變化游走在墻面、地面、樓梯和家具上。以及動靜的變化,營造出一個成功的展示空間。并在在形式上、空間上不斷進化。
新館是貝聿銘對中國建筑所做的探索,對以后我們的設計具有啟示作用。在如今城市化建設不斷加快的背景下,新館的建成雖然有爭論和一些遺憾之處,但我認為,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仍然在設計手法上不斷創新,并關注與地域性文脈的結合,試著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的建筑之路,這是值得我們反思和尊重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