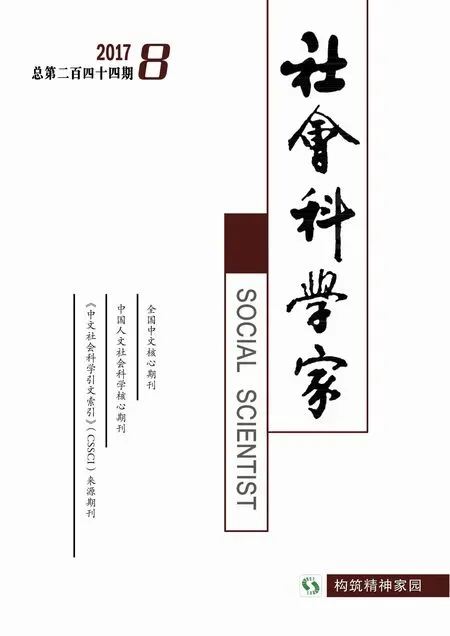推定、倒置抑或第三條道路
——環境污染侵權中因果關系舉證責任分配研究
葉增勝
(浙江大學 光華法學院,浙江 杭州 310008)
【法學與法制建設】
推定、倒置抑或第三條道路
——環境污染侵權中因果關系舉證責任分配研究
葉增勝
(浙江大學 光華法學院,浙江 杭州 310008)
在環境污染侵權糾紛中,污染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分配是一個核心問題。對于該問題,學界存在因果關系推定和舉證責任倒置兩種意見。從文義上看,我國《侵權責任法》第66條對于該問題確立了舉證責任倒置規則。但是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無法兼容被侵權人的初步證明責任,對污染者過于嚴苛。因此有必要在解釋上認為被侵權人的初步證明責任是適用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前置條件,以緩解污染者過于不利的地位。而這一解釋,既符合學界的共識,也符合我國司法實踐的主流,同時也體現了立法者的觀點。
環境污染侵權;《侵權責任法》第66條;舉證責任倒置;因果關系的推定;初步證明責任
一、問題的提出
在我國現階段,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因環境污染引發的糾紛也迅速增多。作為解決環境污染侵權問題的一般性法律,2010年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顯得愈加重要。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侵權責任法》在環境污染侵權法方面的相關規定及其在司法實踐中的實施情況。
依據《侵權責任法》第65條的規定,環境污染侵權適用無過錯責任的歸責原則,[1]被侵權人無須證明污染者在實施污染行為時存在過錯,那么此時,污染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系就成為判斷環境污染侵權責任是否成立的關鍵。而《侵權責任法》第66條規定,污染者對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即“因污染環境發生糾紛,污染者應當就法律規定的不承擔責任或者減輕責任的情形及其行為與損害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如何理解這一規定就成為整個環境污染侵權中最為重要之問題,這一規定究竟是指對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倒置,抑或是對于因果關系的推定,被侵權人是否負有對因果關系的初步證明責任?對上述問題的不同回答,將導致迥異的結果。
二、我國《侵權責任法》第66條的立法選擇及其困境
(一)我國學界對《侵權責任法》第66條所確立規則的爭論
在《侵權責任法》正式出臺之后,許多學者都承認該法第66條確立了舉證責任倒置規則,但同時亦認為被侵權人對于因果關系仍然負有初步證明的責任。
具體來說,王利明先生認為《侵權責任法》第66條的規定采納了舉證責任倒置的方法,[2]但同時認為受害人必須要就初步的因果關系進行證明,[2]在受害人證明了損害和被告的污染行為之間具有可能性之后,由污染者反證證明其污染行為與損害之間沒有因果關系,[2]最后再由法官根據污染者的反證內容,從而確定是否存在因果關系。[2]
周友軍先生也承認依據《侵權責任法》第66條的規定,因果關系的認定實行舉證責任倒置,而且其亦認為受害人需要進行初步的證明,而該初步證明的標準是事實可能存在。[3]令人困惑的是,周友軍先生在肯定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同時,又表明《侵權責任法》第66條屬于因果關系的推定規則。[3]
與上述觀點不同的主要有程嘯先生和楊立新先生。
程嘯先生認為依據《侵權責任法》第66條的規定,環境污染責任實行的是因果關系推定,[4]但這并不意味著原告不負擔任何舉證責任,在訴訟中,原告至少應提出初步的或蓋然性的證據,據以建立加害人的環境污染行為與自己所受損害之間的初步聯系[4]。
楊立新先生在《侵權責任法》正式出臺之后也依然認為該法第66條規定的是環境污染責任的因果關系推定,[5]并認為被侵權人在訴訟中應當首先證明因果關系具有相當程度的蓋然性,即環境污染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的可能性[5]。
在上述學者的論述和觀點中有三點值得注意。
一是無論是主張舉證責任倒置還是因果關系推定,幾乎所有學者都認為被侵權人負有某種程度的初步證明責任,在其完成該初步證明責任之后,才由污染者提出反證,證明不存在因果關系。
二是程嘯先生與楊立新先生堅持認為《侵權責任法》第66條確立的是因果推定規則,而非舉證責任倒置規則。
最耐人尋味的是周友軍先生的觀點。其在肯定該條文確立的是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同時,有表明該條文屬于因果關系推定規則。
(二)對我國學界觀點的探討
綜合學界的觀點,筆者有如下分析:
第一,舉證責任倒置與推定并不相同。雖然都能同樣減輕被侵權人的舉證責任,但是兩者都有著各自不同的適用邏輯和內涵,不可混為一談。舉證責任倒置規則事實上是“應由此方當事人承擔的證明責任被免除,由彼方當事人對本來的證明責任對象從相反的方向承擔舉證責任”[6]。在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則下,被侵權人無須承擔任何程度的先行證明責任,因為由污染者承擔說服責任,并在待證事實真偽不明時承擔敗訴的風險。而因果關系的推定則需要被侵權人先行證明基礎事實以及基礎事實與推定事實之間的常態關系,并以此證明推定事實的存在,然后才由污染者承擔證明因果關系不存在的證明責任。而污染者是否要承擔證明因果關系不存在的說服責任,則需要區分事實上的推定與法律上的推定,如果是事實上的推定,污染者無須承擔說服責任,在待證事實真偽不明時由被侵權人承擔敗訴的風險;如果是法律上的推定,那么污染者就需要承擔說服責任,在法官無法確定因果關系是否存在之時承擔敗訴的風險。因此,舉證責任倒置與推定的區分確有必要,對于《侵權責任法》第66條所確立的規則必須在兩者之間做出選擇,而不能認為該條文在確立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同時又確立了因果關系的推定規則。關于舉證責任倒置與因果關系推定在舉證責任分配上的具體差異,可參見下表。[7]

基礎事實 因果關系分配原則負擔當事人污染受害者的證明負擔排污者的證明負擔一般原則 無(說明:由于不適用推定,因此并不存在基礎事實)污染受害者(說明:由污染受害者就因果關系存在事實承擔首先提出證據的責任和說服責任)強 弱事實上的因果關系推定污染受害者(說明:污染受害者對基礎事實承擔首先提出證據的責任,并要使法官對此形成積極的內心確信。)污染受害者(說明:盡管污染受害者可以通過對基礎事實的證明實現對因果關系事實的證明,但是并未卸除其對因果關系事實的說服責任。)較強 較弱法律上的因果關系推定污染受害者(說明:污染受害者對基礎事實承擔首先提出證據的責任,并要使法官對此形成積極的內心確信。)排污者(說明:在污染受害者完成對基礎事實的證明后,排污者就要承擔對因果關系事實的說服責任。)適中 適中因果關系舉證責任倒置無(說明:由于不適用推定,因此并不存在基礎事實。)排污者(說明:由排污者就因果關系不存在這一事實承擔首先提出證據的責任和說服責任)弱 強
第二,學者均主張“被侵權人負有某種程度的初步證明責任”的原因在于如果被侵權人無須負擔先行提出因果關系存在的初步證明責任,而僅僅只需要證明污染行為與損害結果,鑒于環境污染侵權本身所具有的復雜性,直接由污染者承擔證明因果關系不存在的說服責任,對污染者未免過于嚴苛(參見上表),過于加重污染者的責任,也容易導致濫訴,對被侵權人也顯得保護過度。因此學者們無論持何種主張,都不約而同肯定被侵權人需要承擔某種程度的初步證明責任。事實上依據學者們的觀點,該被侵權人所要承擔的初步證明責任都會被減輕,無須達到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這已經對被侵權人進行了保護。
但是筆者在前文中已提到,在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下,證明因果關系不存在的說服責任完全在污染者一邊,被侵權人無須對因果關系存在先行承擔任何程度的證明責任。因此一方面認為《侵權責任法》第66條確立了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另一方面又認為即便是在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則下,被侵權人仍然需要承擔因果關系的初步證明責任,這并不符合我們對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一般性理解。也就是說,按照前文的結論,一般性的舉證責任倒置與被侵權人對因果關系的初步證明責任并不兼容,而被侵權人的初步證明責任一般只存在于推定情形。
(三)本文對《侵權責任法》第66條所確立規則的認定
要確定我國《侵權責任法》第66條所確立的規則究竟為何,必須首先明確該條文在文義及其形式邏輯結構,并結合事實上因果關系推定、法律上因果關系推定以及舉證責任倒置各自的性質來加以認定。
事實上的因果關系的推定是在法律沒有規定的情況下,由法官基于良知和公正的理念要求,理性地運用經驗法則對個案具體事實進行認定時所采用的方法。比如說日本沒有在立法上明確規定因果關系推定,[7]而是通過一系列的判例學說發展出了一些事實上的因果關系的推定方法。由于我們國家《侵權責任法》第66條就環境污染侵權的舉證責任做出明確的規定,由污染者負責證明不存在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因此我國并不存在事實上因果關系的解釋空間。
而法律上的因果關系推定是指法律上明確規定的推定。而我國《侵權責任法》第66條明確規定“因污染環境發生糾紛,污染者應當就法律規定的不承擔責任或者減輕責任的情形及其行為與損害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就“法律上有明確規定”這一點來說確實符合法律上因果關系的特征。但是該條文的表述在文義以及邏輯結構上與法律上的因果關系存在偏差。具體來說,《侵權責任法》第66條中并未體現推定的內容,而是直接讓污染者就“其行為與損害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關于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從立法過程窺見一二。在立法過程中,有學者就提出環境污染侵權的因果關系應當適用因果關系的推定,而非舉證責任倒置。例如楊立新教授主持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草案建議稿及說明》第120條中就規定了因果關系推定規則,其具體表述為:因環境污染造成他人人身或財產損害的,其污染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的因果關系可以實行推定。結合各國關于因果關系推定的表述,應該說楊立新教授的這一表述是典型的對因果關系推定的規范。而該表述就與《侵權責任法》第66條所規定的“因污染環境發生糾紛,污染者應當就...行為與損害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的表述完全不同。無獨有偶,同樣主張因果關系推定的張新寶教授在其對《侵權責任法草案(二次審議稿)》的修改建議中,明確提出要將二次審議稿第69條修改為“因污染環境發生糾紛,推定排污行為與損害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排污者能夠證明不存在因果關系的,不承擔賠償責任”,[8]并在說明修改理由時提出是“對推定因果關系做更準確的表述”[8]。由此看來,舉證責任倒置與因果關系推定在文字表達上大相徑庭,《侵權責任法》第66條的規定從文字表述上看當屬“舉證責任倒置”的表述無疑。關于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從形式邏輯的角度進行論證。推定的邏輯表述為“A”→“B”。“A”為基礎事實,“→”代表某種常態關系,“B”則是推定事實。而我國《侵權責任法》第66條的規定是“污染者應當就.……行為與損害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其邏輯可以表述為“非B”→“B”。這與推定的形式邏輯結構不相符。
最后,從條文表述的文義和條文的形式邏輯結構兩個方面來看,《侵權責任法》第66條確立的是對于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倒置規則。①關于為何符合舉證責任倒置規則,也將在立法探討部分進行討論,此處不再贅述。民事訴訟中的舉證責任倒置是指按照法律要件分類說在雙方當事人之間分配證明責任后,對依此分配結果原本應當由一方當事人對某法律要件事實存在負證明責任,轉由另一方當事人就不存在該事實負證明責任。[9]在《侵權責任法》第66條中,按照舉證責任的一般分配原則原本由被侵權人負擔的對于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改由污染者加以承擔,體現的正是舉證責任倒置規則。
(四)適用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困境
依筆者的分析,我國《侵權責任法》第66條確立了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則,然而該規則卻可能存在某些適用上的困境。
首先,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在適用時,不要求原告對加害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常態關系承擔舉證責任,因而由其“推定”①此處的“推定”并非前述的事實上或法律上的因果關系推定,而是在舉證責任倒置規則下徑直“由污染者承擔證明不存在因果關系”的另一種表達方式。而成立的因果關系欠缺邏輯基礎,是不可靠的。[10]而正因為原告僅須就污染行為與損害結果承擔舉證責任,在許多事實上不存在因果關系的情況下,原告基于勝訴的預期依然會提起訴訟,造成濫訴的風險,給法院和有某種程度的排污行為的企業帶來極大地負擔,造成司法資源和社會經濟資源的浪費。
其次,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基本上使被告無機會翻身,被告敗訴為適用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必然結果。[10]在環境污染侵權中,原被告的舉證能力確實存在較大的差異,需要對原告給予適當的照顧,但是徑直適用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卻存在矯枉過正的風險。具體而言,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第一,讓被告反向證明因果關系不存在比讓原告正向證明因果關系存在的難度更大。原因在于許多疾病和損害的成因在科學上尚不清楚,原告的正向證明存在難度,被告的反向證明同樣存在難度,甚至更甚。第二,被告在舉證責任倒置條件下承擔的證明標準相當高,使其難以完成舉證。在舉證責任倒置中,因果關系不存在的說服責任是由被告來承擔的,這意味著當因果關系是否存在這一事實處于真偽不明的狀態時,被告需要承擔相應的敗訴責任。我國《證據規定》第73條對民事訴訟中的法定證明責任進行了規定,根據學理解釋,該條所規定的民事訴訟的法定證明標準為高度蓋然性標準。據此,被告對因果關系不存在的證明標準非常高,再加之前述被告對因果關系反向證明的巨大難度,決定了被告幾乎難以完成舉證責任,敗訴幾乎成為舉證責任倒置的必然結果。[10]
從中我們也可以窺知為何我國學者在認定《侵權責任法》第66條所確立的規則的問題上如此地進退維谷。被侵權人的初步證明責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否則對污染者過于嚴苛,會導致濫訴;而被侵權人的初步證明責任只存在于對因果關系的推定規則之中,其與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并不兼容,恰恰我們國家的《侵權責任法》第66條所確立的是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無疑,而舉證責任倒置與推定是涇渭分明的兩個不同的概念,在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則下,被侵權人無須承擔初步證明責任的弊端就會盡顯無疑。
三、司法實務中就環境污染侵權糾紛因果關系舉證責任分配的現狀及其分析
法院直面社會生活,必須對社會生活中出現的問題給予回應。在《侵權責任法》第66條就環境污染侵權糾紛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確立了舉證責任倒置規則之后,法院在具體案件的裁判中到底是如何適用這一規則,是否出現了筆者前文所說的困境,法院又是如何處理的。帶著這些疑問,筆者在北大法寶中查找《侵權責任法》第66條的法寶聯想案例,共找到71條記錄,與環境污染侵權糾紛相關且相互獨立的案例有28個,這28個判決對于因果關系與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表述共有兩種情形:
(一)肯定被侵權人的初步證明責任及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相關案例
有23份判決書明確提出被侵權人必須就污染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承擔初步證明責任,同時明確肯定就該因果關系證明適用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在被侵權人承擔初步證明責任,由其證明存在因果關系的可能性之后,再由污染者就該因果關系的不存在承擔舉證責任。值得注意的是,在這23份判決書之中,有兩個案例正是因為被侵權人無法完成自己的初步證明責任,而被判令敗訴,其判決書概述如下:
在“閻栓林與劉云安環境污染責任糾紛案”②新鄉市輝縣市法院民事判決書(2012)輝民初字第3292號。中,法院認為原告所提供的證據2中僅診斷書并不足以證明原告病癥與牛糞污染的因果關系;法院還認為因污染環境發生糾紛,污染者應承擔相應的舉證責任;原告訴稱自己受牛糞污染致病,但未能提供原告致病及花費的有效證據,并因此對原告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在前述案例中,法院特地提到“因污染環境發生糾紛,污染者應承擔相應的舉證責任”,根據語境,這里所說的“相應的舉證責任”,事實上就是指就因果關系的不存在承擔舉證責任。那么在明確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倒置規則之后,法院認為在污染者就該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之前,被侵權人必須提供“受牛糞污染致病”的證據,也就是說被侵權人必須就污染者的污染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承擔初步的證明責任,而后才由污染者就該因果關系的不存在承擔舉證責任。而本案中,就因為原告所提出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原告病癥與牛糞污染的因果關系”,而此時并不適用舉證責任倒置規則,被告無須承擔舉證責任,因此判決原告敗訴。
在“原告趙振剛訴被告鄭州嶸昌集團實業有限公司水污染責任糾紛案”①(2013)登民一初字第308號中,法院以“原告又未能提供證據證明其所患高血糖、高血壓、高血脂系因飲用井水所造成,故原告要求被告賠償損失因無證據予以證明,”對原告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判令原告敗訴。
(二)不承認被侵權人的初步證明責任而直接適用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相關案例
有5份判決書沒有明確提到被侵權人負有初步證明污染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的責任,而是只明確提到了污染者負有證明該因果關系不存在的責任,也即被侵權人無須就因果關系進行舉證,徑直適用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同樣需要注意的是,該5份判決書中,污染者都因為不能成功證明污染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而承擔賠償責任。
這其中較為典型的有,在“南陽市鑫東海置業有限公司與穆大紅等噪聲污染侵權糾紛上訴案”②河南省南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1)南民一終字第432號。中,法院認為“三原告訴鑫東海公司所造成的環境污染侵權行為,屬于民法規定的特殊侵權行為,依法應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原則”,“被告鑫東海公司在原告所居住的房屋負一樓安裝高壓配電設備是否造成原告室內噪音值和電磁輻射值超標,被告負有舉證責任,而被告沒有提供相應證據證明其未對原告造成侵害”,因此判令被告承擔侵權責任。在本案中,法院并沒有要求原告證明污染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而是認為該案應當徑直適用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由被告證明該因果關系不存在。
在“濟南銀座奧森熱電有限公司等與李傳國環境污染責任糾紛上訴案”③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3)濟民四終字第372號。中,法院認為“熱電公司向李傳國的果園排放污水及李傳國的損失均可以認定”,同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六十六條規定,因污染環境發生糾紛,污染者應當就法律規定的不承擔責任或者減輕責任的情形及其行為與損害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上訴人熱電公司和環冠公司均不能證實向外排放污水與李傳國的損失不存在因果關系,也不能舉證證明存在不承擔責任和減輕責任的情形,因此,熱電公司與環冠公司對李傳國的損失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在本案中,被侵權人只需證明污染行為與損害事實,而這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的證明適應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由污染者負責證明因果關系不存在的舉證責任。
(三)對我國司法實踐的評析
概言之,環境污染侵權糾紛因果關系舉證責任分配在我國司法實務中呈現出三個方面的特點:
首先,從我國的司法實踐上來看,大多數法官在面對環境污染侵權糾紛時,都會要求被侵權人先行證明污染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存在可能的因果關系,然后再依據《侵權責任法》第66條的規定要求污染者承擔證明該因果關系不存在的證明責任,否則承擔侵權責任。
其次,在肯定被侵權人負有先行證明污染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存在某種程度的因果關系的判決中,被侵權人會因為該初步證明責任而敗訴的情形只占十分之一。因此,承擔因果關系的初步證明責任并不會給被侵權人造成重大不利,而是給予污染者在密不透風的舉證責任倒置規則下以喘息之機,對舉證責任倒置規則進行一些微調。
最后,不承認被侵權人的初步證明責任而直接適用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判決中,所有污染者都無法證明不存在因果關系,而無一例外都承擔損害賠償責任。這一結果也與筆者前文的結論相符,即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基本上使被告無機會翻身,被告敗訴為適用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必然結果。
四、一種解釋的可能性:對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修正
我國《侵權責任法》第66條確立了舉證責任倒置規則,而該規則在適用上容易導致濫訴,對于污染者過于嚴苛,因此有必要加以緩和。筆者在梳理學界觀點之時,發現學界雖然對《侵權責任法》第66條所確立的規則究竟屬于因果關系的推定還是舉證責任倒置有不同意見,但一致認為被侵權人應當就污染行為和損害事實之間存在某種程度的因果關系承擔初步證明責任。
同時,在司法實務中,大多數的法官在面對環境污染侵權糾紛時,也都主張被侵權人應當就污染行為和損害事實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因果關系承擔初步證明責任,在被侵權人成功證明這一點以后,才適用《侵權責任法》第66條所確立的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由污染者負責證明不存在因果關系,并在事實真偽不明時承擔敗訴的風險。可見,由被侵權人承擔初步證明責任也是司法實務中的主流。更為重要的是,肯定被侵權人承擔初步證明責任,并不會給被侵權人帶來很大的舉證負擔,在筆者所整理的案例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被侵權人因為無法完成因果關系的初步證明責任而敗訴。由此可知,肯定被侵權人的初步證明責任,并不會顛覆確立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偏惠于被侵權人的利益格局,而只是在某些特定情形下的微調。另一方面,在否定被侵權人的初步證明責任,徑直適用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案例中,所有污染者都無法證明不存在因果關系,并因此承擔侵權責任。這一現象直接驗證了筆者所說的“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基本上使被告無機會翻身,被告敗訴為適用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必然結果”這一徑直適用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弊端。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筆者以為有必要對《侵權責任法》第66條所確立的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在適用上加以限制,其適用的條件必須是被侵權人已經先行證明污染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存在某種程度的因果關系。也就是說,筆者認為應當為舉證責任倒置設立了一個準入門檻,只有當被侵權人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因果關系存在以后,才開始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由污染者提出反證證明不存在因果關系,否則承擔侵權責任。這樣一來,既符合筆者所分析的《侵權責任法》第66條所確立的舉證責任倒置規則,亦能夠避免直接適用舉證責任倒置規則所可能帶來的濫訴以及對污染者過于嚴苛的弊端。
筆者的這一理解也可能符合全國人大法工委在制定《侵權責任法》第66條時的意圖。全國人大法工委認為《侵權責任法》第66條的規定是“環境污染侵權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倒置,由污染者就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承擔舉證義務;污染者必須提出反證,證明其行為與損害之間沒有因果關系,才能不承擔侵權責任,否則依據本條規定,其應承擔環境污染責任”。[11]從該表述中可以看出,全國人大法工委將該條理解為關于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倒置,由污染者承擔不存在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然而,所謂的舉證責任倒置,其實質是對證明責任一般分配原則的修正。在相關條文對舉證責任做出特殊安排之后,負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所承擔的就是一種“正證”,而非“反證”,因為該要件事實的說服責任已經通過舉證責任倒置這一“舉證責任的分配規范”轉移給了當事人。那么全國人大法工委提出的所謂“污染者必須提出反證,證明其行為與損害之間沒有因果關系,才能不承擔侵權責任”,就不符合舉證責任倒置的性質。因為在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下,被侵權人僅需就污染行為與損害事實承擔舉證責任,無須就因果關系進行舉證,也就是說被侵權人無須就因果關系提出“正證”。既然如此,污染者方面也就無所謂“反證”之說,其所承擔的也只是證明不存在因果關系的“正證”。
對此,可以有兩種理解。第一就是立法者并不區分“因果關系的推定”和“舉證責任倒置”,從立法者認為“污染者必須提出反證”這一點上來看,立法者所認為的“舉證責任倒置”實質上指的是“因果關系的推定”。但是前文已經提到,《侵權責任法》第66條的文字表述并不符合“因果關系推定”的典型表述,同時也不符合“因果關系推定”的形式邏輯結構。而且前文已經提到,“舉證責任倒置”與“因果關系推定”無論是在主觀證明責任還是在客觀證明責任(說服責任)上均有很大不同,不可混為一談。因此,關鍵在于第二種理解,即立法者所確立者確屬“舉證責任倒置”,而且在該“舉證責任倒置”中,污染者也必須提出反證。既然污染者必須提出反證,也就意味著之前被侵權人已經提出了某種程度的證明因果關系存在的“正證”,而該“正證”的提出使得被侵權人完成了自己的證明責任,轉而產生了由污染者負責證明因果關系不存在的說服責任。也就是說,按照該種理解,立法者是在為舉證責任倒置設立了一個準入門檻,只有當被侵權人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因果關系存在以后,才開始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由污染者提出反證證明不存在因果關系,否則承擔侵權責任。而該種理解也正符合筆者在前文中所提出的對《侵權責任法》第66條所確立的舉證責任倒置責任在適用上的修正。
五、結論
在環境污染侵權糾紛中,因果關系的推定與舉證責任倒置都能減輕被侵權人的舉證責任,但各自又有不同的特點。事實上因果關系的推定無須法律規定,而由法官依據經驗法則進行適用,這與我國《侵權責任法》第66條對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設有特殊規定的現狀不相符。法律上因果關系的推定倒是由法律直接規定,但與我國《侵權責任法》第66條的文義不符。從我國《侵權責任法》第66條的文義來看,確立的是舉證責任倒置規則。但是在舉證責任倒置規則中,被侵權人對因果關系不承擔初步證明責任,而徑直由污染者承擔證明因果關系不存在的說服責任,這對污染者過于嚴苛,存在適用上的困境,需要從解釋論上加以緩解。
我國學界雖然對于《侵權責任法》第66條規定的是因果關系推定還是舉證責任倒置有所爭議,但是都認為被侵權人應當承擔初步證明責任。在司法實務中,大多數的判決都認為被侵權人對于因果關系承擔初步證明責任。
因此,確立被侵權人的初步證明責任學界以及司法實務中的共識。但是在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則下,并沒有被侵權人承擔初步證明責任的余地。因此,有必要為《侵權責任法》第66條所確立的舉證責任倒置規則設立一個前置條件,即被侵權人必須在某種程度上證明污染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才能適用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由污染者就該因果關系不存在承擔說服責任。
[1]高圣平.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立法爭點、立法例及經典案例)[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662.
[2]王利明.侵權責任法研究(下卷)[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492;494;495;496.
[3]周友軍.侵權法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390;389.
[4]程嘯.侵權責任法教程(第二版)[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273;274.
[5]楊立新.侵權責任法[M].法律出版社,2011.317;319.
[6]湯維建.論民事訴訟中的舉證責任倒置[J].法律適用,2000(6).
[7]王社坤.環境侵權因果關系舉證責任分配研究[J].河北法學,2011(2).
[8]張新寶.侵權責任法立法研究[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71;38.
[9]李浩.民事證明責任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3.164.
[10]薄曉波.倒置與推定:對我國環境污染侵權中因果關系證明方法的反思[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11).
[11]王勝明,全國人大法工委民法室.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條文解釋與立法背景)[M].,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267.
D913
A
1002-3240(2017)08-0102-07
2017-06-10
葉增勝(1987-),浙江瑞安人,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民商法學博士生,浙江警察學院教師,主要從事民法學研究。
[責任編校:周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