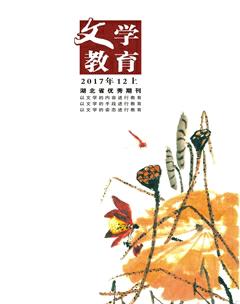語文教學平民化視角下的教學目標設置芻議
內容摘要:以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思想為基礎,當下的語文教學應走向“平民化”,重視“目標”,追求“有得”,崇尚“簡化”。因而在語文教學中,教學目標的設置必須務實務本,注重學生所得;必須有序取舍,進行目標優化。而在其敘寫表達上則需立足于學生“主體”,聚焦“核心”目標,對應“環節”的推進。由此,將“文”“道”各一、一課一得作為價值定位,保障語文教學“平民化”課堂上學生語文能力的習得與提升。
關鍵詞:教學目標 一課一得 語文教學平民化
對語文課程三維目標,教學實踐中呈現出了不同的解讀與取向。均衡論者力圖三者齊頭并進,補缺論者太重其一而忽視其二,難免走進“忙不過來”且“華而不實”的誤區,更有甚者將具體的教學目標與抽象的課程目標等同,課堂教學難逃盲目。
筆者認為,教學目標是課程目標的具體化”,對其的模糊認識會直接導致教學內容的“姿態萬千”,或“空洞無物”,或“包羅萬象”,語文教學“貴族化”趨勢漸盛。語文教學“平民化”“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以此為理論起點,小學語文課堂教學應在目標的定位、優化和敘寫上下功夫以提高閱讀教學的效率。
一.目標定位:務實務本,“文”“道”各得其宜
語文教學“平民化”由蘇州大學王家倫教授提出,其觀點指出,義務教育各學段教學目標應趨向具體化、層遞化,在實施過程中更應注重“語文”化、實際化。由此,我們認為小學語文課堂教學目標的定位首先要務實,即具體實在,看得見、摸得著,不空泛、不浮夸。
1.對三維目標的誤解
由于對三維目標的誤解,一線教師在學目標的設計中,存在這諸如“以教學要求(行為)代替教學目標”和“割裂‘三維目標”等問題,使得目標主體發生錯位,目標導學、導教、導測評功能的實現大打折扣,學習的者目標達能與否更是無法判斷。
當“培養學生熱愛教師事業”“培養學生熱愛生活、關心他人的品質”等空泛、虛化的情感目標屢見不鮮時,過程與方法的落實更是令人憂心。“最有價值的知識是方法的知識”,因此對過程與方法的重視成為了必然。新課程把學習的過程與方法落實到目標體系中,符合學生內在需求、契合語文課程實踐性特點,是其重要理念的體現,也是其創新的標志。而諸如“培養收集、整理社會信息和資料的能力、語言表達能力”“培養學會學習、學會思考、學會合作、學會解決問題的能力”等“能力”傾向的教學目標卻層出不窮。一節語文課如何能做到這樣的“熱愛”、達成這樣的“能力”目標呢?即便如“把握文章寫景的方法”“理清文章的行文思路”“感知文章的語言特點”等看似“很語文”、很“重過程”的目標也是禁不起一個“實”字的衡量的。“寫景的方法”有很多,因景、因時、因文、因人而異,務實就是要以文本為依據,回答清楚“本堂課需要學生把握的是怎樣的寫景方法”這個問題,諸如“行文思路”“結構特點”“敘述手法”“描寫方式”等亦是如此。
2.“文”與“道”目標的落實
與其他學科不同,語文學科在設計教學時,我們手上確也有課程標準,但我們卻看不見成體系的教學內容。教學價值的挖掘、教學內容的選擇全都依賴于教師對教材的二次開發,而這最終必然落實到對教學文本的解讀。如“一百個讀者”與“一百個哈姆雷特”之說,解讀文本必然帶來紛繁收獲,而“授之以漁”的平臺卻只有40分鐘的一節課。少而精,就是避免目標瑣碎、內容冗雜的有效途徑。語文教學“平民化”所提出的“文”“道”各一的價值定位,可作首選。
簡言之,“文”即讀寫聽說能力培養上需要達到的要求,“道”即學生人文培養上需要達到的要求,40分鐘的課堂,兩者得兼,已是成功。小學五年級課文《黃山奇松》是一篇典型的狀物寫景類散文,可作為“樣本”進行教學。其文本的秘妙在于描寫對象的特點與描寫間的巧妙契合,在于對迎客松濃墨重彩的刻畫,在于概括描寫中修辭手法的靈活運用等,這些都可作為課堂教學的主要內容。但作為一個課時,筆者選取“抓住景物特點寫景”作為主要的教學點,將第二課時的教學目標定為:1.通過品味語言材料,初步把握抓住景物特點來寫景的一般方法。2.通過反復朗讀,進一步體會黃山松的“奇”,激發熱愛大自然的情感。課后練筆等不同形式的反饋也充分驗證了“文”“道”各一理念背后“傷十指不如斷一指”的道理。
3.“過程與方法”目標的體現
三維目標是課程的下位概念,其“三維”相互滲透,融為一體。因而,在教學層面,“三維”的互攝與交融是思考的起點。為了體系目標的“清晰”與“可操作”,現行的《語文教學參考用書》上教學要求一般呈現為三點:第一、能正確、流利、有感情地朗讀課文。第二、學會本課()個生字,兩條綠線內的字只識不寫。理解由生字組成的詞語。第三、了解……,感受……,激發……以此為導向,出現了很多將目標列為幾個不同方面的教學設計。且不說這種“單列式”的目標設置是否落實了“清晰”與“可操作”的要求,光就“三維”的踐行程度已大打折扣,而且它還在一定程度上覆蓋了“過程與方法”維度的基本導向。具體來說,多數教學設計是將“通過具體的語言文字材料,感悟……”或“通過自主學習、合作探究、朗讀感悟,領悟作者表達情感的方法”等作為“過程與方法”維度的目標呈現的。顯然,這至少會形成兩方面的缺憾。其一、課時計劃無所適從。其二、教學內容無從取舍。以蘇教版六年級下冊《記金華的雙龍洞》為例,其過程與方法維度的目標是“通過具體的語言文字,了解作者的游覽順序,分清文章主次,學習作者觀察和表達的方法。”那么,課時計劃中,如何將“游覽順序”“文章主次”“觀察方法”“表達方法”等兼而顧之呢?課堂的教學內容如何取舍才能有針對性地為此服務呢?這些問題留給了教師,也留給了亟待提高的課堂效率。
語文教學“平民化”在教學目標層面所倡導的“文道統一”,準確地說,是從我國古代文藝理論中的一對基本范疇——文質關系中延伸而來的。它一方面延續著古代語文教育思想、內容、方法以及教育家理論中的“文道統一”,是一種良好的教學思維導向。另一方面,它尤其重視“文”的目標,將“文”分解、細化,清晰地闡釋了“過程與方法”應然的路徑。筆者將上文《記金華的雙龍洞》教學目標確立為:1、能認、會寫文中的“甸”“鵑”“桐”“臀”“漆”“筍”等生詞。2、通過粗線條閱讀,基本理解游記散文移步換景的結構特點。3、通過文本細讀,深刻體會本文用詞的精準。4、通過反復品位,深刻體會雙龍洞的奇特瑰麗。顯然,前三項為“文”,后一項是“道”。顯性表達而言,“文”的目標中“粗線條的閱讀”“基本理解”“文本細讀”“深刻體會”即是“過程”,“游記散文移步換景的結構特點”“用詞的精妙”即為“方法”;隱性內涵來說,學生“學”的過程得到充分體現。將第二、第三條目標分別落實到第一、第二課時,“道”的目標貫徹始終,課堂教學自然思路明確、得心應手。
二.目標優化:有序取舍,一課一得
有學者在臺灣國小的課堂教學中發現,一篇課文要上5課時,大約一周時間才能上完。每節課解決一個方面的問題,小步子扎實地推進。這就是“一課一得”,也是我們當下的語文課堂必須認真反思的地方。即使沒有那么充裕的課時量,但在有限的兩、三課時中實現“一課一得”還是有可能的。時下多數的語文課堂上,尤其是閱讀教學,內容過多、目標復雜所導致的單課時承載信息量過多、學生負擔過重已是習以為常的現象。優化教學目標,對教學內容進行有序取舍,理應成為思考的起點。
語文教學“平民化”提出了“一課一得”的概念,倡導對可選的教學目標進行篩選和優化,充分利用教材選文本身的序列挖掘教學價值。在這個過程中,根據既定的核心教學目標,對教材文本的價值進行整合重組,合理選擇符合本堂課目標的教學內容。對于該文本其他教學價值的處理則采用暫時的“遺失”與有意的“拾取”相結合的方法,因事因地制宜地進行二次利用。在保障一課一得的同時,也實實在在地完成了對教學內容的二次開發和利用,保障了學生在課堂上的習得。對課堂教學目標進行“一課一得”式的優化,在突破了“三維目標”固化、虛化、泛化等局限的同時,又極其鮮明地凸顯了既定的適于“本課目標”的“三維”。若從“文”,則必求知識與技能的可見可測,過程與方法的有跡可循;若從“道”,必讓情感態度與價值觀內向聚合、外向生發、回歸生活。
此外,在優化目標的過程中,教師要做到“手中有標”“心中有本”“目中有人”。課標是教學目標取舍的基礎和旨歸,語文課程的性質、各學段的不同目標等都應該成為教學目標取舍的依據。例如,同一篇課文《九色鹿》可以作為不同學段的內容進行教學,但所確立的教學目標是不一樣。依《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中年段“能復述敘事性作品的大意,初步感受作品中生動的形象和優美的語言,關心作品中人物的命運和喜怒哀樂,與他人交流自己的閱讀感受”這樣的要求,可以確立目標之一,即能復述課文故事。依高年段“閱讀敘事性作品,了解事件梗概,能簡單描述自己印象最深的場景、人物、細節,說出自己的喜愛、憎惡、崇敬、向往、同情等感受”的要求,則可以將高年段的教學目標確立為:初步把握在故事情節的推進中抓住細節凸顯人物性格和特點的方法。誠然,教學文本的特點以及當前的實際學情也是目標取舍的重要依據。小學四年級連續兩篇文章《我給江主席獻花》和《天安門廣場》都被看作政治性較強、情感教育較為明確的篇目,但妥善取舍、巧妙剩余、適時撿起的做法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幾節課后,學生對于“按照方位順序寫清景物特點”與“文字表達為情感表達服務”這樣的語用層面的習得尤其扎實。
三.目標敘寫:凸顯核心,注重表達
既是“文”“道”各一,就應明確何是“文”,何是“道”,兩者的核心詞分別是什么,如何表述?這就需要我們對三維目標進行切換視角的解讀,將其融合在我們所設定的“核心目標”之中,使之達到到隱含于此、作用于此的綜合性功用。四年級課文《宋慶齡故居的樟樹》第三課時我們設置的“把握借物喻人手法中物與人的內在聯系”這一“核心目標”就包含了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方面的目標。六年級課文《記金華的雙龍洞》第一課時教學目標“通過粗線條閱讀,基本理解游記散文移步換景的結構特點”亦是如此。其二,擁有明確“核心”的目標,才能夠真正對應好“環節”,卷起來是幾句話,展開來是一個“微型教案”。因為它能夠解決“到底寫多少條目標”和“寫到怎樣的程度”等普遍性的問題。筆者認為,目標的表述中,“環節”之于“核心”的觀照就好比地圖之于終點的輔襯。終點清晰,地圖自然詳略有致;終點模糊,地圖也就無路可循。
這就給目標的敘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這一點上,“語文教學平民化”以包含“五要素”的完整句作為表達的基本規范。筆者認為,其“主語”“途徑”“程度”“能力”“知識”的選擇和排列為我們如今略顯混亂的甚至途徑與目的不分的表述方式提供了明確的修正導向。筆者兩次執教四年級課文《但愿人長久》,也兩次敘寫了第二課時的教學目標,感受頗深。第一次的目標敘寫為:1.能正確、流利、有感情地朗讀課文,背誦第四、五、六自然段;2.能通過自主研讀、交流,抓住關鍵詞、句、段,讀悟行文脈絡及內涵,初步感知作者在表現人物心情時的巧妙筆法。3.理解“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意思并能進行較為清晰地表述。4.借力于文本,理解詞的內容,領略詞的意境;在朗讀中逐步體會蘇軾既思念親人,篤于情誼,又通情達理,以理遣情,熱愛生活的豁達情懷。第二次的敘寫為:1.通過品味語言初步掌握文包詩形式文本中文與詩合二為一的方法;2.通過揣摩人物心情的變化,感知“但愿人長久”的豐富內涵。顯然,第二次的敘寫凸顯了“文包詩合二為一的方法”這一核心目標,隨之收獲的是教學環節的清晰明確與環環相扣,更是學生在語文能力上的扎實所得。
此外,權衡“文”與“道”二者本身的“分量”與“差異”后,我們自然會將目標敘寫的立足點放在“文”之所得上。這既是由教材選文在“道”層面的不確定性和深層次性決定的,又有賴于“文”的承載性和滲透性。總體而言,在單課時教學目標的設定中,采用“文”“道”各一的形式,能簡明扼要、突出重點,有助于“平民”學生真正受益于“一課一得”的課堂承諾。
參考文獻
[1]顧明遠.教育大辭典(增訂合編本)[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2]鐘啟泉.課程論[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7.
[3]教育部.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S].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4]王家倫.教材選文一定要名篇嗎[J].中學語文,2009(2)
[作者介紹:張敏芳,蘇州大學在職研究生(在讀),就職于昆山市城北中心小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