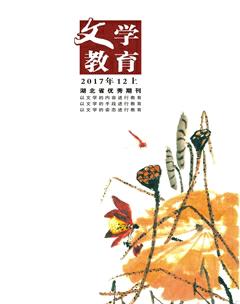論題畫詩在唐寅仕女畫創作中的作用
內容摘要:詩歌和繪畫是兩種不同的藝術門類,但題畫詩的出現,打破了這兩種藝術形式的時空界限,讓中國的詩畫之間聯系更加緊密,創造了一種具有獨特魅力的綜合藝術。唐寅把題畫詩廣泛運用到仕女畫上,增加了畫面的形式美感,闡釋了畫面的含義背景,豐富了作品的文化內涵,展現了作者獨特的情感世界。因此,題畫詩在唐寅仕女畫的創作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唐寅 題畫詩 仕女畫 畫面布局 繪畫內涵
題畫詩的創作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賞析式的題畫詩,由畫的欣賞者(詩人)創作,是對畫家的作品做一些批評和鑒賞,并不題于畫上;一種是創作型的題畫詩,由畫的創作者(畫家)創作,提示作品背景,表達自我情感,它們被題于畫上,成為繪畫的一部分。唐寅仕女畫上的題詩屬于后者。詩人和畫家的雙重身份讓唐寅在仕女畫上題詩的行為耐人尋味,它使詩歌與繪畫之間產生內在的聯系,用詩歌的形式補充畫面的不足,豐富畫面的含義,加強畫面的表達效果。于是題詩與畫面在布局上相呼應,在內容上相聯系,在意境上相交融,并賦予了畫面生動的美感,增添了仕女畫的藝術韻味。題畫詩成為唐寅仕女畫的有機組成部分,是解讀唐寅畫中豐富內涵和隱晦含義的重要渠道,也是打開唐寅情感世界的一把鑰匙。
一.平衡畫面布局
中國畫講究布置意象、經營位置,就是在創作繪畫作品時注重構圖的形式美感。而一首成功的題畫詩,不僅要在文辭內容上與畫面契合,也要在筆法位置上與畫面相得益彰。所謂“畫上題款,各有定位,非可冒昧”,“一圖必有一款題處,題是其處則稱”[1],可見在畫上題詩也要苦心經營,不可隨意。唐寅的仕女畫就是如此,畫上的題畫詩在追求內涵的豐富性的同時,還重視形式的藝術性,平衡好了題詩與畫面之間的關系。
例如唐寅的《秋風紈扇圖》,紙本立軸畫,縱77.1厘米,橫39.3厘米,收藏于上海博物館。畫面中央是一位體態瘦弱、衣著素雅的女子,婷婷玉立在土丘之上。她手執一把紈扇靠在肩上,獨立于深秋之中。秋風吹拂著她的素雅衣裳,泛起道道波痕。女子左上方的土丘上有兩株細竹,在秋風中顯得十分蕭瑟。右下角是一塊奇詭嶙峋的怪石,暈染濃郁。畫面沒有明顯的地點限制,遠景的虛化處理讓人無法確定畫面具體的環境氛圍,尤其是女子背后的留白,仿佛秋風自遠處吹來,給人一種冷寂空曠之感。畫的左上方是唐寅題的兩行字,曰:“秋來紈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傷。請把世情詳細看,大都誰不逐炎涼。晉昌唐寅”,筆法俊逸流暢而又不失穩重。
從構圖角度來看,這首題畫詩的作用十分重要。縱觀全畫,畫面的內容比較精致,墨色濃淡相宜,以寫意為主,占整幅畫的比重不大,且主要位于畫的中部和右下方。換言之,作者在畫的左上方留白較多,這樣就會打破畫面的平衡,右下方太過濃密而左上方略顯空疏。因此,唐寅在左上方題了兩行詩,并且一改傳統寫字習慣,從左往右來書寫,就是為了平衡畫面,避免有頭輕腳重之感,使畫面的結構更加穩定,真可謂是匠心獨運,妙筆生花。而飄逸的字體和浮動的衣物線條又一脈相承,增加畫面的節奏感,防止畫面過于穩定而顯得呆滯刻板,使整幅畫達到了動靜結合的效果,充滿韻律與節奏。從左上方的字,到畫面中央的人,再到右下方的土石植物,這條對角線上的三個有機組成部分,彼此相對獨立又相互聯系,形成了唐寅獨特的構圖方式。
畫上的題詩,不僅讓空間畫面蘊含著時間性,還通過詩歌意象來表情達意,“詩歌作為一種時間藝術的存在,它以運動的方式融入到繪畫的結構中去,增強了繪畫藝術的活力,將詩歌融入到繪畫的空間視覺里,使這幅靜態的繪畫富有生機,使人感受到詩情畫意的審美時空。”[2]因此,語言和圖像的完美結合,打破了時空的界限,使得畫面的意境更加圓融,情感更加真摯。那高超的筆墨、精美的造型,無不體現著作者想要表達的“世態炎涼”之感。
二.闡釋畫面意義
唐寅的仕女畫由于受到時代背景、社會風氣以及畫家本人的人生經歷、性格修養等方面的影響,與一般的美人圖有很大區別,極具唐寅的個人風格特色,包含豐富而又隱晦的情感意蘊,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這是唐寅仕女畫的藝術魅力所在,但也影響了人們對唐寅作品的解讀。尤其是畫面的題材內容和藝術形象豐富多元,而唐寅又喜愛使用視覺典故,這就提高了他的繪畫作品的欣賞門檻。那么怎樣才能全面而準確的理解畫面內容,把握作者通過仕女畫所要表達的情感態度和價值取向,是擺在每個欣賞者面前的難題。幸運的是,由于畫上題詩的內容相對直觀,減少了人們解讀畫面的難度,有利于了解畫面之中的隱藏的復雜含義,是分析唐寅仕女畫的重要途徑。
以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李端端圖》為例,這幅立軸畫紙本設色,筆法精妙,墨色雅麗。畫面的內容是這樣的:在兩面對折且帶有山水畫的屏風所形成的半封閉空間內,有五位人物,斜坐在畫面中間的儒雅文人,頭戴東坡巾,留八字胡,手持書卷;文人的右邊有兩位女性,好似兩位侍女,立于書桌兩側,桌上擺有一把錦囊包裹的古琴以及筆墨書卷。左邊也是兩位女性,一位手里拿著白牡丹花,身材窈窕、亭亭玉立。她衣著素雅、氣質不凡,應該是畫中主要的女性角色,而位于她左下方背面而立的女性應該是她的侍女。五人位置以屏風對折線為界大致分為兩部分,又因為文士與牡丹女子位于畫面中間且二人各自位于兩面屏風中間,因此這五人分別以文人和牡丹女子為中心。
雖然這幅畫的內容很清晰,但只看畫面卻不能讓人明白其中所蘊藏的含義,因此想要讀懂這幅《李端端圖》,還是要從畫上的題詩入手。畫的右上角有詩曰:“善和坊里李端端,信是能行白牡丹。誰信揚州金滿市,胭脂價到屬窮酸。”這首詩包含了豐富的內容。首先,首句“李端端”三個字點出了畫中所包含的視覺典故。這幅畫取材于唐代文人范攄的筆記小說《云溪友議》,描繪的是唐代名妓李端端和狂士崔涯之間的故事。其次,“李端端”與“白牡丹”暗示了這幅畫的真正主角。看似位置最顯眼并且形象最高大的崔涯是畫中的主角,但事實上這幅畫之所以被稱作《李端端圖》,主要還是因為詩歌的內容描寫的是妓女李端端,這就提醒我們她才是畫家著力描繪的主要形象,這一點還可以通過畫中人物的眼神交流來得到驗證。最后,詩中的“白牡丹”、“窮酸”暗含了唐寅的情感態度和價值取向。“白牡丹”喻指的是李端端,唐寅用以贊美她艷麗的容貌和高潔的品格。“窮酸”諷刺的是狂生崔涯,唐寅不滿他肆意侮辱社會底層女性的行為,譏諷他一介“窮酸”文人卻自視甚高。
三.豐富畫面內涵
畫家在畫上題詩,詩的內容就要與繪畫的內容密切相關。畫家一般是從畫面內容出發,在詩中或是表達自己對人生際遇的感慨,或是闡述自己的創作理念,或是表達與繪畫藝術相關的意見和看法。而詩與畫的互動結合,也提升了繪畫作品的藝術內涵和價值,讓原本屬于畫匠所為的繪畫藝術變成文人手中的詩書畫結合的綜合藝術。尤其是仕女畫,自唐代成熟以后便在畫壇逐漸低沉,不再是文人畫家創作的主流。而唐寅在仕女畫上大量題詩,不僅是開辟了仕女畫創作的新天地,也賦予了仕女畫深刻的意蘊。我們可以通過把唐寅的《仿韓熙載夜宴圖》和顧閎中的原畫《韓熙載夜宴圖》做對比,來分析題畫詩對提升繪畫作品內涵的作用。
據《宣和畫譜》記載,南唐后主李煜猜忌大臣韓熙載,“乃命閎中夜至其第,窺竊之,日識心記,圖繪以上之。故世有《韓熙載夜宴圖》。”[3]這幅作品技法高超,內容豐富,深受后世畫家喜愛,臨摹者眾多。唐寅也摹寫了一幅《仿韓熙載夜宴圖》,并在畫上題了兩首詩,一是“身當釣局乏魚羹,預給長勞借水衡。費盡千金收艷粉,如何不學耿先生。”一是“梳成鴨鬢演新歌,院院燒燈擁翠娥。瀟灑心情誰得似,灞橋風雪鄭元和。”唐寅的臨摹并不是亦步亦趨的仿造,而是在尊重原作的基礎上,加入了自己的畫風。例如,他改變了原畫的順序和細節內容,畫中的裝飾物品也更有明代的特色。相比于原畫的典雅沉靜,唐寅的用色更加艷麗輕快,世俗性更加明顯。二者最大的不同,也最有唐寅的特色的部分,便是在畫上題寫的這兩首詩。
唐寅在這兩首題畫詩中運用了一些典故,詩中“如何不學耿先生”指的是南唐女道士,她通曉鬼魅異術,糊弄權貴。“灞橋風雪鄭元和”是指唐傳奇《李娃傳》里的書生鄭生,他為博得名妓李娃的歡心而散盡千金。唐寅在題詩中用了“耿先生”和“鄭元和”這兩個典故,意在表達他對韓熙載的自污行為的不贊同。在唐寅看來,與其這樣委曲求全,不如真的不問世事、及時行樂,以酒色自娛,讓自己從權力斗爭中獲得解脫。這也是為什么唐寅在畫中舍棄傳達韓熙載內心的憂慮,而著重展現他縱情享樂的歌舞生活。這兩首題畫詩實際上暗示了唐寅的態度傾向,是對畫面內容做了一次語言化的詮釋。如此一來,這幅著名的繪畫作品就被唐寅重新進行演繹,賦予了新的含義,同時也體現了唐寅的生活態度,間接反映了唐寅的精神世界。
顧閎中的原畫上并沒有文字,題跋都是后人加上的。雖然這是一幅非常精彩的藝術作品,畫面甚至表現出了韓熙載那歡快表面下隱藏著的濃濃憂慮,但畫中并沒有體現出畫家顧閎中自己的創作意識,而它所蘊含的深刻思想都得益于后人對它的解讀,是在賞析中賦予了它復雜的藝術內涵。說到底,這只不過是一幅精彩的“間諜畫”而已。唐寅的仿畫則不同,如果說在繪畫技巧層面,二人的作品旗鼓相當、各有千秋,那么唐寅畫上的兩首題畫詩就從內涵上提高了這幅臨摹的作品的審美價值和藝術成就,使它從畫匠之作晉升為文人精品。
四.傳達獨特情感
唐寅出身于商賈之家,從小接觸三教九流之人,思想較為開放。他雖然才高八斗,但身世坎坷、命途多舛。尤其是陷于科場舞弊和藩王造反兩件禍事,雖然幸免于難,但終究為主流社會所鄙夷,這造就了他特立獨行的精神氣質和游戲人間的處事態度。唐寅經常通過創作仕女畫,來對一些歷史上的人物或事件表達自己獨特的情感態度。這些情感態度是他在人生逆境中慢慢形成的,與社會主流觀點截然相反,有些甚至是離經叛道的。由于視覺藝術與語言藝術的不同,唐寅的獨特情感價值隱匿于畫面之中,并通過題畫詩展現在欣賞者面前。
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陶谷贈詞圖》描繪的是五代后周文人陶谷出使南唐時所發生的一件風流軼事。據史書記載,陶谷出使南唐后,自恃是上國來使,態度驕傲蠻橫。南唐重臣韓熙載使計讓妓女秦弱蘭誘惑他,成就一夕歡好。陶谷十分得意,寫了一首《春光好》贈給秦弱蘭。之后南唐國主宴請陶谷,請出秦弱蘭歌唱陶谷寫的艷詞,讓他狼狽不堪,十分羞愧。[4]畫中的情景正定格在陶谷聽秦弱蘭彈琴唱曲的一瞬,陶秦二人相對坐于樹下,被奇石和秋葵包圍著。二人背后皆立有屏風,屏風上畫著精美的山石草木人物繪畫。陶谷坐于左側榻上,身體左邊放著紙筆用具,右邊放著酒具,既顯示了他作為文人的矜持,又與畫面左下角溫酒的童子一起暗示了宴飲的場景。秦弱蘭位于畫面右側,坐在圓凳之上,左手執琵琶,右手彈琴,姿勢優雅嫻靜。二人中間有一精美燭臺,上面燃著一根紅燭,說明畫中的場景發生在夜晚,并與周圍的草木樹石一起烘托出環境的幽靜雅致。
唐寅的這幅作品創作的十分“滿”,只在畫上右側留了一段空白,題了一首七言絕句。詩曰:“一宿姻緣逆旅中,短詞聊以識泥鴻。當時我作陶承旨,何必尊前面發紅。”詩的內容很簡單,但里面傳達出來的情感態度卻很大膽。前兩句描寫的是陶秦二人的一夜姻緣,后兩句則是唐寅對此事的評價,表達了他獨特的見解。他“并非站在儒家衛道士的角度,盡譴陶谷之非,而是……一種暢飲生命,游戲人間的態度”[5]。反過來再看此畫,就會發現陶谷全神貫注的聽琴形象其實就表明了唐寅對這件事所持的看法,這與題畫詩中所表達的價值取向是一致的,都來自于唐寅在歷經風雨后所形成的對社會的批判、對人性的思索以及對自我的反省。而唐寅之所以喜歡在題畫詩中發表議論,表達見解,也是為了彌補視覺畫面難以直接傳達復雜情感的不足。
五.結語
唐寅的仕女畫內容豐富、意蘊深刻,包含著唐寅的人生感悟和情感態度,因此欣賞者對繪畫作品的解讀也就必然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而題畫詩的出現,既明確了畫面所表現的內涵,幫助欣賞者解讀繪畫,也限制了人們對藝術作品的多元化理解,甚至可能會妨礙人們理解唐寅的作品。但總的來說,題畫詩在唐寅的仕女畫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它在平衡畫面布局,闡釋畫面意義,豐富畫面內涵,傳達獨特情感等方面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唐寅仕女畫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人們分析唐寅仕女畫必不可少的環節要素。
參考文獻
[1]周積寅.中國畫論輯要[M].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5:559,562
[2]王丹青.試析明代畫家唐寅仕女畫中的詩與畫互文性現象[D].福建師范大學,2016.
[3]潘運告.中國書畫論叢書·宣和畫譜·卷七[M].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2:151
[4]文瑩.玉壺清話·卷四[M].鄭世剛、楊立揚點校,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4:41-42
[5]朱良志.論唐寅的“視覺典故”[J]北京大學學報,2012(02).
基金項目:安徽師范大學研究生科研創新與實踐項目(2017cxsj008)。
(作者介紹:李凱,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研究生,藝術學理論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