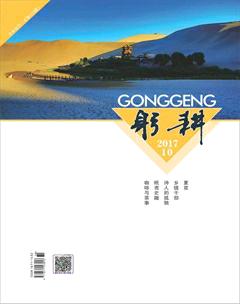詩圣的還鄉路
翟傳海
公元763年春天,由于“安史之亂”而漂泊劍門外五個年頭的杜甫,突然聽說官軍收復了薊北,喜極而泣,不能自抑,揮筆寫下了流傳千古的妙詩佳句——《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劍門關外忽然聽說官軍收復薊北,乍一聽到止不住的淚水灑滿了衣裳。回頭看妻兒的愁容不知去了何方,胡亂收拾著詩書不由得欣喜若狂。白日里引吭高歌而且須縱情飲酒,春光正好伴我返回那久別的故鄉。立即動身穿過巴峽再穿過巫峽,然后經過襄陽就能直接奔到家鄉——東都洛陽。
因“安史之亂”而四處流浪的杜甫,無時不期望著能夠平息叛亂,早日歸家。詩人用了“忽傳”、“初聞”、“卻看”、“漫卷”四個連續動作,把驚喜心情有表達得淋漓盡致。而在“即從”、“穿”、“便下”、“向”這四個富有動感節奏的描述中,似乎看到詩人已經穿過巴峽、巫峽,路過襄陽、洛陽,馬上就回到了夢寐以求的家鄉!
這是窮困潦倒、顛沛流離、“餓走半九州”的詩人,生平一千四百多首詩中第一首快詩,也應該是詩人一生唯一的一首最開心的詩。其歡快和狂歡躍然紙上,就連我們每位讀者也無不隨之高興和歡快。
然而,詩人的狂歡只是曇花一現,空喜一場。國內的混亂局面并沒有隨著河南河北的收復而平定,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在成都叛變,蜀中道路也被阻隔,致使他不得不流亡于東川梓州(四川三臺縣)、閬州(四川南充)、綿州(四川綿陽)及漢州(四川廣漢)等地。這期間他“三年奔走空皮骨”,為了生計他是:“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后。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
七六四年六月,他被成都尹兼劍南節度使嚴武推薦為節度使府中的參謀、檢校工員外郎(節度使府中下屬部門的代理副長官)。在成都節度使幕府中住了幾個月,因不慣于“當面輸心背面笑”的幕府生活,加之他的身體難以支持(早年就有肺病、瘧疾,這時又新添了風痹),不得不辭官重回草堂。永泰元年(765年)四月,嚴武忽然死去,杜甫失去憑依,不得不在五月里率領家人離開草堂,乘舟東下。
九月到達云安(四川云陽),因一路上感受潮氣,肺病和風痹發作不能前進,直到次年暮春病勢減輕,才遷往夔州(重慶奉節)。在夔州山坡上架起簡陋的房屋,租得一些公田耕種。居住未滿兩年(中間幾度遷移),他的健康情況越來越壞,瘧疾、肺病、風痹、糖尿病等不斷纏繞著他。因為夔州氣候惡劣,朋友稀少,便在大歷三年(768年)正月起程出峽,三月到江陵。他本想北歸洛陽,又因河南兵亂,交通阻隔,不能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生活一天比一天惡劣,身體一天不勝一天。耳朵聾了,和他人談話須要寫在紙上;右臂偏枯,寫信須兒子代書。
在江陵生活難以為繼,晚秋時又移居江陵以南的公安縣。沒有居住多久公安也發生了變亂,他不得不乘船到了岳州(岳陽)。隨后又從岳州乘船到衡陽,投友不成到處碰壁,在陸地上再也沒有安身的處所,此后的一年半船就是他的家。大歷四年冬天,寒流侵襲長沙,大雪下得家家灶冷,戶戶衣單。杜甫以船為家停泊在湘江岸邊,從秋到冬已經四個多月了。
之后,他計劃南下郴州(其舅父崔偉在郴州),溯郴水入耒陽縣(衡陽盆地南)境,遇江水大漲停泊在方田驛(今湖南省耒陽市),曾五天得不到食物。耒陽縣令聶某聞之,曾給他送些酒肉。待水落,聶縣令派人尋找杜甫,卻再也找不到杜甫的蹤跡,他以為杜甫必定是在水漲時被大水淹死了,就在耒陽縣北為他建了一座空墳。事實上,杜甫被洪水阻著不能南下郴州,想北上沿漢水回長安,但貧窮與疾病已使他沒有走出湘江的能力了。不久,偉大的詩圣杜甫在“烏幾重重縛,鶉衣寸寸針”的艱難困境中,在“轉蓬憂悄悄,行藥病涔涔”的悲慘境況下,死在了長沙與岳陽之間湘江上漂浮的小船上。那是大歷五年(770年)的冬天,他年僅59歲。
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喜欲狂殆盡了,還鄉夢破滅了。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他熱愛生活,熱愛人民,熱愛祖國的大好河山。由于他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寫出許多反映與批判現實的、不朽的詩篇。他嫉惡如仇,對朝廷的腐敗、社會生活中的黑暗現象都給予批評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著為解救人民的苦難甘愿自我犧牲。然而,寫詩一千四百余首的一代詩圣,最終活活困死在了難于上青天的還鄉之路。
杜甫的悲劇是仰慕他的人心中永遠的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