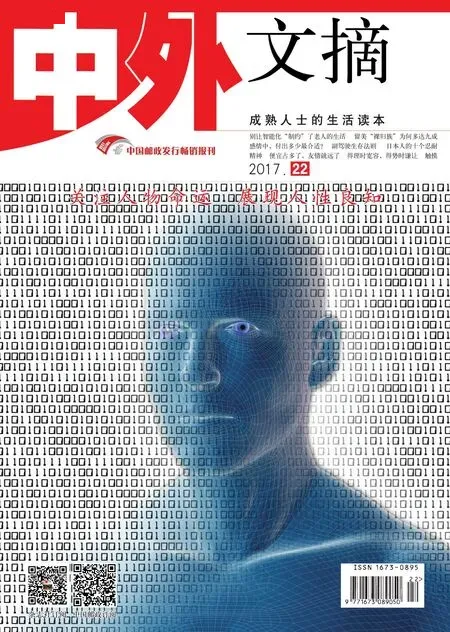觸 摸
□ 張立新
觸 摸
□ 張立新

我羨慕那些有家譜的人,他們可以在紙頁上觸摸先祖,能夠明了自己的來路。我家沒有家譜,家族的記憶只能追溯至我的祖父。父親的記憶像一只漏了底的碗,我曾祖父之前的雨水,他已經盛不住了。
更可怕的是,我祖父的印跡,如今也只剩一些片段。
父親講過若干關于祖父的小事,像電影一般。天剛蒙蒙亮,小巷里傳出幾聲狗吠、幾聲雞鳴,月亮若隱若現,懸在頭頂。一位讀書人,頭戴氈帽,身穿粗布襖,挑著擔,低頭疾行。他走到街上,放下擔子,沒多久,便有人圍了過來。擔子里全是粽子,還是熱的。糯米粽,粒粒晶瑩。解開粽葉,蘸少許蜂蜜,拿一支竹片叉了,輕咬一口,黏而韌,香甜可口。讀書人臉皮薄,覺得賣粽子不該是自己干的活兒,好在一擔粽子半天不到就賣光了。旁邊有人說:“粽子張,今天生意好啊。”讀書人回過頭去含糊答應著,摸出煙鍋,填滿莫合煙葉,點燃,吞吐。
這樣的場景,在父親一次又一次的訴說中,閃過我腦海很多次了。吃粽子的竹片還在,銅質的煙鍋也在,快一個世紀了,這些物件,老得像是傳說。
這位賣粽子的讀書人,就是我的祖父。
當年祖父、祖母都抽大煙,后來迫于生計,兩個人才先后戒了煙,改賣粽子,還闖出了“粽子張”的名頭,這一步邁得確實艱難而沉重。抽大煙在當時不算新鮮事,很多人家都有人抽。當時的大煙不純,戒起來也不難。在祖父心目中,或許賣粽子比戒大煙難多了。這個猜想在我母親那里得到了印證。母親說:“你爺爺當年,讓戒大煙很爽快,賣粽子一事卻猶豫了很久。”
從此,膽小、靦腆,被迫以賣粽子為生的讀書人,就是我對爺爺的全部印象。
沒想到的是,父親偶爾聽說,我家巷子里的一位鄰居竟然收藏著我祖父的一幅字。這個消息讓我欣喜若狂,仿佛由此能夠觸摸到祖父的脈搏。于是,幾番溝通后,一個黃昏,我陪著父親,敲開了鄰居家的大門。
“來了?”
“來了。我們來瞅瞅那幅字。”
“好,稍等啊。”
鄰家大伯慈眉善目,已經八旬開外。他顫顫巍巍、小心翼翼地從一個柜子里摸出一張紙,遞了過來。
我小心地展開,密密麻麻的小楷,工整圓潤,內斂秀美,紙頁已經有些發黃。是一份房屋契約,看落款,時間是“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代筆人是“張竭誠”。常說字如其人,從祖父的字體中能看出他的內斂和謙遜。我久久注視著契約,仿佛觸摸到祖父隔空伸出的手。
我忽然覺得,這張房契不能這么看過就算了。于是,我趕緊掏出手機,恭敬地拍了幾張照片,才將這紙疊好,還給鄰家大伯,然后告辭。
回家路上,父親說,祖父能寫會畫,還手巧,所繪的工筆人物栩栩如生,還能扎各種樣式的風箏,吃粽子的竹片也都是他親手刻、磨而成的。父親至今保存著一個竹片,他拿竹片包肉餡餃子的時候,肯定能夠觸摸到祖父的體溫。
我的手機里從此一直保留著祖父寫的那張房契的照片,像保留著家族的血脈。每當看到它,我就感覺是在和祖父隔空擁抱,用心靈對話。
(摘自《讀者·原創版》201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