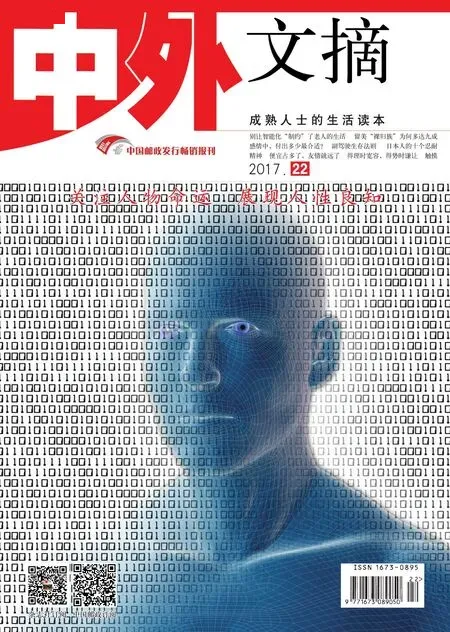墻邊愛情
□ 李金宇
墻邊愛情
□ 李金宇
何以墻邊的愛情如此之多呢?究其原因,墻在古人的筆下似乎成了一個矛盾的象征體,既是屏障,又是橋梁

古人的愛情故事常讓我們遙想揣測,許多愛情的端倪竟是在墻邊發生的。
白仁甫的《墻頭馬上》寫裴少俊和李千金的戀愛是在墻頭一見,互生愛慕。《王嬌鸞百年長恨》里,嬌鸞在后花園打秋千,被周延章于墻頭窺見,彼此傾心。皇甫枚《三水小牘》中寫步飛煙和趙象一見鐘情。趙象在墻縫里窺見飛煙,頓時“神氣俱喪,廢寢忘食”,托人傳情。一墻之隔,園內園外,因窺而喜歡,因見而生情。相識離不開墻,男女的表白、互訴衷腸也常選擇在墻邊。王實甫《西廂記》里,崔鶯鶯與張生,在隔墻酬韻中,傳遞愛慕之情;孫傳鋕《軟郵筒》里,公子郎生與小姐青霞,隔著墻,在和詩唱吟中,暗通情愫。
上面所舉,如果還只限于男女愛情的發微,那么,感情升溫后,就不再是隔墻而“窺”、隔墻而“談”了,而是要跨過墻去。《詩經》里的將仲子開了“跳墻”的先河,“將仲子兮,無逾我墻,無折我樹桑……將仲子兮,無逾我園,無折我樹檀”。這以后的墻,就常常成了引導人們走向情愛的踏板。元代無名氏的《碧桃花》里,張道南因追鸚鵡而跳墻入園,從而看見了意中人徐碧桃。《金瓶梅》第十三回里“李瓶姐隔墻密約”。《鐘情麗集》中,辜生約會瑜娘,也是“至更深夜靜,生遂逾垣而入”。墻在《聊齋》里,幾乎成了男女相悅傳情的鵲橋,“相如坐月下,忽見東鄰女自墻上來窺”(《紅玉》);“南指曰:夜以花梯度墻,四面紅窗者,即妾居也”(《葛巾》);“忽一女子逾垣來,笑曰:秀才何思之深”(《胡四姐》)。
墻,現實中原是用來遮蔽、阻隔的,是一種制止他人進入的藩籬,但在古典小說、戲曲里,卻成了傳情達意的好地方。那么,墻邊的愛情在現實中真會上演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特別是南宋之后,“設男女之大防”,是統治者、道學家和“良善人家”的首要之事,男女相見都很難,更何況還被高墻所阻。
而在文學作品中,何以墻邊的愛情如此之多呢?究其原因,墻在古人的筆下似乎成了一個矛盾的象征體,既是屏障,又是橋梁。所謂屏障,因為那時男女授受不親。墻內是自閉、禁錮之所,墻外卻是爛漫、自由的天地,如《牡丹亭》里杜麗娘所唱:“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墻,隔開的是身體,隔不開的卻是少男少女情竇初開、向往愛情的心。
說它是橋梁,是因為世間就有這么一個悖論:越是壓抑,就越要反抗。你道高墻鎖春深,我卻偏要在墻邊談戀愛;你道高墻可以限制身心,隔開自由,我卻偏要抬腳過去談情說愛。
因為現實中缺乏,才倍感珍惜,才會激發小說家、戲曲家縱情抒寫,在替代里滿足,在滿足中渴望。
(摘自《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