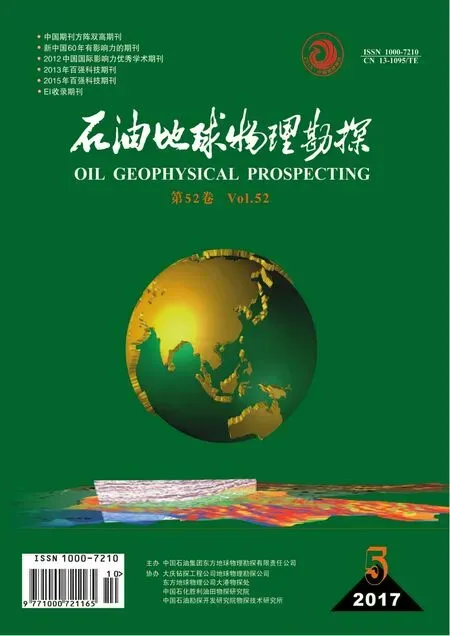微地震地面監測系統的優化設計
余洋洋 梁春濤* 康 亮 尹 陳 巫芙蓉
(①成都理工大學地球勘探與信息技術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四川成都 610059;②中國石油川慶鉆探工程公司地球物理勘探公司,四川成都 610213)
·微地震·
微地震地面監測系統的優化設計
余洋洋①梁春濤*①康 亮②尹 陳②巫芙蓉②
(①成都理工大學地球勘探與信息技術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四川成都 610059;②中國石油川慶鉆探工程公司地球物理勘探公司,四川成都 610213)
余洋洋,梁春濤,康亮,尹陳,巫芙蓉.微地震地面監測系統的優化設計.石油地球物理勘探,2017,52(5):974-983.
在水力壓裂微地震定位中,監測系統的選取直接決定了定位的效果,并最終影響對壓裂效果的評估。采用震源掃描算法對合成的地震信號進行定位以評估不同監測系統的定位效果。通過測試不同的檢波器布設模式、布設范圍以及布設間距對不同深度的微震事件的定位效果,得到了地面監測系統優化設計的一些基本原則:檢波器數目基本相同時,星狀系統優于網狀系統;在一定范圍內,適當增大檢波器布設范圍,增加接收線數,增大檢波器間距,可以在節約成本的基礎上得到較好的定位效果;監測系統布設范圍的半徑,應該與震源的深度相當,或略大于震源深度;若已知震源分布的大致范圍,監測系統的檢波器應該側重于該范圍布設等。
微地震定位 震源掃描算法 地面監測系統
1 引言
微地震監測是目前儲層壓裂中最精確、最及時、信息最豐富的監測手段之一[1],而監測系統的空間布置是影響定位效果及監測效果的關鍵性因素。根據微地震監測檢波器的布設方式,微地震監測可以分為井中監測和地面監測[2]。與井中監測相比,地面監測雖然有信號衰減嚴重、信噪比低的缺點,但其具有簡單、經濟、適應性強和數據量大的優勢,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應用[3-5]。在“十三·五”低油價新常態下,物探業務更是面臨降本增效的新要求及發展效益科技的新挑戰[6]。因此,通過對地面監測系統的優化設計,在經濟、高效的基礎上提高定位的精度,對低滲油氣資源的開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自1978年Hardy等[7]成功運用聲發射技術進行地下水壓裂裂縫定位之后,微地震監測技術也獲得了長足發展。王維波等[8]對網格狀、環狀和星狀等站點分布方式進行了討論,得出了站點數目相同時定位效果與分布結構無關的結論;李雪等[9]對地面監測和井中監測以及陣列式監測技術做了簡要說明;宋維琪等[10,11]對微地震定位方法和波形反演進行了討論; Gajewski1等[12]分析了不同速度模型對定位效果的影響;王晨龍等[13]討論了介質擾動和不同檢波器分量對定位效果的影響。
本文從檢波器的布設方式、布設范圍以及布設間距等方面討論地面監測系統對定位效果(定位精度及能定位事件數量)的影響,總結監測系統的設計原則,以期在保證定位精度的同時經濟、高效地實現對壓裂的監測。
2 理論方法
微地震定位方法一般可分為:S波和P波旅行時差法、震源空間掃描法、相對旅行時法、逆時偏移成像法等[14]。S波和P波旅行時差法一般用于S波和P波初至都比較清晰的情況,比如天然微地震監測和井中微地震監測[15];震源空間掃描法一般用于地震信號非常微弱的情況,比如俯沖板塊的地幔地震定位以及壓裂監測中的地面微地震監測定位[16];而相對定位法[17,18]是利用兩個事件的相對旅行時,在其中一個事件位置已知的情況下,對另一事件進行定位,該方法常作為一種輔助方法;逆時偏移成像法[19]正在發展中,且計算量較大。
針對地面微地震監測數據信噪比低、事件拾取困難以及數據量大的特點,本文采用震源掃描算法(Source -Scanning Algorithm, SSA)[20]進行震源定位。
該方法不需要對事件的初至進行拾取,僅利用相對振幅和旅行時等波形數據,便可監測給定的時空范圍內是否有事件發生,更適用于大量監測臺站的大型地面微地震監測系統,其原理如圖1所示。

圖1 地面監測系統和震源空間示意圖
將射孔附近區域分割成若干網格點,假定該空間內的每一個網格點均為一個虛擬震源,網格點η在τ時刻發震,由N個臺站記錄。在速度模型已知的情況下,通過射線追蹤計算虛擬震源到臺站的旅行時,按照式(1)對波形資料做動校正然后疊加平均。
(1)
式中:un為觀測地震記錄;N為臺站總數;τ為虛擬震源點η的發震時刻;tη n為從點η到臺站n的旅行時。該過程的實質是以P波為標準進行動校正,將波形資料從觀測時空域轉換到震源時空域(圖2)。經過處理后P波的疊加能量會增強,S波和其他轉換波的疊加能量會減弱,可以通過P波進行事件的識別。即使波場較為復雜,只要信噪比相對較高,也能得到較好的定位結果(圖2)。
圖2a縱坐標為觀測時間,每一道對應一個臺站的記錄;圖2b縱坐標為發震時間,每一道對應一個虛擬震源的疊加平均記錄。在圖2b的3.5s附近有一個較弱的事件,而在圖2a的4s附近并未見其對應的波形,證明了震源掃描算法拾取低信噪比事件的能力。
然后,在震源時空域中,計算每個采樣點的“亮度”函數
R=STA/LTA
(2)
式中:R體現信號相對于背景噪聲的均方根振幅之比,稱為“亮度”;STA為短時窗平均值,反映微地震信號的均方根振幅;LTA為長時窗平均值,反映背景噪聲的均方根振幅。一定時間內,空間中“亮度”函數最大的采樣點所在的虛擬震源點,被視為該時間段內震源最可能發生的位置[21]。本文均選取R≥3.0作為識別微地震事件的標準。

圖2 觀測時空域道集(a)與震源時空域道集(b)的對比
3 數據合成
震源掃描方法定位效果與速度模型、波場特征、振幅、相位等問題密切相關,而本文的研究重點是監測系統的優化設計原則。因此,為了減弱速度模型與震源因素對定位結果的影響,采用地表無起伏均勻各向同性介質(圖3a)和水平均勻層狀介質(圖3b)速度模型對位于(0,0,3000m)處的ISO型震源[22]進行正演模擬和微地震定位分析,其中均勻介質模型速度為水平層狀介質模型的等效速度(4500m/s)。模型離散化為400×400×300的網格,間隔為15m。用任意曲線坐標有限差分算法及其配套程序[23]模擬微地震事件,主頻為30Hz,圖3c和圖3d分別為均勻模型和層狀模型對應的波場快照。采用圖4a的星狀監測系統,分別使用均勻模型和層狀模型合成地震記錄,添加隨機噪聲,形成信噪比SNR從0.02到1.0變化的合成數據(0.02到0.1間隔為0.02,0.1到1.0間隔為0.05),其中SNR定義為地震記錄最大振幅所在道的信號時窗內的均方根振幅與隨機噪聲的均方根振幅之比。圖3e和圖3f分別為不同SNR合成數據定位結果的水平誤差(dh)和垂向誤差(dz),當SNR<0.15時沒有對應的誤差值,說明當SNR<0.15時得不到定位結果。盡管兩種介質模型的波場有明顯差異,采用等效速度進行定位后,兩者的定位效果差異并不大。當SNR較高時,兩種介質模型的定位誤差完全一樣;當SNR較小時,層狀介質的定位誤差有所增大。測試表明,對水平均勻層狀介質,用等效速度代替介質速度進行定位有一定的合理性。

圖3 速度模型、正演波場及不同信噪比(SNR)數據定位效果
(a)均勻各向同性介質模型;(b)水平均勻層狀介質模型;(c)均勻模型正演波場快照(t=1.0s,y=0.0); (d)水平層狀模型正演波場快照(t=1.0s,y=0.0);(e)水平定位誤差;(f)垂向定位誤差
4 合成數據定位分析
頁巖氣等非常規資源的埋藏深度范圍一般為2000~3000m[24]。因此,測試震源為分別位于2000、2500和3000m深度的ISO型震源。進行掃描定位時, 假定虛擬震源分布在以理論震源坐標為中心100m范圍內、間距為5m的網格上。
基于簡單的均勻各向同性介質,定位時以P波速度為標準進行動校正處理。從地面監測系統的布設方式,布設范圍以及布設間距等方面討論監測系統對定位效果的影響。
4.1 布設方式分析
地面檢波器的分布方式主要可以分為星狀和網格狀,采用1000個檢波器如圖5的四種布設方式,對深度為2000、2500和3000m的震源進行定位。
圖4a為一典型的星狀地面監測系統示意圖,3000m長的10條接收線均勻分布,接收點距為30m;圖4b為網格狀監測系統Ⅰ,10條接收線均勻分布,接收線距為750m、點距為30m;圖4c為網格狀監測系統 Ⅱ,10條接收線均勻分布,接收線距為1500m、點距為60m; 圖4d為網格狀監測系統Ⅲ,接收線距和點距均為60m。圖5為四種監測系統對不同深度微地震事件的定位誤差對比,若在圖中相應SNR處沒有點,即表示定位程序沒有識別到該事件。

圖4 四種微地震地面監測系統
對于4種監測系統,隨著震源深度的加深,能識別事件的最小SNR均逐步增加,因而得到的事件數目逐步減少。星狀監測系統能識別出的事件數目最多,而網格狀監測系統Ⅱ識別出的事件數目最少。根據地震能量和數量的分布規律,事件能量越小,其數量則會成指數增加。因而,綜合所有深度,從能夠定位的最小事件可以看出,星狀監測系統要優于其他三種系統。
對于網格狀監測系統Ⅲ,小震源距的檢波器分布密集,因而水平誤差較小,而大震源距檢波器較少,因而垂向誤差較大。星狀監測系統的整體誤差最小,而其他監測系統的誤差則要大得多,尤其是垂向誤差。各監測系統中絕大多數事件的橫向誤差小于垂向誤差,尤其是SNR較大的事件,因此以下重點討論垂向誤差。
綜上所述,在檢波器總數目相同的情況下,相較于網格狀布設方式,星狀布設方式的定位效果最好。
4.2 布設范圍分析
通常檢波器布設的范圍越大,得到的信息越豐富,但經濟成本也越高。在實際施工中,由于地形和資金的限制,監測系統的布設范圍是有限的,所以有必要研究布設范圍對定位結果的影響。
將圖4a所示星狀監測系統的接收點距設置為10、20和30m,則監測系統半徑分別為1000、2000和3000m。圖6對比了不同半徑監測系統對不同深度微地震事件定位的垂向誤差(dz)。當監測系統半徑從1000m增大到3000m時,得到的事件個數差異不大,但定位精度逐漸提高。當監測系統的布設范圍遠小于震源深度時,由于沒有遠端檢波器的約束,其定位誤差較大,且很不穩定; 當布設范圍大于或等于震源深度時,其定位的誤差較小,且比較穩定。

圖5 四種監測系統對不同深度微地震事件定位的水平(左)和垂向(右)誤差對比

圖6 不同半徑星狀監測系統對不同深度微地震事件定位效果對比
4.3 布設間距分析
將圖4a所示星狀監測系統的檢波器個數設為1500、線數設為10、檢波點距設為20m,形成星狀監測系統Ⅰ;將圖4a所示星狀監測系統的檢波器個數設為1500、線數設為5、檢波點距設為10m,形成星狀監測系統Ⅱ;將圖4a所示星狀監測系統的檢波器個數設為750、線數設為10、檢波點距設為40m,形成星狀監測系統Ⅲ。圖7對比了不同檢波器間距星狀監測系統對不同深度微地震事件定位效果。由圖可以看出,星狀系統Ⅱ監測到的事件數目最少,且震源越深這種現象越明顯,但定位精度與其他監測系統區別不大,說明方位角的覆蓋范圍影響了定位事件的數目;星狀系統Ⅰ與星狀系統Ⅲ的整體定位效果相差不大。由此可見,接收線數越少,監測到的地震事件越少;在接收線數和布設范圍一致的情況下,適當增大檢波器的間距、減少檢波器個數,定位效果基本不變,但可以降低成本。

圖7 不同檢波器間距星狀監測系統對不同深度微地震事件定位效果對比
4.4 列震源的定位分析
在工業生產中,微地震一般集中分布在壓裂井的附近,觀測系統是否應當側重于震源區域布設?將深度均為2500m 的20個震源排成一列,與x軸垂直相交于x=500m處,在x軸兩側等間隔(30m)分布(圖8)。圖8a星狀監測系統10條接收線均勻分布(方案A),圖8b監測系統10條檢波器側重于震源區域分布(方案B),兩種方案按檢波器個數和間距分為四種情況:檢波器個數Nr=3000,間距為10m;檢波器個數Nr=1500,間距為20m;檢波器個數Nr=1000,間距為30m;檢波器個數Nr=750,間距為40m。圖9~圖11分別對比了兩種布設方案識別出微地震事件數目、水平定位誤差和垂向定位誤差。

圖8 列震源地面監測系統

圖9 列震源兩種地面監測系統方案識別的微地震事件對比

圖10 列震源兩種地面監測系統方案微地震事件水平定位誤差對比

圖11 列震源兩種地面監測系統方案微地震事件垂向定位誤差對比
當SNR>0.35時,采用方案B布設方式,所有的四種情況監測系統都能定位出全部20個震源;而采用方案A布設方式,只有當SNR>0.65時,所有監測系統才能定位出20個震源。至于定位精度,垂向誤差大約是水平誤差的兩倍,兩種布設方案的垂向誤差基本相當,但方案B的平均水平誤差總是小于方案A。
所以,檢波器側重于震源區域分布,能夠有利于在較低信噪比時識別出更多的微地震事件,且能提高水平定位精度。
5 實際監測系統的定位分析
實際工區的噪聲遠比隨機噪聲更復雜。采用四川M工區的實際地面監測系統,震源坐標為x=1500m,y=2000m,深度分別為2000、2500和3000m。添加實際噪聲,將實際監測系統按不同的布設范圍、線數與檢波點距進行重新抽取,得到檢波器約為800個的四種監測系統方案(圖12)。方案Ⅰ監測系統接收線有17條,檢波點距為30m,半徑為3000m;方案Ⅱ監測系統接收線也有17條,檢波點距為20m,半徑為2000m;方案Ⅲ監測系統接收線有9條,檢波點距為10m,半徑為2000m;方案Ⅳ監測系統接收線有17條,檢波點距為10m,半徑為1000m。從方案Ⅰ~方案Ⅳ,檢波器的覆蓋范圍逐漸減小,檢波點距逐漸減小。圖13對比了四種監測方案對不同深度微地震事件的定位效果。

圖12 實際監測系統的4種方案

圖13 實際監測系統4種方案對不同深度微地震事件的定位效果對比
隨著震源深度的增加,所有監測系統識別的地震事件數目逐漸減少,垂向誤差逐漸增大。其中方案Ⅲ對上述現象表現得最為明顯,方案Ⅲ和方案Ⅳ的整體誤差水平也較高; 方案Ⅰ識別的事件數目與方案Ⅱ相仿,但其整體精度卻優于其他監測系統方案。
所以,當檢波器數目一定時,可以適當增大檢波點距,擴大布設范圍,增加監測線數。其中分布范圍是影響定位精度的主要因素,監測線數主要影響識別微地震事件的個數。
6 討論
由以上分析發現,定位效果與監測系統的覆蓋范圍、接收線數、檢波器間距、震源深度及介質速度等均有直接關系。震源與檢波器的幾何關系如圖14所示,H、Z和θ分別表示震中距、震源深度和離源角,介質速度為v,震源到檢波器的旅行時可以表示為
(3)

圖14 震源與檢波器的幾何關系圖
那么由于時間誤差dt所導致的垂向幾何誤差(dz)和水平幾何誤差(dh)分別為
dz=dtvcosθ
(4)
dh=dtvsinθ
(5)
對于相同的時間誤差dt,介質速度與兩個方向的誤差成正比,介質速度越高,其幾何誤差越大。對于單個檢波器,當深度Z不變、震中距H越小時,其θ越小,那么垂向幾何誤差越大,水平幾何誤差越小;當震中距H不變、震源深度Z越小時,其θ越大,那么垂向幾何誤差越小,而水平幾何誤差越大。因此,地面監測系統的布設范圍越大,垂向幾何誤差越小,震源位置越深,垂向幾何誤差越大。所以,適當擴大檢波器的布設范圍,能夠有效抑制垂向幾何誤差。
在實際地面監測系統中,大多數檢波器的震中距都小于震源深度,即H (6) (7) 式中:n表示地面檢波器的總數目;tij表示第i個網格點到地面第j個檢波器的P波旅行時;tcj表示理論震源點到地面第j個檢波器的P波理論旅行時。 針對以上測試,用20個檢波器設計了如圖15所示的三個地面監測系統,其中第1個監測系統(圖15a)的檢波點距較小,布設范圍較小; 第2個監測系統(圖15b)的檢波點距較大,布設范圍較大;第3個監測系統(圖15c)的檢波點距較小,側重于一側分布。計算三種地面監測系統對不同深度(500m和1100m)震源的旅行時殘差的標準差(圖15等值線所示)。 由圖15可以看出,震源越深,旅行時殘差的標準差越發散,其整體旅行時誤差越大。對于同一深度震源而言,改變監測系統方案,主要是水平旅行時誤差發生改變,檢波器布設的范圍越大,其水平旅行時誤差越小。另外第3個監測系統說明了檢波器應該側重于震源區域布設,才能有效減小旅行時誤差。 圖15 三個監測系統及其旅行時殘差的標準差分布 由以上測試和討論,可以得出以下幾點地面監測系統的優化設計原則。 (1)檢波器數目相同時,星狀布設方式的定位效果要優于網格狀,原因是星狀布設方式經濟高效地擴大了檢波器的布設范圍。 (2)若已知震源分布的大致區域,應當增加檢波器在該區域上方的分布密度。 (3)在一定范圍內,適當增大檢波點距、增大檢波器的布設范圍、增加檢波線數,可以在節約成本的前提下得到更好的定位效果。擴大檢波器的布設范圍雖然在一定程度增大了水平幾何誤差,但也能有效減小垂向幾何誤差和水平旅行時誤差,且大部分檢波器的震中距都小于震源深度,誤差主要集中在垂直方向。所以,整體而言,擴大監測系統的布設范圍能夠有效提高定位精度。 (4)監測系統設計應考慮震源深度合理布置。一般來說,水平覆蓋半徑約等于震源深度即可。布設范圍太小,垂直誤差可能會更大;布設范圍太大,則會增加經濟成本。 另外,對于地面監測系統,水平方向的誤差普遍小于垂直方向的誤差,隨著震源深度的增加,能識別的地震事件數目逐漸減少,定位誤差也逐漸增大。 [1] 劉振武,撒利明,巫芙蓉等.中國石油集團非常規油氣微地震監測技術現狀及發展方向.石油地球物理勘探,2013,48(5):843-853. Liu Zhenwu,Sa Liming,Wu Furong et al.Microseismic monitor technology status for unconventional resource E & P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 in CNPC.OGP,2013,48(5):843-853. [2] 張山,劉清林,趙群等.微地震監測技術在油田開發中的應用.石油物探,2002,41(2):226-231. Zhang Shan,Liu Qinglin,Zhao Qun et al.Application of microseismic monitoring technology in development of oil field.GPP,2002,41(2):226-231. [3] Duncan P M,Eisner L.Reservoir characterization using surface microseismic monitoring.Geophysics,2010,75(5):A139-A146. [4] 李會儉,王潤秋,曹思遠等.利用多尺度形態學識別微地震監測中的弱信號.石油地球物理勘探,2015,50(6):1105-1111. Li Huijian,Wang Runqiu,Cao Siyuan et al.Weak signal identification in microseismic monitoring with multi-scale morphology.OGP,2015,50(6):1105-1111. [5] 邵婕,孫成禹,唐杰等.基于字典訓練的小波域稀疏表示微地震去噪方法.石油地球物理勘探,2016,51(2):254-260. Shao Jie,Sun Chengyu,Tang Jie et al.Micro-seismic data denoising based on sparse representations over learned dictionary in the wavelet domain.OGP,2016,51(2):254-260. [6] 撒利明,張瑋,張少華等.中國石油“十二·五”物探技術重大進展及“十三·五”展望.石油地球物理勘探,2016,51(2):404-419. Sa Liming,Zhang Wei,Zhang Shaohua et al.Geophy-sical technology major achievements at CNPC during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and lookout for the Thirteenth Five-Year Plan.OGP,2016,51(2):404-419. [7] Hardy H R.Acoustic Emission/Microseismic Activity.Balkema A A Publishers,2003. [8] 王維波,周瑤琪,春蘭.地面微地震監測SET震源定位特性研究.中國石油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2,36(5):45-55. Wang Weibo,Zhou Yaoqi,Chun Lan.Characteristics of source localization by seismic emission tomography for surface based on microseismic monitoring.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Natural Science Edition),2012,36(5):45-55. [9] 李雪,趙志紅,榮軍委.水力壓裂裂縫微地震監測測試技術與應用.油氣井測試,2012,21(3):43-45. Li Xue,Zhao Zhihong,Rong Junwei.Microseismic monitoring technology of hydraulic fracture and its applications.Well Testing,2012,21(3):43-45. [10] 宋維琪,馮超.微地震有效事件自動識別與定位方法.石油地球物理勘探,2013,48(2):283-288. Song Weiqi,Feng Chao.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microseismic effective events.OGP,2013,48(2):283-288. [11] 宋維琪,高艷珂,朱海偉.地面微地震水平層狀模型波形反演.石油地球物理勘探,2013,48(1):64-70. Song Weiqi,Gao Yanke,Zhu Haiwei.Waveform inversion of horizontal layer model for surface micro-seismic.OGP,2013,48(1):64-70. [12] Gajewski1 D,Sommer K,Vanelle1 C et al.Influence of models on seismic-event localization.Geophysics,2009,74(5):WB55-WB61. [13] 王晨龍,程玖兵,尹陳等.地面與井中觀測條件下的微地震干涉逆時定位算法.地球物理學報,2013,56(9):3184-3196. Wang Chenlong,Cheng Jiubing,Yin Chen et al.Microseismic events location of surface and borehole observation with reverse-time focusing using interfero-metry technique.Acta Geophysica Sinica,2013,56(9):3184-3196. [14] Liang Chuntao,Yu Yangyang,Yang Yihai et al.Joint inversion of source location and focal mechanism of microseismicity.Geophysics,2016,81(2):KS103-KS111. [15] Maxwell S C,Rutledge J,Jones R et al.Petroleum reservoir characterization using down hole microseismic monitoring.Geophysics,2010,75(5):A129-A137. [16] Kao H,Shan S,Dragert H et al.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of seismic tremors in northern Cascadia.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Atmospheres,2006,111(B3):113-132. [17] Eisner L,Abbott D,Barker W B et al.Noise suppression for detection and location of microseismic events using a matched filter.SEG Technical Program Extended Abstracts,2008,27:1431-1435. [18] Kummerow J.Seismic event location using the value of the cro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Geophysics,2010,75(4):MA47-MA52. [19] Gajewski D,Tessmer E.Reverse modelling for seismic event characterization.Geophysical Journal International,2010,163(1):276-284. [20] Kao H,Shan S J.The source-scanning algorithm:mapping the distribution of seismic sources in time and space.Geophysical Journal International,2010,157(2):589-594. [21] 李文軍,陳棋福.用震源掃描算法(SSA)進行微震的定位.地震,2006,26(3):107-115. Li Wenjun,Chen Qifu.Micro-earthquake location by means of source-scanning algorithm.Earthquake,2006,26(3):107-115. [22] 唐杰,方兵,藍陽等.壓裂誘發的微地震震源機制及信號傳播特性.石油地球物理勘探,2015,50(4):643-649. Tang Jie,Fang Bing,Lan Yang et al.Focal mechanism of micro-seismic induced by hydrofracture and its signal propagation characteristics.OGP,2015,50(4):643-649. [23] Zhang W,Chen X F.Traction image method for irre-gular free surface boundaries in finite difference seismic wave simulation.Geophysical Journal International,2006,167(1):337-353. [24] 肖鋼,唐穎.頁巖氣及其勘探開發.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Xiao Gang,Tang Ying.Shale gas and its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Higher Education Press,Beijing,2012. [25] Kidney R L,Zimmer U,Boroumand N.Impact of distance-dependent location dispersion error on interpretation of microseismic event distributions.The Lea-ding Edge,2010,29(3):284-289. (本文編輯:宜明理) 余洋洋 博士研究生,1989年生;2012年畢業于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應用地球物理系,獲得學士學位;2015年畢業于成都理工大學地質工程專業,獲得碩士學位;現在成都理工大學地球物理學院攻讀博士學位,主要從事微地震地面監測與震源機制方面的研究。 1000-7210(2017)05-0974-10 P631 A 10.13810/j.cnki.issn.1000-7210.2017.05.010 *四川省成都市成都理工大學地球勘探與信息技術教育部重點實驗室,610059。Email:liangchuntao12@cdut.cn 本文于2016年2月23日收到,最終修改稿于2017年8月9日收到。 本項研究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41374058,41340009,U1262206)及四川省科技支撐計劃(2015RZ0032)聯合資助。


7 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