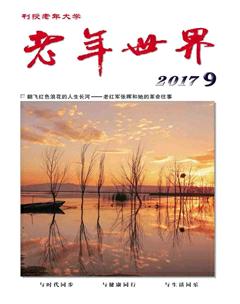翻飛紅色浪花的人生長河
海爾罕
1920年7月,張暉出生于廣西南寧。當時的中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她出生時,恰逢第一次粵桂戰爭爆發。
一
張暉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曾祖父是晚清廣西龍州縣教育局的一名小官吏,父親是南寧測量局的測繪員,姊妹幾人,生活雖稱不上大富大貴,卻也殷實。
在張暉童年的記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家有兩間小房,外屋住著曾祖母,人瘦得皮包骨,里間養著兩頭豬,曾祖母每日忍受尺把深的豬糞的惡臭,而養豬是她唯一的生活來源。當時只有六七歲的張暉不明白曾祖母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處境,只知道曾祖母的丈夫死了,子女們亡的亡,病的病,日子拮據。
離曾祖母住處不遠,是一戶富人家的大宅子,宅子門口,常看到一個和她年齡相仿的女孩遭受打罵。張暉知道那個女孩是“妹仔”(舊時有錢人家雇來役使的女孩子),那時,無業游民的四叔一出現,張暉就悄悄對弟弟妹妹們說:“要緊緊地看好小妹妹,小心被四叔賣掉。”童年的經歷,讓張暉開始思考:這個社會為什么對女人如此不公。
父親勤于苦學,寫得一手漂亮的毛筆字,張暉自小受父親影響,學業優異。等到上中學的年紀,為了給父母減輕負擔,也為了讓弟弟能獲得更好的教育機會,她進入幼兒師范學院學習,學費全免。1935年,張暉在全省幼師畢業班的一百多名畢業生中脫穎而出,在畢業會考中取得第一名的優異成績,成為僅有的兩名進入市幼兒園任職的畢業生之一,每月俸祿15塊大洋。
作為當時南寧市唯一一家幼兒園,能夠入園學習的都是軍閥和富家子第,桂系軍閥白崇禧的孩子也在班上。課堂上,保姆的數量比學生還多。幼兒園園長不思搞好教育,而在于巴結達官顯貴。每到周末,便邀青年女教師進入茶館消遣,暗中安排軍官及富豪從旁觀察,物色姨太太人選。張暉看出園長的意圖,極為反感,不禁想起之前上學時,班上最漂亮的女生被迫嫁給富貴人家作姨太,表面上錦衣玉食,眼中卻常含淚水,身上遍布大大小小新舊傷痕。張暉心里明白,這份工作雖來之不易,卻既不能實踐她的所學,也絕不是她未來的方向。
二
自1932年至1936年,廣西由新桂系軍閥管轄,新桂系決心提高廣西的自治實力以與之抗衡。在一些有識之士的幫助下,廣西的教育事業逐漸發展起來。1933年,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成立,教育廳長雷沛鴻兼任院長。雷沛鴻是中國現代教育史上一位杰出的教育改革家和教育思想家,他聘請了許多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受迫害的知識分子在“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中任職,教育家孫銘勛就在其中。張暉聽到這一消息,毫不猶豫的辭掉工作,進入該院,并且結識了她的馬克思主義啟蒙者——教育家孫銘勛。自此,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種子深植于張暉心中。
孫銘勛是上世紀30年代我國著名的育兒專家,是陶行知先生的杰出弟子,他寫的文章經常見諸于當時的報刊雜志。張暉在讀書期間便閱讀了孫銘勛的許多著文,但是張暉不知道的是,這位享有較高社會知名度的孫老師當時已是一名秘密的共產黨員。作為廣西教育實踐項目的一名負責人,孫銘勛一方面實踐著陶行知先生“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另一方面注重發掘進步青年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張暉在孫銘勛老師的課堂上學習了《大眾哲學》《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等課程,在她的腦海中,馬克思唯物主義辯證法的認識已逐步形成。
1935年秋天,張暉等一批進步青年,在孫銘勛、杭葦等老師的帶領下,在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院長雷沛鴻的支持下,來到了雷沛鴻的家鄉——廣西金頭村,在那里,他們一邊學習馬列主義知識一邊開設幼兒園辦學。張暉在這段時間里快速成長起來,在學習社會發展史的過程中,共產主義理想深深打動了她,在共產主義社會,再不會有曾祖母和無數“妹仔”……張暉的進步,孫銘勛看在眼里。有一天,孫老師抓住機會問她:“假如共產黨就在你身邊,你愿不愿意加入?”張暉早已對共產黨充滿憧憬,自然是滿口答應。孫老師又語重心長地說,“愿意入黨是好事,但是,要問自己兩個問題,第一,怕不怕死,能不能隨時作好為黨犧牲的準備。第二,能不能保守黨的秘密,即便是對自己最親的人,也決不能透漏半點。”
轉眼,寒假到了,一個陰冷的傍晚,在金頭村邊上一座河堤的掩護下,由孫銘勛引導,張暉和另外兩個女生宣誓加入了中國共青團。孫銘勛告訴她們:因為年紀小,你們需要先加入共青團,等日后到了規定的年齡,再轉成黨員。
1936年2月,隨著抗戰形式的日益高漲,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以下簡稱民先隊)在北京成立,這是由中國先進青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立的抗日救國組織。根據中央指示,原共青團團員符合條件的轉為共產黨員,于是,張暉正式成為一名共產黨員。
三
1936年6月,兩廣事變爆發,廣西的新桂系軍閥和廣東的陳濟棠粵系軍閥,利用抗日運動之名義(實際上他們接收過日本的軍援),反抗處心積慮要消滅兩廣軍閥勢力的國民政府中央首領蔣介石,雙方出動高達80萬部隊,擺出決戰的架勢,歷經了三個多月的對峙后,新桂系服從蔣介石政權領導,積極反共,而廣西的共產黨經歷了來自軍閥方面的剿共,加上蔣介石的嚴密圍剿,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為了保存革命力量,不得不北上與共產黨領導的大部隊會合。
1936年年底,張暉和她的同學們兵分兩路,準備北上。其中五人帶著所有人的組織關系,通過南方局,走更安全的水路,經香港北上至上海,再輾轉到蘇區。張暉和她的入黨介紹人楊大姐則經陸路北上。楊大姐是軍需官的女兒,她的母親是姨太太,楊大姐作通了母親的思想工作,變賣了自己的嫁妝,又在同學和親戚中四處籌資募捐,最終湊齊了兩人的路費。上路之前,鑒于青年知識分子是國民黨重點盤查對象,匆忙上路有極大風險,黨組織又聯系到一名準備去往延安八路軍總部的攝影師,讓他們三人在行程途中假扮成一家三口,既便于掩護身份又方便互相照應。張暉因為身材瘦小,扮作女兒,楊大姐雖然只大了兩歲,也只好佯裝母親。因為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張暉無從知曉這位攝影師的真實身份,事后回憶,當時的情形更像是她和楊大姐掩護了那位攝影師。endprint
1937年6月,張暉和楊大姐抵達西安,一路提心吊膽的日子終于告終。她們到了北新街七賢莊的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報道。林伯渠和熊天荊接待了她們,一切安頓妥當,囑咐她們耐心等待組織關系。八路軍辦事處的主要工作是:開展統一戰線工作,輸送進步青年去延安,為陜甘寧邊區和前方轉送戰爭物資。如今,在八路辦事處的舊址,成立了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1988年,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在等待組織關系的這段時間,張暉和楊大姐被安排在北大街一家幼兒園當老師。不久之后,楊大姐繼續留在幼兒園任教,張暉則進入了民眾教育館。這是國民黨的正規文化機構,張暉十分珍惜這份工作。在民眾教育館,張暉負責教一個兒童識字班和一個婦女識字班。此外,識樂譜會唱歌的她,還加入了抗日歌詠隊,教人們學唱抗日救亡歌曲。黨組織指示她要盡量利用合法身份宣傳抗日,擴大民眾基礎。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
拋棄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
整日價在關內,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哪年,哪月,
才能夠收回那無盡的寶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時候,
才能歡聚一堂?
抗日歌詠隊在西安的街頭唱起這首《松花江上》,聽到歌聲的老百姓都會情不自禁的圍上來,越唱人越多,大家一起唱,流著淚,一遍又一遍……《松花江上》在日寇大舉侵華的緊要關頭,唱出了“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民眾乃至全國人民的悲憤情懷,喚醒了民族之魂,點燃了中華大地的抗日烽火。
四
1938年2月,張暉的組織關系順利到達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推薦她去延安學習。從西安到延安,乘汽車有兩天路程,張暉是其中唯一的一名女乘客。她自小有暈車的毛病,唯有唱歌能緩解,兩天的旅途,張暉唱了兩天的抗日救亡歌曲,一路輕松愉快,全體同行人員包括司機都十分喜歡這個嬌小的女孩,一路上也格外照顧她。到了延安,恰逢1938年的元宵節,張暉觀看了江青和孫維世的話劇表演。孫維世飾演一位想要投身革命事業,卻受到家庭阻撓的富家大小姐,江青飾演她的母親,最終被女兒說服,支持女兒參加革命。這出戲是當時社會現象的真實寫照,無數有識青年,不論家境貧富,受到理想感召后奮不顧身投入革命的事業之中。這出戲也讓張暉想起了曾祖母,想起許許多多妹仔,還有她的入黨介紹人楊大姐。
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于1936年6月1日在陜北瓦窯堡創立,是中國共產黨為適應抗日戰爭的需要成立的中國抗日紅軍大學。1937年校址遷至延安,改名抗日軍政大學。毛澤東任教育委員會主席,林彪任校長。學員主要來自部隊抽調的干部,并招收一些知識青年,學習政治、軍事、歷史、民運、統戰等課程。“邊生產邊學習,邊戰斗邊學習”,是抗大辦學的特色。學員們邊行軍、邊學習,既完成了軍事任務,又學會了文化知識。張暉進入抗大后,先是在二大隊女生隊學習,她不僅文化課成績優異,軍事課也學得很好,還成為了一名好槍手。不久,因為組織的信任和辦學規模的不斷擴大,表現突出的張暉被任命為了三大隊女生隊的區隊長。也就是在這期間,張暉將她原來的名字張光瑜改為“張暉”。
張暉在抗大擔任區隊長期間,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工作當中。一天,正在和指導員匯報工作的張暉突然暈倒。經美國醫生,也是抗戰老兵的馬海德診斷,是感染上了肺結核,在舊社會被稱為“十癆九死”的不治之癥——肺癆。
由于當時缺醫少藥,病人往往只能依靠自己的抵抗力和病魔抗爭。為避免結核病大肆傳播,馬海德醫生給出了幾條建議,一是讓大家多吃生蒜、多曬太陽;二是增強體育鍛煉,用涼水洗臉,以提高自身抵抗力;三是有條件一定要睡午覺,保證休息避免超負荷工作。除此之外,八路軍還實行了嚴格的隔離制度。盡管如此,結核病還是大范圍的傳播開了。在組織的動員下,一些有條件的人只得回家休養。離開了延安,離開了熱火朝天的抗日事業,許多年輕人因此郁郁寡歡,有的病情加重,離世。
張暉經歷了一段隔離養病的日子,幸運地退了燒,再次投入到工作當中。可是由于未經過徹底的醫治,在之后的幾年當中肺病不斷復發,但她一直堅持工作,由于表現突出,被選為模范共產黨員,參加了表彰大會。這種一邊與疾病斗爭,一邊力爭做好工作的日子,伴隨了她的一生。
抗日戰爭期間,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人民抗日力量的指揮中心。從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飛機開始轟炸延安,到1941年8月,日軍陸軍航空兵對延安空襲達17次,出動飛機208架次,投彈1690枚,炸死炸傷延安軍民398人;僅1939年空襲就達10次,炸死炸傷人員達229人。張暉親歷了這些,1938年底的一個午后,她準備去往延安城的新華書店買書,一進延安,就被眼前的慘狀驚呆了,走在路上,看到的都是斷壁殘垣,地上,樹上,到處是殘肢,到處是人和牲口的尸首,耳畔都是哀嚎聲…… 面對眼前的景象,她義憤填膺,抗日烈焰在她的心中燃燒。
在延安大轟炸期間,中共中央及時組織撤退,有效減少了人員的傷亡。中央機關撤退到了延安周邊一些地區,在革命圣地延安的象征——清涼山繼續展開工作和學習。陳毅《赴延安留別華中諸同志》詩云:“眾星何燦爛,北斗駐延安。大海有波濤,飛上清涼山。”中共中央為躲避轟炸,在山崖的峭壁上人工開鑿了作戰室和教室。高聳峻峭的清涼山成為天然屏障,讓敵軍的飛機無可奈何。現山上建有“延安清涼山新聞出版革命紀念館”一座,館前矗立一座漢白玉雕像,旁有石碑,上面鐫刻毛澤東題詞:“深入群眾、不尚空談”。館名為陸定一題字,這是中國唯一的一座新聞出版專業博物館。endprint
1939年2月,一匹馬馱著高燒中的張暉到了距延安城幾十里的八路軍衛校。衛校的政治氛圍比不上抗大,多數學員和部分領導人具備一定的理論知識積累,而另外一部分教員和紅軍的衛生干部則是有過實戰經驗的。因此,兩方面經常互相不服氣,常出現意見分歧,身為指導員的張暉就肩負著加強政治工作、提高大家的覺悟,相互取長補短促進團結的工作。在衛校期間,張暉在肺病反復發作的情況下,依然強撐著沒有耽誤工作。
五
1943年,張暉進入陜甘寧邊區政府交際處工作。陜甘寧邊區政府交際處(又稱延安交際處),前身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外交部招待科,負責接待外來賓客。1940年,交際科改為交際處,中央組織部派曾在白區做過上層統戰工作的金城任處長。
延安交際處是黨中央在延安時期設立的黨政軍諸多機構中的一個部門,主要就是接待工作。 當時從國統區進入延安的第一站就是交際處,無論是自己的同志,還是我們的朋友包括許多愛國民主人士(如黃炎培、陳嘉庚等)、來訪的國民黨將領、國際友人等等,都由交際處負責接待。由于接待對象非常復雜,張暉作為交際處的工作人員,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和技巧搞好接待工作。結合之前的工作經驗,張暉熱情周到的對待朋友,同時也很好地接待了國民黨派駐延安的聯絡參謀。工作期間,張暉結識了她一生的愛人、戰 友——王再天。
王再天是優秀的蒙古族干部,曾任中共中央情報部副科長,在交際處負責情報工作。由于到延安的人士來自各個方面,他們經常帶來國統區各方面的信息,特別是聯絡參謀與重慶的往來通訊。王再天每天都要將這些通過各種途徑搜集得來的情報匯總后匯報給黨中央, 而張暉則將每天的情報復寫謄抄,報送中央和軍委的主要領導人。
1945年抗戰勝利,不久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王再天張暉夫婦帶著襁褓中的長子,來到冀察熱遼軍區交際處,王再天任副處長。次年6月,他們的第二個孩子出生,同年10月,他們接到任務,護送軍調小組到石家莊。于是,王再天張暉夫婦領著一歲的兒子,懷抱著剛過百日的小女兒上路了,可是張暉沒想到是,有國民黨成員和美國人的軍調小組竟然也會遭到襲擊。在護送途中,車隊突然遭到國民黨飛機的掃射轟炸,張暉和孩子在隊伍的最后,看到前面的車被炸,驚慌下車,她抱著小女兒翻滾到路邊的深溝里,而后又不顧一切沖回車里救兒子。張暉緊緊把兒子抱在懷里,剛跳下車,就看到敵機再次掃射過來,她來不及再跑只得趴在地上,彈雨在身旁落下,敵機在頭頂呼嘯飛過,張暉抬頭,清楚地看到飛行員的眼睛和他得意的神情,她充滿了憤怒。多年以后,回憶起當時的情形,張暉說,我們的孩子們長大了,一定要造更好的飛機,把他們都打下來!
完成護送三人小組的任務后,王再天張暉夫婦面臨一個選擇,一是去八路軍炮兵學校任教員,培養炮兵;一是去新建立的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繼續從事軍事和情報工作。 1945年11月6日,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籌備委員會在張家口組成。張家口也是王再天和張暉夫婦所在的冀察熱遼軍區交際處的駐地,張暉懂得王再天一直以來懷揣的民族情懷,看出了他的意向,她勸丈夫和時任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主席兼軍事部長的烏蘭夫同志先接觸再作決定。而后,王再天、張暉夫婦受到烏蘭夫同志的熱情接待,就這樣,他們來到了內蒙古。
在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工作期間,王再天任社會部部長,隨著戰事的發展,社會部經常要在草原上行軍作戰,婦女和兒童隨行多有不便,烏蘭夫同志便和蒙古共和國方面聯系,準備把聯合會在代喇嘛廟的家屬和孩子送到中蒙邊境蒙古共和國,蒙古共和國方面也表示愿意幫助安排。于是,張暉和另外幾名同志一起,負責帶領十多個家屬和二十幾個孩子到蒙古人民共和國邊境暫住。
六
1946年11月,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成員的家屬到蒙古人民共和國后,先是生活在蒙古人民共和國邊境的一片原野上,因為邊境一帶供應短缺,過了春節,她們出發前往首都烏蘭巴托。
到了烏蘭巴托,張暉和其他隨行人員積極爭取學習和工作的機會。不久,她們進入蒙古人民共和國中國工人俱樂部工作,張暉在俱樂部下設的圖書館任館長,后來又兼任俱樂部小學的教員。在圖書館的旗牌室里,有一臺收音機,可以收到來自延安的無線電波。每逢周末,大家都會聚在一起收聽廣播,一方面能夠了解國內的戰事,另一方面,來自祖國的聲音,親切的母語,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大家的思鄉之情。
1947年,內蒙古自治區成立,張暉等人在度過一年多異國他鄉的生活以后,于1948年3月回到家鄉和親人團聚。1948年至1956年,張暉任內蒙古政治部辦公室主任,由于她具有扎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組織經常派她到公安部的相關單位以及政法干校講課和做宣傳工作。在政治部任職期間,張暉生了四個孩子,生活的重擔并沒有影響她為革命工作的熱情。
1954年,大批高等院校相繼成立,這其中有內蒙古師范學院、內蒙古工業學院、內蒙古科技學院等。1956年,內蒙古醫學院成立,是新中國在少數民族地區最早建立的高等醫學院校之一。
張暉是內蒙古醫學院的第一任黨委書記,為醫學院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不論是在建院還是引進人才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張暉頂著巨大壓力,幫助了大批醫學人才。
1978年4月,張暉離休,現享受正省部級醫療待遇。 2017年7月,她剛剛度過97歲的生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