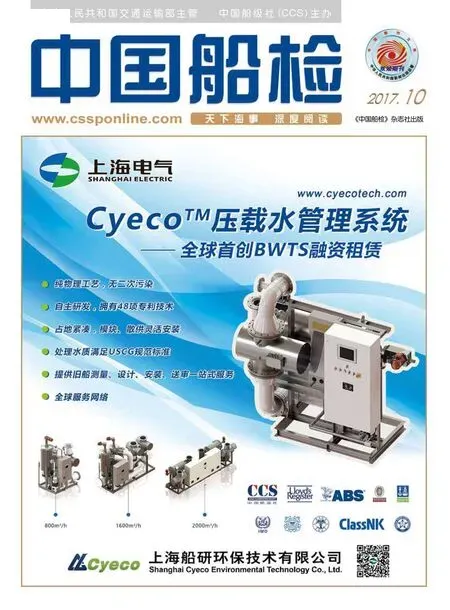《1979年國際海上搜尋救助公約》的誕生
沈肇圻
《1979年國際海上搜尋救助公約》的誕生
沈肇圻
為開展國際合作搜尋營救海上遇險人員,“海協”于1979年4月9日~27日在漢堡召開國際海上搜尋救助會議,討論并制定了《1979年國際海上搜尋救助公約》。公約強調發揚人道主義,規定締約國在本國的法律、規章制度許可的情況下,應批準其他締約國的救助單位為了搜尋發生海難的地點和營救遇險人員立即進入或越過其領海或領土。公約的附則對搜尋救助的組織、國家間的合作、搜尋救助的準備措施、工作程序和船舶報告制度等作了規定。公約自1985年6月22日起生效。中國于1985年6月24日核準了公約。
其實,制定這樣一部公約的想法最早要追溯到20世紀初。
長久以來,人們千方百計避免和防止海難,但事故仍時有發生,為挽救遇險人員的生命,搜尋和救助是重要的措施。“海上皆兄弟”,船長在海上接收到求救信息,要做出相應回應,這是古老的海上傳統,人道主義的表現。
1910年9月23日在布魯塞爾召開的第三次海洋法會議把這個傳統寫入了1910年統一海難援助和救助某些法律規定的公約,此公約在規定“無效果,無報酬”原則的同時,將這個傳統,用國際法固定下來。它的第11條規定:“船長在海上發現遭遇生命危險的每一個人,即使是敵人,都必須援助,只要這樣做,對其船舶、船員和旅客沒有嚴重危險。船舶所有人不因上述規定的違反而承擔責任”。
“泰坦尼克”號慘案后,第一次國際海上安全會議簽訂的1914年安全公約,也作出了類似規定。公約第Ⅴ章無線電報第37條規定:“接到遇難船舶求救的船長有責任向遇難船舶提供援助”。
1929年安全公約也有類似規定。第五章航行安全第四十五條:“遭難電信執行職務程序 第一款,船長于本船收到遭難之無線電信,應即開足速力(當時習慣用詞,相當于現在的‘馬力’),駛往援助,但船長委實無能為力,或按當時特定情形無理由或無必要為之執行或依本條第三款、第四款之規定,應免執行者不在此限(注:第三款指已知其他船已應征前往,第四款指已知其他船已抵遇險現場)。”
1948年安全公約作了進一步規定,第五章第一條遇難通信、程序規定:“海上船舶之船長,不論由任何方面接到有船、飛機或艇筏在遇難中之信號時,須以全速度前往援助遇險之人,如屬可能,必須通知他們正在前往援助中,若此船不能前往援助或因情況特殊認為前往援助為不合理或不必要時,該船長必須將未能前往援助遇難人之理由載入航海日志中。”
這樣的規定,一直沿用到1960年和1974年安全公約中。
第四次國際海上安全會議通過1960年安全公約的同時,還用決議形式對海上搜尋救助工作提出了建議:締約國政府應設立海岸無線電臺,以保證在無線電報、無線電話頻率及救生艇所用頻率上的連續守聽;“海協“應與國際民航組織(ICAO)、國際電訊聯盟(ITU)和世界氣象組織(WMO)合作研究搜尋救助設施計劃;“海協”、國際民航組織、國際電訊聯盟和世界氣象組織抓緊研究以最好的方式建立飛機與遇難船舶之間的通信聯系;締約國政府應鼓勵本國所有船舶參加商船船位報告系統,該系統應免費提供有關船舶所使用,政府應鼓勵船舶適時配備應急示位標,以利搜尋救助。
1969年“海協”起草了“商船搜救行動手冊”,作為海上遇難求救人員或救助人員的行動指南,并由1971年“海協”第七屆全體大會通過,推薦給各國使用。手冊共八章。它們的題目是:搜救協調、遇難船的行動、救助船的行動、飛機的救助、搜尋計劃及指導,搜救結束、通信及海上飛機事故。1978年“海協”修訂了這個手冊,改名為“海協搜尋救助手冊”,共兩部分,第一部分:搜救機構,主要介紹現有各國搜救機構,現有服務和設施等。第二部分:包括對所有參加搜救行動人員,特別是船長有幫助的資料。手冊還有一個附錄,“海上搜救識別規則”供搜救人員和被搜救人員----遇險人員的相互通訊聯絡之用。
1970年10月美國舉辦的搜尋救助座談會建議,“海協”應在海上安全委員會下設立一個搜尋救助專家組,著手起草國際搜尋救助公約。
往事拾遺之三十四
座談會認為手冊對海上搜尋救助業務流程作了詳細規定,對救助操作很有幫助,但海難事故的特點是偶然性、突發性,時間和地點都難以預料。因此不可能像岸上消防隊那樣,可以常設,這就需要國際間合作。同時海難救助,時間極為緊迫,可以說爭分奪秒,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聯系網絡,更好地協調行動。更主要的是搜尋救助可能要進入一國領海領空,又涉及國家主權,只有通過國際公約才能協調好這方面的關系。
海難救助是偶然需要,即使西方海運發達國家,也不保持一個長時間專門職業隊伍,而是依靠社會力量,作為公益事業,組織志愿人員來進行。例如英國救生艇協會,總部設在英國普爾(Poole),在一些海港有分部。總部設執行局長和秘書二人。分部也只有一到二個專職或兼職人員。會員均為志愿人員。因必要時要放下工作執行救助任務,所以均須所在單位同意,經體檢合格,登記在冊。協會組織培訓和操練,提供救助用設備和服裝,無報酬,只有年度評獎等精神獎勵。協會經費來自社會捐助,其中包括獲救人員和家屬親人的捐助。它成立于1824年。在荷蘭、前西德和加拿大等44個國家有類似機構。但他們是民間機構,相互間保持聯系,并組成聯盟。作為非政府性國際組織,“海協”還給予這個聯盟咨詢地位,可應邀參加“海協”會議,但涉及跨國搜尋和救助,涉及國家主權,他們就沒有決策權,因此有必要通過國際公約來建立政府間的救助合作渠道。
應前西德政府邀請,這次會議有51個國家派代表出席,2個國家和聯系會員香港派觀察員列席。此外,還有4個國際組織派出觀察員。5個非政府性國際組織也派了觀察員。總計245人。西德杰·布魯爾博士當選大會主席,中國等十個國家代表被選為副主席。
中國代表團由交通部救助打撈局吳英誠局長任團長,通知我從倫敦去漢堡,任副團長。圖1會議現場。大會選舉主席、副主席前,秘書長找我擬選中國代表團為副主席。經與吳英誠局長商量,他表示,語言上有難處。我說這是國家榮譽,可以在旁協助。選舉結果,他當選大會第一副主席。
這次會議是發揚人道主義精神的會議,對海上遇險人員伸出援助之手,挽救他們的生命。因此要強調爭分奪秒。但是海難事故不一定發生在本國海域,需要鄰國之間的合作。當援救來自鄰國時,就涉及入境問題。經過協商,中國代表團提出,援助和尊重主權必須兼顧,得到多數代表的認同。在締約國的本國法律許可情況下,應批準其他締約國的救助單位,只是為了搜尋發生海難的地點和救助海難中遇險人員的目的,立即進入或越過其領海和領土,寫入了公約。
人們都不希望發生海難。但還是時有發生。為做好充分準備,就需要將海域劃分成搜救責任區,由負責國家來承擔搜救主要責任,也不排除鄰近國家的協助。如何劃區,就需要相鄰各國來協商。這是一項非常復雜的工作。本來相鄰國家之間就有領海,還有大陸架,專屬經濟區的爭議。我們國家,按公約建議在第七區,周邊國家有澳大利亞、日本、朝鮮、韓國、越南、菲律賓、泰國、柬埔寨、馬來西亞、新加坡、文萊等。在討論中,我們表示了搜救責任區的劃分不應與國家領海主權相混淆。最后在公約中寫明,并強調:搜尋救助區域的劃分不涉及,并不得損害國家之間邊界的劃分。
會議討論通過了1979年國際海上搜尋救助公約。其主要目的是:為國際海上搜尋救助方案確立法律和技術基礎,以推動搜救組織之間和參加海上搜救作業的各個單位之間進行合作。公約有8個程序性條款和1個附件。附件共6章,開展搜救工作指導原則;名詞和定義;搜尋救助的組織機構;國家間搜救合作;搜尋救助的準備措施;工作程序和船舶報告制度。公約規定各締約國應盡快完善搜救機構,建立救助協調中心和救助分中心、劃定搜救區域、制訂搜救行動程序和通信聯絡程序,并建議在負責的搜救區域建立船舶報告制度,要加強各締約國之間的合作以及海、空搜救部門之間的合作,以便對海上遇險人員提供搜救服務。另外,會議還通過了8個決議,以推動進一步改善海上搜救作業。會議期間,在漢堡港內組織了救助表演。見圖2和圖3,還參觀了漢堡港用的救助船,見圖4和圖5。
因會后要應前西德一家救撈公司之邀,進行參觀訪問,國內來專業人員六人,譯員三人,加我共有十人之多,原擬住外貿部駐漢堡商務處,但它在郊區,無公共交通。我們在附近散步,竟有西德人停車,好心地問,要不搭他車進城。于是決定搬去會場——漢堡國際會議中心附近。所住旅館房內,只有一個小臺燈,三周會議文件眾多,只能夜間閱讀,準備意見。會后回到倫敦,竟有一個小黑點在左眼內不停地轉動,英國皇家醫院稱,要住院手術。經大使特準,有生以來第一次住院。第二天,輪椅推進手術室,半小時完成手術,用冷凍方法把破裂視網膜補起來。怕愛人沈福妹擔心,未告訴她。1990年工作調動到中國船舶工業集團,被派去漢堡任西歐代表處首席代表,愛人同去常駐。一次去漢堡國際會議中心參觀,因時間已過去近二十年,才告訴她眼睛出過事,在她建議下照了張照片留念(見圖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