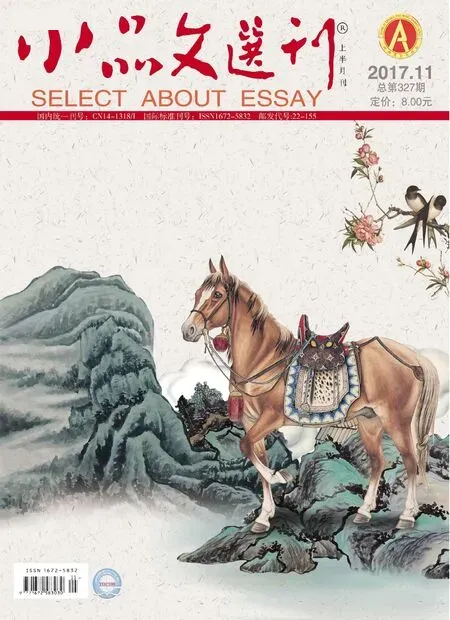我將成為土壤
□小艾
我將成為土壤
□小艾
1881年,一艘從東京駛往紐約的客輪上,一位面容清秀的東方女子站在甲板上,她出神地盯著茫茫大海上逐浪的海鷗,思緒卻回到遙遠的過去。
記憶的影像是模糊的,她出身于寧波一個基督教會牧師家庭,2歲半時,父母在一場瘟疫中雙雙去世,是父親在中國工作的美國好友麥嘉諦收養了她,8歲時,養父母帶著她東渡日本,在那里讀完中學,她天資聰穎,學業優秀,精通英文和日文,喜愛之余,養父決定送她學醫,就這樣踏上了去美國的路。
她叫金雅妹,這年,只有17歲。
海上顛簸數周后,金雅妹抵達美國,進入紐約女子醫科大學,成為該校唯一的中國留學生。她“虛心好學,注重實驗和各種醫療器械的使用”,四年后,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成為第一個獲得大學文憑的中國女留學生,在紐約的中國領事參加了她的畢業典禮。

畢業后,金雅妹繼續深造,1887年,她在《醫學雜志》等權威刊物上發表了多篇當時剛剛興起的顯微醫學研究的學術論文,扎實的功底引起紐約醫學界的重視,多家醫院紛紛向這個嬌小的東方女子拋出橄欖枝。然而穩定的工作、優越的環境并不能撫慰她思鄉的心,父母因醫療落后而亡故的慘痛經歷“一直烙在心里”,她堅信“自己的事業在中國”。
1888年底,金雅妹回到闊別16年的祖國,進入福建廈門一家教會醫院。緊張的工作中,她不幸染上了瘧疾,氣候不適又兼舉目無親,不得已投奔在日本工作的養父母。在神戶,她結識了一位葡萄牙音樂家,為了愛情,隨他重返美國。
身在異國,金雅妹仍然不忘中國心,她交往廣泛,經常發表演說,向美國社會介紹中國的人民和文化。“兩千年來,中國人始終是和平的守護者,和平是中國人的天性”,在1904年的第13屆世界和平大會上,她以獨特的講演魅力駁斥了當時西方的“黃禍”論(中國威脅論),她還就遠東政治形勢發表演說,揭露日本侵華陰謀,《紐約時報》這樣稱贊:“金雅妹醫生這位優雅嬌小的中國女性,以其為自己人民辯護的演說,一直使美國聽眾傾倒。”
遺憾的是,異國情緣僅僅維持了10年。婚姻失敗,心系祖國的金雅妹再次回到故土。她開辦私人診所,高尚的醫德、高超的醫術在多地負有盛名,1907年到天津后,受邀出任北洋女醫院院長。
行醫中,金雅妹深感條件落后、人才缺乏,嬰幼兒的高死亡率尤其使她痛心,正值清政府倡興女學,她說服了當時的直隸總督袁世凱,創辦了我國第一所公立的護士學校——北洋女醫學堂,她親自擔任堂長兼總教習,成為中國護理教育的開拓者。第一批學員畢業后,津門女性率先告別了“接生婆”時代,享受到了西方先進的接生技術。
辦學之余,金雅妹還籌辦紅十字會,管理育嬰所,積極從事社會活動,兩次旅美期間,都不忘通過演講向美國傳遞一個真實的中國,“我的旅行不是讓我更出名,而是讓我的國家更好地被了解。”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日本以對德國宣戰為借口出兵山東,正在美國的金雅妹發表演講,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日本的狼子野心,一時間,這個身穿鮮艷的中式絲綢長袍、發鬢上總是插著一朵鮮花,又精通多國語言的東方女性成為紐約的傳奇,《紐約時報》稱她是“當今世界最杰出的女性之一,是本民族進步運動的一位領袖”。
晚年的金雅妹定居北京,依舊熱心于醫療和社會公益事業。盡管幼年喪親,中年離異,唯一的兒子又死于戰爭,但她始終“在亂世中保持著東方女性特有的堅持與優雅”,只有北平的寒夜、客廳的壁爐見證著這個裹在大衣里的老婦人的孤獨。
1934年3月,金雅妹因肺病去世,依她生前的愿望,長眠于海淀的農場里,在那小小的樹叢里,她睡得甜美而愉快,“我的骨灰會與土壤混合,待到他們在我墳頭拍成的那堆泥土瓦解,我將成為土壤,肥沃的土壤。”
選自《青年博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