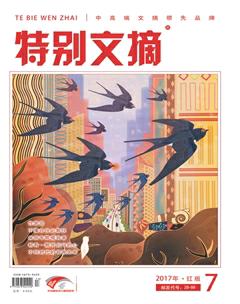文盲高育良
這個時代,有讀書人和偽讀書人,區別并不在于讀書的多少。論讀書量,停車場的保安讀書很多,沒事就拿著手機看小說,一天十多萬字,大學教授反而讀書時間不多,都用在跑項目、發論文上了。
《人民的名義》里,高育良是學者從政。作為政客,他是貨真價實的。但作為學者,他真的像傳說中那么淵博嗎?——不,實際上,他就是個文盲。
電視劇中,高育良很少直接開口談學問。我印象中,只有兩處:一處是和侯亮平講岳飛情商低,死于莫須有。一處是問高小鳳讀什么書,高小鳳說《萬歷十五年》,高育良表示出濃厚興趣。
岳飛情商低不低,這是宋史問題,比較復雜,高育良不懂無可厚非。我們講個簡單點的,“莫須有”的意思,不懂這個,就有點說不過去了。
高育良一再講:莫須有什么意思?就是未必有。
去查查詞典吧。能望文生義嗎?——噢,“莫”就是“未”的意思,“須”就是“必”的意思,“莫須有”就是“未必有”的意思?
這就是高育良的水平。
如果說“莫須有”是“未必有”,怎么拿“未必有”給人定罪呢?高育良不是老強調“疑罪從無”嗎?這邏輯上都說不通。
實際上,“莫須有”是“也許有”的意思。換言之,是“未必沒有”——“莫不是該有吧?”
高小鳳說,她最近在讀《萬歷十五年》。可是有哪些證據表示她真的讀過,又得到什么啟發呢?
“我就覺得,明朝的皇帝太難當了。”
你要是上大學,老師布置讀這本書,讀完,你的心得就是“皇帝太難當”,要能及格,只能說,老師太草包了。
哪個朝代的皇帝好當?——這個心得,還要讀過《萬歷十五年》才知道?沒讀就是沒讀,甭裝。
不知高育良是故意沒戳穿,還是高育良自己也沒讀過,他說:“那大臣就好當了?”
這句更有意思。從對話中,你完全找不到任何證據,表明這倆人真讀過《萬歷十五年》中哪怕一行。不過,這個回答很巧妙,透露出一種態度:我相信你讀過。這說明什么?自然說明我也讀過嘍。
調情就是調情,非得以《萬歷十五年》的名義,這就是文盲病,生怕人家不知道自己有文化。
高小鳳接下來一句更有意思:“書記您不覺得,有明一代的臣子,都很強勢嗎?”
太亮了。這句話暴露出,高小鳳確實被培養過,被訓練過——不然,她怎么懂得把“明代”叫作“有明一代”?
一個地級師范學院的教師,花月把兒時間,就能把一個沒怎么上過學的漁家女,調教成一個懂明史的人,還超過名牌大學的明史專家,這說明什么?大眾很好欺騙,文化人很好冒充。
無論觀眾如何看待作為政客的高育良,很少有人否認作為學者的高育良。雖然他實際上是連“莫須有”的意思都搞不懂的草包。
事兒還是那檔子事兒,只不過,以文化人的名義罷了。
雖然你也沒文化,我也沒文化,但我們彼此達成默契,互相承認對方的淵博,大家就都是文化人了,都有品位了。
(摘自“王路在隱身”微信公眾號 圖/亦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