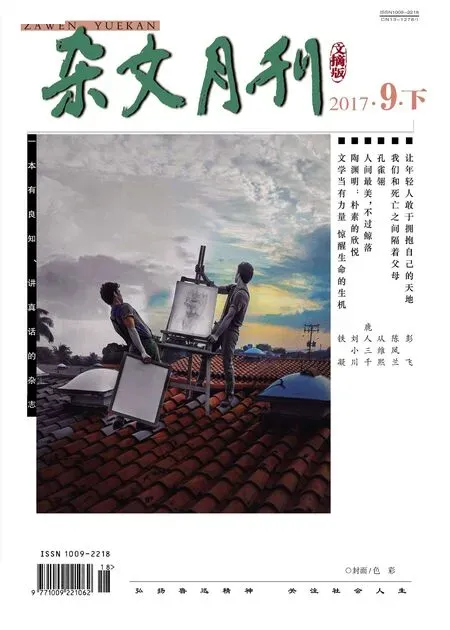游走于道德和法律之外
□趙 威
游走于道德和法律之外
□趙 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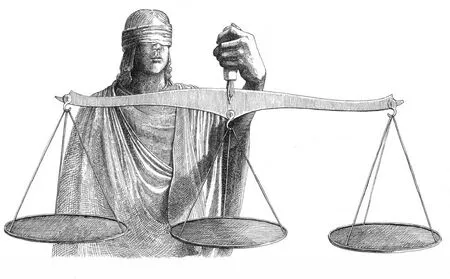
《紅樓夢》里“豐年好大雪”的薛家有個公子哥兒薛蟠,外號“呆霸王”,愣得很,犯過兩起命案。第一次,因與馮淵爭買香菱(甄英蓮),指使家人把對方打死。馮淵的仆人將薛公子告到應天府,知府賈雨村新官上任,想一試身手,卻被門子一個眼色攔下。當他得知,對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賈政是薛公子的姨夫后,做了個順水人情,使薛公子逍遙法外。第二次,薛公子去南方置貨,在酒館喝酒,跟酒保起了沖突,拿碗將對方拍死了。薛公子被官府捉住,判了個絞監候。薛姨媽和王夫人央求賈政出面,上下打點,復審時,證人改口,而且仵作(管驗尸的衙役)協同書吏在驗尸報告上做了手腳。此案便由故意殺人變成誤傷,把薛公子關進大牢,等待上級審核。上面反駁下來,牢里的主文相公即刻做了回文頂了回去,薛公子再次逃過刑罰。
這兩起命案中的門子、仵作、書吏、主文相公,連同其他章節中管門的李十兒、書辦詹會、刀筆先生等,都屬于同一個群體——胥吏,他們不同于官員,那么,和官員之間是什么關系呢?
清道光年間有個叫惲世臨的進士,曾先后任長沙知府、湖南巡撫。中進士前,有次他在京城一家酒館喝酒,偶爾聽到鄰桌的一名胥吏對人說,官場就像一輛車子,我等吏人好比趕車的人,主官和屬官好比騾子,我們鞭子一揮,叫他們向左他們不敢往右。惲世臨聽了,心中暗暗“怪嘆”。(清·朱克敬《瞑庵雜識》)
“官人視事,則左右前后皆吏人也,故官人為吏所欺、為吏所賣,亦其勢然。吏人自食而辦公事,且樂為之、爭為之者,利在焉故也。”宋人陸九淵的這段話,簡明扼要地道出了官與吏的關系。
“縣官不如現管”,作為各項政策實際操作者的胥吏,往往挾持主官,陽奉陰違,暗中掣肘。《紅樓夢》第九十九回說,賈政外放江西糧道,一心想做個好官,連“有約束力的規范空間”都放棄了,從家里帶著銀子來做官,嚴格管理,以致手下的人沒機會撈好處,于是,他們開始找碴兒了。先是長隨(生活秘書)集體告假,后是管門的李十兒攛掇眾人向賈政發難,沒人打鼓,沒人吹號筒,沒人抬轎;一問,有的說誤把號衣當了,有的說三天沒吃飯抬不動轎子。最后,干脆連飯都不給賈政做了,理由是銀子花完了。這時,在李十兒的一通為官“大道理”的調教下,賈政就范。
封建社會的胥吏是一個游走于道德和法律之外的群體。用來規范、制約官吏的,首先是法律。然而,由于各地的情形千差萬別,若嚴格按照法律條文執行、搞一刀切的話,官僚體系或許就會崩潰;于是各方之間相互制約,形成了一種張力。官逼民反,只要民不反,官吏就可以不斷加壓。但是,做官是要講良心的,這便是官德。朝廷通過諸多措施,提高官員的道德,以求清官廉吏——道德的自我約束力量甚至大過了法律。
當時,官員受儒家文化熏陶,要立言、立德、立功;所以,法律和道德對其起到一定的約束作用,但對胥吏來說,則毫無用處。胥吏不是官,不受法律和監察制度的制約;胥吏是賤民,沒有上升渠道,為吏的目的就是生存——因為想撈錢,所以貪;因為貪,所以猾、酷、惡。因此,也就只能期盼有個青天大老爺,來約束他手下的胥吏了。胥吏對民眾的魚肉,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可以填補低賤身份帶來的自卑心理。民眾對官府的不滿也往往轉嫁到胥吏身上,但他們既害怕胥吏的蠻橫,又鄙視胥吏的卑賤,還羨慕胥吏的漁利,這種心理是極其矛盾的。
作為歷史鏡鑒,胥吏之害暴露了古代官僚體制的弊端,對后世影響深遠。
郭旺啟薦自《上海法治報》2017年7月24日 王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