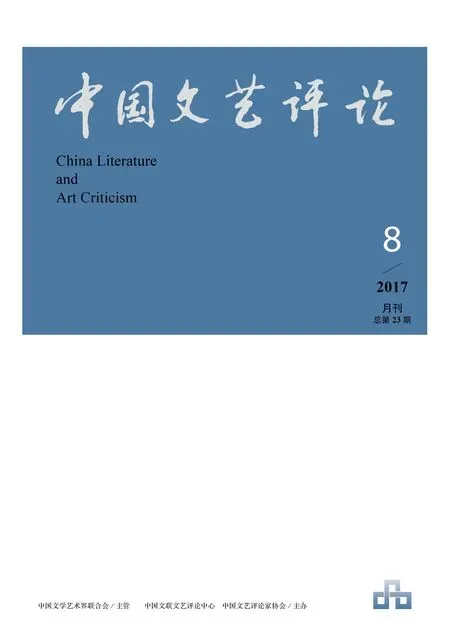藝術無涯與歷史有待
——以話劇《啟功》為例
解璽璋
藝術無涯與歷史有待——以話劇《啟功》為例
解璽璋
戲劇舞臺如何寫人,如何寫好歷史的人,是當下戲劇創作遭遇的眾多難題之一。本文試圖從歷史劇的本性、歷史與歷史觀對戲劇創作如何處理歷史題材的制約,舞臺表現手段的創新與作為戲劇主體的人在舞臺上的地位,形的實事求“史”與神的得意忘“象”的分寸和互為依存,以及虛構與想象的必要性、局限性和實現的手段與方式等諸多方面,探討并回應這個問題,提出自己對這個問題的一點見解,以期引起更多人的重視和興趣。
歷史劇 歷史觀 舞臺與人 形神兼備 虛構與剪裁
舞臺上的歷史劇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紀事的,如《西安事變》;一類是寫人的,如《大先生》。當然,紀事的也要寫人,寫人的也離不開紀事,二者兼而有之,區別只在以誰為主。我們這里所要討論的,便是如何寫人。
文學是人學,戲劇也是。舞臺為人立傳,人就是舞臺的主宰。沒有人的舞臺是一片荒漠,人在舞臺上立不住,舞臺也就立不住,是會塌陷的。可見,寫好人對戲劇舞臺來說是多么重要。
這個簡單的道理做起來并不簡單,因為人不好寫。世界上沒有比人更復雜的事物。現在有許多關于戲劇、舞臺,乃至劇場的新理論、新探索、新實驗,都把精力用在手段和形式上,人有時倒成了陪襯,甚至異化為工具。這是當下戲劇舞臺很少能打動人的原因之一。
手段和形式并非不重要。一定的手段和形式總是和一定的社會背景、文化背景及心理背景相聯系,和一定的生活形態與意識形態相聯系,所以才有“有意味的形式”和“形式化了的內容”的說法。至于“意味”和“內容”,仍少不了“人”這個核心要素。《啟功》一劇是很強調“手段和形式”的,劇作者要求“呈現舞臺假定性、形式感和間離感”,要求“營造儀式感、舞臺感”。這些“感”能否成為“有意味的形式”和“形式化了的內容”,卻正是我們要討論的。
戲劇舞臺上的人固然活在一定的形式中,但賦予人生命和靈魂的,卻并非形式,或主要不是形式。通常,人以幾種不同的面貌呈現在戲劇舞臺上。作為導演手中工具和玩偶的人就不說了,比較多的,是只有軀殼且精神空洞、靈魂出竅的人物,或神氣飛揚而根基不牢,脫離現實的人物。形神兼備是戲劇舞臺寫人的最高境界,因其高,故十分難得。《啟功》所設定的目標不可謂不高,劇作者也做出了可貴的探索和努力,“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形神兼備之所以很難,是因為劇作者總要兼顧形、神兩個方面,并將形、神融為一體。先說形。我們強調“神”的重要性,并不意味著“形”不重要。形靠神獲得生機,神靠形得以顯現。我們畢竟不是御風而行的列子,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運行軌跡,劇作家寫人,不能不顧及到這一點。這便是莊子所謂有待,有待即有所限制,不能放任胡來。人都是歷史的人,故寫人一定要尊重歷史。不尊重歷史,甚至改寫歷史,其結果是給人物戴上一副虛假的面具,看上去可能光鮮亮麗,或丑陋猙獰,但隨著時光的流逝而磨蝕、消退,真相總會顯露出來,而失去的是觀眾對于戲劇舞臺的信任。郭沫若是歷史劇的大家,他的《蔡文姬》《武則天》《虎符》《屈原》,都曾風光一時,但事過境遷,其價值也是要打一些折扣的。他曾有過“失事求似”一說,意思是說,如果能求其“似”(藝術本在似與不似之間),則“事”可“失”。而一旦“事”(歷史真相)有所“失”,那么,欲求其“似”也是可能落空的。他還說過“蔡文姬就是我!——是照著我寫的”這樣的話,既然如此,蔡文姬“似”了郭沫若,就一點也不奇怪了。雖然他告訴我們,他“沒有絲毫意識,企圖把蔡文姬的時代和現代聯系起來。那樣就是反歷史主義,違背歷史真實性了”,但是,觀眾還是能夠從劇中看到,那不是蔡文姬的時代,而是郭沫若感受到的“郭沫若時代”。
蔡文姬固然是有“神”的,不過,此“神”已非蔡文姬之“神”,而是換作郭沫若之“神”了。其中的原因,或許要比“失事”復雜得多,我們暫且不去管它。可它昭示于我們的危途和險境,卻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想象未嘗不可,虛構未嘗不可,如果這些想象和虛構能夠成功地喚起我們對于歷史真相的某些認知,我們就應該感謝這些想象和虛構。而獲得這種效果的前提之一,就是相信“事”不可“失”。戲劇性很重要,盡可能地忠實于史實同樣重要。《啟功》是在實事求“史”上下過一番功夫的。看得出來,劇作者在講述啟功的人生經歷時一直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甚至顯得有些過于拘謹,盡管如此,觀眾對于舞臺上的這個“啟功”還是認可的、接受的,“這就是啟功”,他們說。要知道,坐在臺下的這些觀眾,有許多是啟功的親屬、學生、同事、朋友,他們或與啟功朝夕相處,或經常往來。這顯然增加了在戲劇舞臺上為啟功立傳的難度,并且凸顯了實事求“史”的重要性。也就是說,寫一個離我們很近的人,劇作者的想象力可能會更多地受到歷史的限制,稍一疏忽就會前功盡棄。
但是,歷史畢竟不能等同于戲劇,雖然我們常說,歷史曾經上演過,今天也仍在上演著一幕幕活劇。然而,沒有人可以把歷史活劇原封不動地搬上舞臺,以取代戲劇。很顯然,戲劇的表達是有其自身規律的,違背了這個規律,則難以實現戲劇的目的。在這里,首先要予以關注的,就是剪裁。無論是處理我們自己的生活經驗,還是處理歷史人物的人生經歷,只要你不否認在搞文學創作,沒有不需要剪裁的。只有經過剪裁的人生,才可以區別于履歷表和年譜,產生文學的意味。常聽人說,文學寫作中以戲劇為最難,就因為戲劇對剪裁的限制更多,要求更高。剪裁是實事求“史”的重要手段,剪裁就是“求”。“求”的過程,也就是剪裁的過程。
那么,如何進行剪裁呢?這顯然不是單純的技巧或技術問題。誠然,在剪裁背后,是有更多的東西作為支撐的。這是些最基本、最核心的,先于剪裁而存在的因素。比如歷史觀、價值觀、戲劇觀,又比如敘事立場、敘事態度、敘事角度和敘事方式等,都制約著劇作者對敘事對象的剪裁和處理。《啟功》的劇作者沒有選擇按照線性時間邏輯進行剪裁,而是采取了主題性縱橫交錯的剪裁方式。她為全劇設置了四場加尾聲的結構框架,分別為:第一場:竹之愿,第二場:竹之學,第三場:竹之緣,第四場:竹之節,尾聲。竹子的意象是全劇的關鍵,也是劇作者剪裁啟功人生的重要依據,可惜沒有引起導演的重視,舞臺布景和天幕投影都忽略了這一點。
我們看到,在“竹之愿”中,啟功已垂垂老矣。他的唯一心愿,是在有生之年,以一己之力,為恩師陳垣籌備“勵耘獎學金”。這里是要表現他的知恩、感恩、報恩,劇作者把文章作在“寫字”上,為“勵耘獎學金”募捐而寫字,是報恩,為學校退休司機、女清潔工、河南來的打工者寫字,何嘗不是報恩?或者是有感于、同情于別人的報恩,就像那個河南人,因老父患腎病,兒子患肝病,家中困難,才向他求字的。這是從側面烘托他的知恩、感恩、報恩。還有從反面渲染的,比如在任的空軍首長,喜歡拿贗品蒙人的畫廊老板,包括有人想以愛新覺羅家族的名義搞書畫展,求他寫字,他都一口回絕,不容商量,顯出他的狷介和耿直。
再看“竹之學”。這一場的場景是一年一度的畢業典禮,啟功先生正為畢業生作報告。他講了自己的家世,先祖給予他的影響,少年時代所經歷的貧窮和困苦,祖父對他的培養,曾祖和祖父的門生如何救助他們一家,他由此感受到師道的傳承,師生情誼的偉大,最后歸結到他的平生志愿,是要做個傳道、授業、解惑的教師。他把自己比作一根“竹筍”,深知竹筍長成高竹的不易,猶如他這一生,不經歷“好幾年的黑暗和掙扎”,哪有“破土而出”的幸運?恰如一首詩說的那樣:“泥中莫怪出頭遲,歷盡冰霜只自知。昨夜震雷轟渭畝,請君來看化龍枝。”這時,天幕上出現了竹筍破土而出的投影,舞臺一角,少年啟功正在祖父的指導下,搖頭晃腦地吟誦蘇東坡的《游金山寺》,老年啟功雖未離開舞臺,他的敘述倒更像是“畫外音”了。在這里,他用自己的人生經歷,詮釋了“學為人師,行為世范”的校訓,身為教師,就是要以勵志和傳承為己任,反哺社會。
第三場“竹之緣”是第二場“竹之學”的延續,不是時間的簡單延續,而是內在的戲劇邏輯的延續。這場戲的核心情節是“三進輔仁”。舞臺空間被一分為三,扮演啟功的演員在“老年”和“青年”之間跳進跳出,并在講述與表演之間互相轉換。啟功初識陳垣先生就在這個時候。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先生在他的勵耘書屋接待了這個來求職的年輕人。他給陳垣先生留下了不錯的印象,是個可用之才,遂安排他到輔仁附中教一年級國文。不久,有人借口他中學尚未畢業,不能教中學,把他趕出了輔仁。陳垣先生不認為學歷可以決定一個人的前途,既然啟功有比較豐富的繪畫知識,于是,他又被安排到美術系做了助教。可惜,還是有人不能接受他,他又被循例開除,離開了輔仁。這期間,他迫于生計,在日偽政府的秘書廳里找了個助理員的職位。有一天,陳垣問到他近來有沒有事做,他隱瞞了真相,說:“沒有。”結果他三進輔仁,跟著陳垣先生教大一國文。后來他向陳垣先生坦白自己說了假話,陳垣先生對他只說了一個字:“臟!”這個字讓啟功羞愧難當,長跪不起,淚流滿面。他把這個字視為恩師的當頭棒喝,告誡自己要警戒終身,不能再沾染任何污點。
第四場“竹之節”的動人之處,是把啟功生命中絕望的痛苦和悲泣展現在了舞臺上。“文革”中,恩師陳垣去世,他卻失去了最后與恩師告別的資格。遠處隱約傳來陳垣告別儀式的樂聲,這時,舞臺上出現了悲壯的一幕,被巨大傷痛所淹沒的啟功,要在家里私祭恩師。他寫的挽聯鋪滿了舞臺,掛滿了舞臺,他就跪在挽聯的海洋里,高舉酒杯,灑酒祭奠。這不僅是一個學生獻給老師的祭禮,更是中華道統綿綿不絕的一個象征,一種誓言。多年后,啟功已是桃李滿天下,教師節這天,學生們來看望老師,在師生們無拘無束的對談中,一種深深的憂慮和不安慢慢浮現出來,即使濃濃的師生情誼也掩蓋不了。有的學生對老師說,面對殘酷的現實,他不得不選擇離開學校,離開教師這個職業。啟功是否想到了當年他的“迫于生計”呢?這也許不可同日而語,但此時的他,無可奈何之余,也只有嘆惜:由他去吧!這種氛圍彌漫在舞臺上,給我們一種強烈的刺痛,也促使我們去思考。
總而言之,這四場戲全是圍繞“竹”這個意象來展開的,竹是《啟功》一劇的精神內核。中國傳統士人(文人)將“梅、蘭、竹、菊”譽為“四君子”,以此象征人格的高潔。早在先秦時期,人們就注意到了“竹”與君子人格之間的同構關系,寫出了以“竹”寄寓君子美德的詩句。唐代白居易更以《養竹記》一文總結“竹”的“四大美德”,他寫道:“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似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可見,古代的士人君子是以“竹”的品格自喻、自勉的。《啟功》的作者發現,在啟功、陳垣兩代人身上,就突出而鮮明地體現了“竹”的品格,他們在艱難困苦中對學統、道統的堅守與傳承,所體現的,正是“竹”的涵養和節操:頑強堅毅、不屈不撓、欺霜傲雪、經冬不凋、瀟灑俊逸、不為俗累、安之若命、謙虛待人。
自古以來,畫“竹”者多矣,但白居易說:“植物之中竹難寫,古今雖畫無似者。”他不無夸張地認為,就他目力所及,至今還沒看到畫得很像的,只有“蕭郎筆下獨逼真,丹青以來唯一人”。我們且不管這位蕭郎到底畫得怎樣,只看白樂天評判這幅畫時用的標準:“不根而生從意生,不筍而成由筆成。”這里涉及到一個中國古典美學的重要概念,即所謂“意”。古人言道:“言生于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于意,故可尋象以觀意。”進而言之:“然則忘象者,乃得意也;忘言者,乃得象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這也就是白居易贊賞蕭郎畫竹的理由,不生于根而生于意,不出于筍而出于筆。說法不同,意思是一樣的。在古人那里,象比言重要,意比象重要。言可以忽略,象不能忽略;象可以忽略,意不能忽略。超越了言與象,就有了得意的可能性,用于畫竹,也就接近了似與逼真,就有了生氣灌注的感覺,就不僅寫其形而且傳其神了。
描摹人物,為人立傳,更不能拘泥于形似,以形傷神,得形忘神。當下的戲劇舞臺,何以真人少而木偶多,神似少而形似多?簡言之,就在于寫其形而未能得其神。有形而無神,有象而無意,故原本活生生的人物,到了舞臺上,也就成了沒有生氣的“木偶”,僅有形似,難有神似。固然,“作畫形易而神難。形者具形體也,神者其神采也。凡人之形體,學畫者往往皆能,至于神采,自非胸中過人,有不能為者”。作畫如此,作戲也不例外。劇作者如果不是胸中過人,也就很難捕捉到筆下人物的精神意象,賦予他元氣淋漓的生命活力,達到形神兼備的境界。《啟功》一劇,以“竹”寫人,寓人于“竹”,將“竹”的品格蘊涵在啟功、陳垣的人格之中,猶如點睛之筆,使得啟功、陳垣的形象在舞臺上有了鮮活的生命,像雨后春筍,蓬勃生長,氣韻不凡。
竊以為,話劇《啟功》是啟功的精神傳記,人格評傳。歷史劇寫人,為人立傳,常用敘事體,以戲劇沖突推動情節發展,在社會歷史情境中完成對人物性格的刻畫和形象的塑造。然而,寫人的精神、品格,敘事則難免采取夾敘夾議的方式。劇作者聲稱,她要作的是一部“敘述體史詩劇”,既是詩,主觀的表達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看劇中,常有啟功出來自言自語,現身說法,這種自述式的袒露心跡,有時是針對舞臺上其他角色的,有時是直接面對觀眾的,總之是說出來而非演出來的。甚至還有劇作者自己“站”出來,以類似“旁白”的方式,交代背景,提示觀點。這種表現方式顯然是一著險棋,搞不好,很容易傷害劇作的真實性和藝術效果。特別是觀眾看多了說教式的、主題先行的作品,對此也許就會先入為主,心生反感,橫加排斥。
誠然,這種情況畢竟沒有發生在話劇《啟功》身上。這要感謝劇作者所采取的兩個“補救”措施,終于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使該劇平安度過一險。首先是在敘事中,劇作者大量采用了帶有啟功個性和文人特點的行為方式和風趣的語言,比如他拒絕那位來求字的空軍將領秘書,一本正經地說了一句話:“我要是不寫,你們不會派飛機來炸我吧?”為了把那些求字的人擋在門外,他寫了一張字條“大熊貓病了”貼在門楣上。一個常拿贗品蒙人的畫廊老板來看他,他靠近門窗,把身體的各個方面一一展示給對方看,然后說:“看完了吧?那就請回吧!”那人很尷尬地說,還帶了一些禮品,啟功笑著說:“你到公園看熊貓,還帶送禮嗎?”畢業典禮上,他先向學生們作揖鞠躬,又稱“各位學長”,讓學生們一時摸不著頭腦。一個學生要用氣功治他的頸椎病,問他什么感覺,他頗為無辜地說:“我感覺,你差點兒把我推到臺下頭去!”然后笑著說,“看來,氣功治不了啟功啊!”
這種啟功式的幽默在劇中還有很多,不一而足。而正是這些內容的積累,成就了啟功形象的生動和逼真。它提醒我們,歷史不僅是一些事件和故事,乃至細節,還有活躍在其中的人的行為和言說方式,以及語言,這是最有助于恢復歷史真相的寶貴資源。同時,劇中還穿插了溥心畬、吳鏡汀、賈曦民等老一輩文人對他的熏陶和教誨,顯示出啟功成長過程中思想文化資源的豐富性和多樣性。至于劇作者的另一個“措施”,其實是對該劇舞臺空間和敘事角度的整體設想,她借鑒了古希臘戲劇的舞臺呈現方式,歌隊在其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以及獨立的敘述空間。歌隊的存在,使得演員離開角色身份的“自白”,以及劇作者本人關于舞臺之外發生事情的敘述,都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這都是古希臘戲劇舞臺呈現方式固有的特點;包括扮演劇中人物的演員,在幾個角色之間轉換,以穿戴不同的戲裝和面具來說明身份,也是其傳統之一。甚至劇中人物(不僅歌隊演員)對臺詞的處理,以朗誦、吟誦的情調敘事和解說,使演出更具有莊重的儀式感,凸顯了舞臺的“悲劇”美和悲愴的意味,雖然它并不是一部標準的悲劇。
令人不勝惋惜的是,該劇的二度創作沒有從整體上考慮歌隊的重要性,過于輕率地把它降低為一種陪襯,一種可有可無的舞臺的“盲腸”,從而削弱了該劇舞臺呈現的藝術魅力。
解璽璋: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副秘書長
(責任編輯:陶璐)